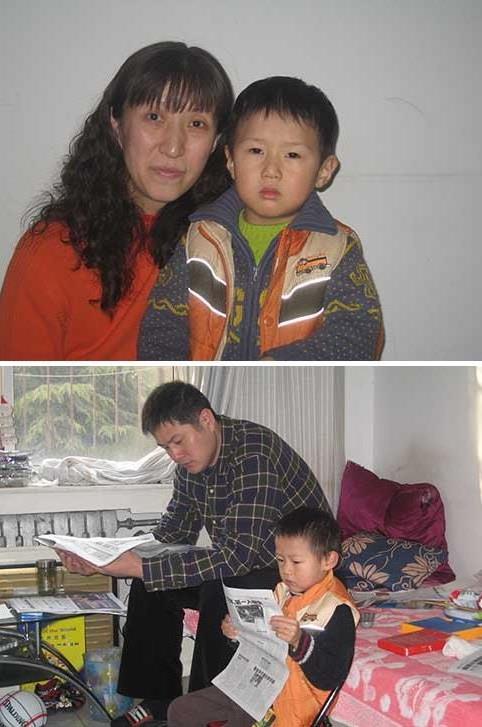乔治桑塔亚纳 重新发现桑塔亚纳 (孔新峰)
半个多世纪前,一群闲极无聊的哈佛毕业生筹建了所谓“美国君主党”(American Monarchist Party),当被问及谁是其心中君主的不二人选时,异口同声的答案竟是他们的哈佛校友、长期寓居英美的西班牙人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
柏拉图“哲学王”故事的这一20世纪版本虽然语近戏谑,但确实反映出桑塔亚纳在当时西方学子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小说家或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等多种面貌见称于世。
他曾获得过世界性的声誉,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其自传体著作三部曲之一的《人与地》(有人认为该书取得了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叶芝的《回忆录》以及《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相仿的成就)及小说《最后的清教徒》在美国一度是洛阳纸贵的畅销书。
《时代》杂志在其去世后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将其与伯特兰·罗素以及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并称为“西方三位最具智慧的老人”。
我国文豪钱钟书先生早在1933年即已将桑塔亚纳归入“五位近代最有智慧的人”之列。 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降的英美学界,桑塔亚纳的思想及其重要性却鲜少为人讨论。在许多人看来,他的著作过于散漫驳杂,欠缺明晰的体系性,而如今更显得迂阔不实而使读者寥寥,不再具备“第一流的哲学与文字”所具备的那种丰厚的启迪意义。
当然,这种局面近来已然有所扭转,包括约翰·格雷(John Gray)在内的诸多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其自由主义批判及对西方人文主义危机之诊断的当代意义。
有鉴于此,桑塔亚纳若干重要著作的中译本近年来也陆续问世。 桑塔亚纳得享高龄,活了88岁,其中儿童时期的八年在西班牙度过,而其后八十年的前半居住在美国的波士顿,最后四十年则悠游法、西、英、意等欧洲国家,最终选择“永恒之城”罗马作为终老之所。
由旧大陆而新大陆卒又返归旧大陆,可以说桑塔亚纳是位不折不扣的世界公民。
虽然他长期寓居美国,对英国文化有着由衷的喜爱,毫不讳言自己是个“亲英派”(Anglophile),而且一直采用英文笔耕不辍;但终身未婚的他亦从未改变自己的国籍,一直持有西班牙护照。对此,桑塔亚纳的解释是:“国籍和宗教就像我们对女人的爱情和忠诚,这些东西与我们的道德本质过于盘根错节,难以体面地改变,而对自由不羁的人而言,它们又是偶然之物,不值得变更。
”(《英伦独语》) 这位“自由不羁”之士于1863年12月16日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并接受天主教洗礼(尽管他实际上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他父母的感情并不融洽。1869年其母前往波士顿照看过去与前夫生育的儿女。三年后,其父奥古斯丁携小桑塔亚纳奔赴美国。
但奥古斯丁不喜欢那里的新教氛围,数月之后便只身返回西班牙,从此直至1893年去世,再未与妻子见面。 侨居美国之后,桑塔亚纳开始学习英文,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后考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深造。
从此之后,桑塔亚纳也就兼有了两个精神家园:西班牙拉丁民族的快乐主义(hedonism)以及美国的新教主义,两者之间的某种张力此后也贯穿了桑塔亚纳一生。 1889年,桑塔亚纳以关于德国哲学家洛策(Rudolf Herman Lotze,1817-1881)的论文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二十几年的哈佛执教生涯中,桑塔亚纳成了一位广受尊敬的教授,其弟子包括诗人艾略特(T. S. Elliot)、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等人。
同时,桑塔亚纳发表了大量文学与美学著述,包括《十四行诗及其它诗篇》、《美感》、五卷本巨著《理性的生活》以及《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等等。
然而,就在其声名如日中天之际,桑塔亚纳作出了一项颇为惊世骇俗的举动——辞去哈佛的教授职务。这一选择大概是出于下列原因:第一,其自然主义哲学观念的逐渐形成以及前述两个精神家园之间的紧张,使之厌倦美国的生活与文化氛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尖锐批判者,并开始与学界乃至哈佛的同事刻意地保持距离。
以致和其先前的师长、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公开交恶,后者甚至讥诮桑塔亚纳的洛策研究不过是“臻于化境的无稽之谈”(‘the perfection of rottenness’)。
其次,桑塔亚纳反感当时哈佛等美国大学的发展理念,钟情于原来类似于英国牛津与剑桥传统研修风格的哈佛学院,对哈佛的急剧膨胀和类似产业化的教研模式深感不满。
最后,此时的桑塔亚纳似已颇有积蓄,足以维持其作为自由作家的生活;而后来其母去世,更使得波士顿完全丧失了家园之感,也使他坚定了请辞的决心。
于是,才有了我国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在1968年结束西雅图大学执教生涯时,充满钦敬之情引述的那一幕: “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注:即桑塔亚纳)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
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
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 此后,桑塔亚纳便开始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流浪学者”生涯。旅居欧洲的头两年是在西班牙与法国度过。1914年7月,他由巴黎前往伦敦,并探访剑桥与牛津。
由于一战爆发,桑塔亚纳滞留英伦达五年之久,并撰述了文思隽永的随笔集《英伦独语》。在这部著作中,桑塔亚纳流露出对于英国文化与传统的深深敬意,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这部著作中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犀利抨击。
此外,还有清算德国黩武行为之文化根源的《德国哲学中的自大主义》。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留学德国期间,桑塔亚纳便已结识了约翰·罗素伯爵(Earl John Russell),这位罗素伯爵正是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两度拜相的罗素勋爵(Lord Russell)之孙,而他的弟弟便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通过约翰,桑塔亚纳得以认识包括伯特兰在内的一系列英国知识界名流。
桑塔亚纳旅欧期间的著作中,就有专门批评伯特兰·罗素早期哲学的《教条之风》,据说罗素便是在其影响下修正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尽管对英国文化有着由衷的欣赏,然而由于观察到英国有被“一股暴虐的民主洪流”吞噬的危险,桑塔亚纳最终还是离开了英国。
随后的几年中,他足迹遍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选择罗马作为落脚点,在一所女修道院度过了余年。脱离了大学教授生涯(当然,他一直都不缺乏追求者,包括哈佛、剑桥、牛津在内的多所名校都力邀其任教,但均被拒绝),桑塔亚纳得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思考与撰述,写下了众多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进一步陈述自然主义哲学主张的《怀疑主义与动物信念》、遐想自己(“陌生人”)与“苏格拉底”对谈的《地狱边缘对话录》、四卷本《存在诸领域》、《最后的清教徒》、《〈福音书〉中的基督观》,亦有对人文主义展开激烈批评的《绅士遗风的末路》以及集中体现其政治观念的《支配与权力》等。
尽管桑塔亚纳一如既往地试图远离公共生活,遁入自己内心的城堡,但至少在其有生之年,桑塔亚纳依然声名广布,他在罗马的寓所不时会出现一些高贵的访客——其盛况不下德国著名公法学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晚年寓居之所“圣卡西亚诺”(San Casciano)。
1952年9月26日,桑塔亚纳因癌症逝世。其生前遗愿之一便是葬礼不要遵循天主教的神圣奠仪,墓地也不要选在教会认可的圣地,可这样的墓址在罗马只有那些为死囚准备的坟场。
在西班牙使馆的干预下,桑塔亚纳还是被葬于坎波·维拉诺公墓,以表达对于这位终身未改国籍的西班牙哲人的某种奖掖(尽管这或许有违逝者的意愿)。 钱钟书先生喜做文字游戏,曾经在《围城》中毫不客气地将桑塔亚纳的学生、名诗人T.
S. Elliot唤作“爱利恶德”,却在《大公报》撰文盛赞桑氏,别出心裁地称其为“山潭野衲”。通观桑氏生平,这个雅致译名的确道出了他闲云野鹤、不求羁绊之哲性诗人的性格特质。
“寻得桃源好避秦”,那么,飘萍欧美、凄惶一生的桑塔亚纳所避者为何? 在其与“苏格拉底”的虚拟对话《地狱边缘对话录》(Dialogues in Limbo)中,桑塔亚纳借昔勒尼学派的阿里斯蒂卜之口说道:“我总是寓居他国,以逃离公民的苦役”。
桑塔亚纳也是个“永远的异乡人”,但他的“祖国”并不是某种政治实体,而是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从其中后期著作——尤其是封笔之作《支配与权力》(Dominations and Powers)——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以哲学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济世情怀,然而在希腊先哲“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两造之间,桑氏无疑选择了前者,更多地将哲学视为涵养性情的个人物事,这或许会让前文所述那些“美国君主党”的后生们感到不快;而其“旧世界”—“新世界”—“旧世界”或拉丁—盎格鲁撒克逊—拉丁的生命轨迹,尤其是后期常年安居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这一事实,更是让许多自由主义民主卫道士义愤填膺,进而指责他在女权与种族问题上的“政治不正确”,咒骂其反犹主义以及对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意大利墨索里尼及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同情。
实际上,在桑塔亚纳宏富的著述之中,充斥着此类矛盾与杂糅性。
即以《理性的生活》为例,桑氏认为“理性”乃是生命冲动经有效反思改造而成,“自然是理想的完美家园,而情感则是诗歌、神话与思辨的永恒沃土”,理性的生活即是冲动生活与反思生活的融会,整个人类发展史便是此种融会在社会、宗教、艺术、科学诸领域展开的一出道德戏剧。
我们足可由此看到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对峙以及“批判实在论”的折中性格。(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英美坊间流行的《理性的生活》乃是缩略本,而中译所据则为1905-06年的五卷单行本,更为原汁原味,富有可读性) 另外,如同所有堪称“经典”的文字一样,桑塔亚纳的学说也具有多种面貌或诠释的面向。
这其中有作为美学家与哲学家的桑塔亚纳,作为诗人与文学批评家的桑塔亚纳,更有站在整个西方文明传统高度对现代政治与社会展开批判性反思的政治思想家桑塔亚纳。
中文世界对于桑氏学说的绍介,迄至目前更多地展示了他的前两个面向。然而《英伦独语》以及《理性的生活》的译介,则带给中文读者一个日益丰满且更具有当代相关性的桑塔亚纳形象。
桑塔亚纳在当代受到忽视的原因,一是在于他的自然主义哲学与英美哲学界主流如分析哲学传统存在不小的抵牾之处;二是在于学界的一种偏见,即认为文字秀丽者便不可能称得上严肃的思想家。
诚然,桑塔亚纳的政治思想不为当代读者熟知,甚至完全地不合时宜,可是单凭这一点,便足见桑塔亚纳的著述蕴含了不少有益的成分,足以揭示出当今主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悖谬与局限之处。
因为桑氏的重要贡献之一,便在于力图澄清深藏于现代人潜意识之中的某种精神特质,这种特质为人们习焉不察,平时隐而不彰,却深刻地型塑着人们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思考与行为方式。
循此,欲了解桑塔亚纳的当代意义,便应当把他放在整个20世纪反思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洪流中加以把握。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以“合理化”和“除魅”这两个概念概括“现代性”及其基本困境。一方面,人类拥有达到目标的更大能力,其基础是对物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知;另一方面却是对目标的客观价值的信念消失了,人类进入了精神上的冰川期。
从海德格尔到萨特,从列奥·施特劳斯到沃格林,20世纪最伟大的西方思想家无不殚精竭虑地思考现代性的危机及其救治问题。
桑塔亚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纯粹现代与世俗的语言,重新阐发了一种对于人性的洞见,绍述了卢克莱修、圣奥古斯丁及斯宾诺莎所代表的传统。他将西方现代性视为一种正日益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根源斩断关联的工业化文明,人文主义传统在此被斵丧殆尽,并日益被一种勘天役物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虚妄(hubris)取而代之——“若是有什么政治倾向点燃我胸中怒火的话,那正是工业自由主义将所有文明贬低为某一廉价而单调模式的倾向。
”(《支配与权力》)。但桑塔亚纳有别于其他现代性批判者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以一种更为积极和富于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可能的疗救方案。 这是种怎样的方案呢?那就是:人只是这个宇宙的过客(guest),而不是主宰(master);将人们的价值观念“化主为客”,正是桑塔亚纳哲学致力的目标。
英国政治思想家诺尔·奥沙利文称其为“谦逊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modesty)——一方面是严苛的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则是自然主义、幽默感、虔敬、谦恭与超然的结合。
除掉亚里士多德、蒙田、洛克、休谟及晚近的奥克肖特之外,此种“谦逊的哲学”恰恰是西方文化较为欠缺者;也正是这种“谦逊的哲学”,足以为后现代世界提供唯一清明的智识根基。
桑塔亚纳更将其哲学运用于政治,展开对自由主义尤其是其“进步”观念的批评,试图从意识形态之中抽离出一种有限政治的理论。
过去岂能是累赘?未来怎会是一张可以任意涂抹的“好做画”的白纸?他在《英伦独语》中写道: “这场战争(指一战——笔者注)将一举歼灭人们对进步的信念,也正是时候了。进步常常是事实:先设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达到,有时我们就可能注意到一个不断向这个目标靠近的进程,就比如当一条腿被碾碎后,我们就会朝着干净利落地截肢这一目标努力。
这样的进步是一切人类技艺所渴求的。但是,笃信进步,就和相信命运和数字3一样,纯粹是种迷信,是个疯狂谵妄的想法,认为如果某种思想观念――这儿是指不断地朝着好的方向变化的观念――在某处已得到了实现,那么这一观念本身就有命中注定要在那儿实现自己的能力,而且一定也会在别的地方,甚至在事实与之相悖的地方,不动声色地实现自己。
” 早在近30年前的《理性的生活》(注意其副标题正是“人类进步诸阶段”!中译本未译出)的总纲《常识中的理性》中,桑塔亚纳便写下了下述为后世频频征引的名句: “进步的关键远不在于变化,而是依赖持存(retentiveness)。
如果变化是绝对的,这时不存在需要改进的生命,也不会确定可能进步的方向:而如果存在未被持存(比如在野蛮人那里),幼稚状态就会永远保持下去。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黑体部分为笔者自译) 以进步为枢轴,桑塔亚纳进而批评自由主义“自由”与“平等”的核心理念。他指斥“不平等者的平等便是不平等”(“ The equality of unequals is inequality.
”)他抨击现代人性的变动不居及以此为基础之“自由”的无根基性: “哲学家轻而易举就能看到,这一自由理想暗含了一种对人在世界上的各种关系的看法。它的言下之意就是:无论是神的还是自然的终极环境,或者它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的,或者是人类科学所探究不穷的;人性也是如此,或者千差万别,或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本质特征起决定作用,因人而异的个性围绕着它们随意变化。
因此,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宗教、科学、艺术或幸福的方式可以规定。对于它们永远都没有定论,甚至它们的根基也不是确定的,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它们应当是什么样的。越多的事物没有固定的本质,可任意选择,世上存在的这种自由就越多越安全,也越深入人心。
”(《英伦独语》) 桑塔亚纳对于西方文明进行了一番尼采式的“价值重估”(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的工作,试图唤起人们对于自然及历史传统的重新珍视。
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将其纳入所谓“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中。然而此种贴标签的做法毋宁会妨碍我们对于桑氏思想的整全把握。下面这则轶闻权作本文的结语,亦提请我们注意:“重新发现”桑塔亚纳,我们才刚上路。
话说《美国的保守主义智识运动》(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一书的作者乔治·纳什(George H. Nash)曾经致信沃格林,希望后者能够提供一张照片以收入书中,但后者的回信却让纳什大吃一惊——沃格林非常干脆地答复:“我的确尚未愚蠢到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愚蠢到去做一个保守主义者。
”沃格林对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诸种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因此不希望自己被简单地贴上“保守主义者”的标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桑塔亚纳身上:我们知道,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学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曾著有《保守主义心智》(The Conservative Mind)一书,并在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对桑塔亚纳多有着墨。
然而,该书的副标题却从首版的“从柏克到桑塔亚纳”(“From Burke to Santayana”)变成了后期版本的“从柏克到埃利奥特”(“From Burke to Elliot”)!
实际上,桑塔亚纳既非全然“美国”,也非纯粹“保守”,在自传《人与地》中他把自己描述成什么? ——“一个带着保守主义者假面的靡菲斯特”(a Mephistopheles masquerading as a conserv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