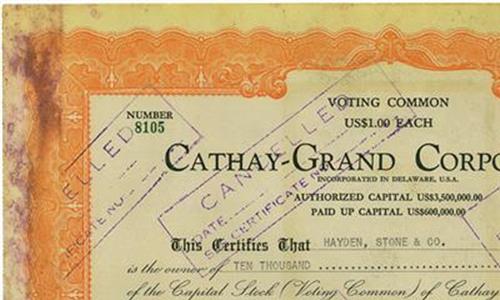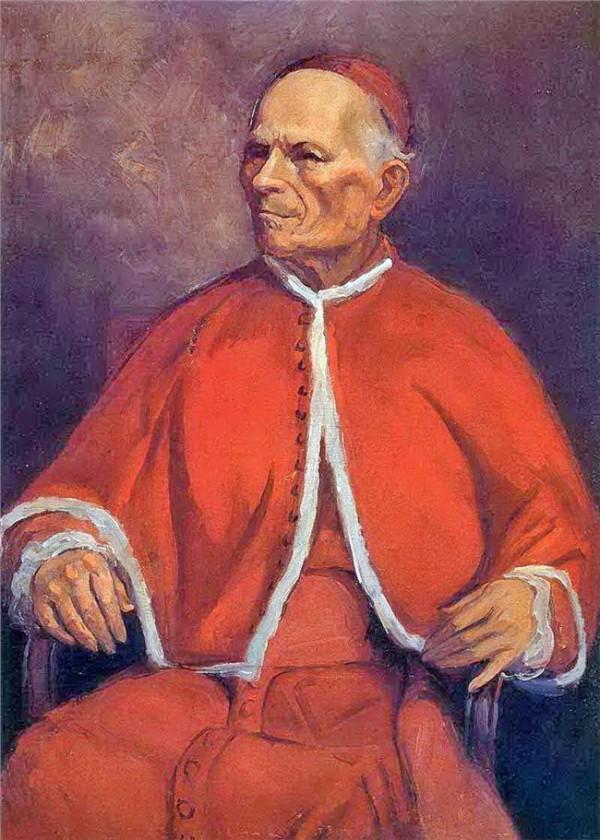潘知常反美雪 潘知常:审美回忆:生命的反刍——关于生命美学的思考
(本文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我的《生命美学》中的一节,属于年轻时写的论文,谨作为岁月的纪念)
生命是一个秘密。正象几乎所有的人都曾体味到的:在生命的原野跋涉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流逝了的生命就会变成一个秘密折磨着我们。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无以名状的秘密,又是一种痛楚的、铭心刻骨的折磨。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一生命的秘密以及这一生命的秘密所挟裹而来的折磨。
我们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是真实的吗?过去是真实的吗?? ,? … 诸如此类的疑惑粗暴地逼迫着我们,犹如人面兽身的斯芬克斯用自己的谜语逼迫着每一个疲惫不堪的还乡者。
于是,我们突然间恍然大悟:我们稀里糊涂地闯进了生命的舞台,蹦蹦跳跳地风光了一个晚上,结果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演出的是什么。于是,在一个美丽清新的早晨,我们又不能不为昨天的演出苦苦地追索着理由、价值或意义。
看来,我们还并非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确立自身在这生命的世界中的身份、如何去确立已经流逝了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不得不反复地为自己的生命辩护。为自己的过去辩护。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为自己的昨天寻找一个合法的理由,可是,这又谈何容易。
正象卡夫卡所感叹的;这作为生命秘密的过去,并不隐身于背景之中,“恰恰相反,它直瞪瞪地看着你,正因为它显而易见,我们才视而不见。日常生活才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侦探小说。
”何况,这种辩护又难免不是一个多余的、奢侈的举动,甚至一个天方夜谭般的举动。试想,从宇宙或自然的观点来看,这种辩护本身岂不就是一种令人障目结舌的疾病?而诸如理由、价俏、意义之类,岂不又统统是这种令人瞳目结舌的疾病中的吃语?由此看来,不去喋喋不休地谈论理由、价值和意义不就摆脱了这种疾病中的吃语了吗?因此,那些从来不曾念及这一辩护的人,那些从来不曾问及理由、价位和意义的人倒是很有点令人羡慕的了。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羡慕那些从来不曾念及这一辩护的生命,仍然无法羡慕那些从来不曾问及理由、价值和意义的生命。
显而易见,对于那些从来不曾为自己的生命辩护、为自己的过去辩护的人来说,理由、价值、意义之类统统是最最无聊、最最无所谓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对于已经流逝了的生命,所应该采取的举动只能是:遗忘。永远紧紧地抓住现在,就是他们的艰难选择。
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地涉人浸染着世俗的污秽的线性的时间之流,随波逐流地飘然而去又飘然而来。无端的哭、无端的笑、无端的应酬、交往、奔波、流离、无端的掠夺、占有、成功、失败? ? ? ? ,,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一切都毋须言说,他们有成千上万的理由去为现在建筑“广厦千万间”,也有成千上万的理由去拒绝为过去保留一片自由飞翔和艰难喘息的幽秘之地。
过去,在他们那里无非是炫耀的资本或者秘不示人的隐私,无非是某种可以兑换和可以作交易的祛码,无非是几张搔首弄姿的风景照片、情侣照片。
就是这样,他们很快便在现实可见的现在身上寻觅到了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每一个现实的事件的到来都不难成为行动的理由,而这种忙碌的行动本身又不难成为生命存在的理由。目标是现实的,行动是现实的,成果也是现实的,这种明白无误的现实,使人心安理得地生活在现在,并目,无限虔诚地讴歌着现在。
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过去果真就这样被“遗忘”掉了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过去并没有被“遗忘”掉,恰恰相反,倒是过去反过来逼死了现在,因而也就逼死了生命。道理十分简单,“遗忘”意味着死亡。人虽然只会死一次,“遗忘”却会使人死上无数次。
在这个意义上,“遗忘”正是“先行到死”。在“遗忘”中,人与真实的生命体验逐渐剥离开来,与源初的生存之根逐渐剥离开来,日益沉人漫无边际的死寂之地。值此时刻,生无异于死。“遗忘”之生正是“沉沦”之死。
在我看来,对于生命的误解,对于过去的误解,关键在于;对人的误解。在某些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看待物的方式去看人。因此,总是局限于人的现实存在,局限于进步与退步,占有与失去的简单二分。或者进步,或者退步,或者占有,或者失去,这样一种贫乏而又苍白的非此即彼,便构成了在看待人时全部的可怜疆域。
其实,在人的问题上,要远较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得复杂。在历史的表层事实之下,奔涌着最为深蕴、最为隐秘、最为复杂的人性长河。
就人的角度而言,人虽然象动物一样,有着把握现在的渴望,但人作为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存在,又不能象动物一样将把握现在作为唯一选择。他必须致力于超越有限的现在、企达永恒。正象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所洞查:“人本身就是具有深刻悲剧性的生物.
当他开始认识周围的生活时,他就明白有朝一日他会死去。这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一切其他的生物活着,但是不知道他们迟早终将死去。而人知道每个生命将会结束,而且知道怎样结束,这就是人所感受到的悲剧成分的根源,而这种悲剧成分永远伴随着人。
”(转引自《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 第4 页)并且,“悲剧性是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使人们精神升华,从而去思考生活的意义。”(转引自《 苏联文学》 1986年第5 期第53 页)
因此,人不可能满足于停留在同样会流逝的现在之上,而必须追寻超现在的永恒。他必须从自己的全部生命中孕育出一种东西,超越现在、超越死广:,为生命命名。否则,他就只是活死人。
如此看来,人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经验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存在。说得更准确些,永恒与意义,正是从自己的全部生命中孕育出的一种东西。它超越现在,超越死亡,为生命命名,是生活中最为真实、最为内在、最为核心的所在。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生命存在,过去——现在一一未来的线性划分是毫无意义的(详见《在时间中征服时间》)。正象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人的生命历程“是此在在生死之间的途程。
”走向生同时也就走向了死,走向结束同时也就走向了开端。人的生命历程是一条双向的存在之路。因此犹如西方的两面神的瞻前而又顾后,犹如中国的申公豹的眼睛向后,两腿向前,也犹如那个著名的哥德尔怪圈,对人来说,通向过去之路与通向未来之路必须同时敞开。
在这个意义上,叶赛宁的诗句:' ‘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腐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就未必有什么道理。相比之下,倒是克罗奇的名言更为震撼人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此,人要企达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就必须为生命辩护,为过去辩护,正象牛、羊等动物要反刍已经在胃中初步消化过的食物,人也必须反刍自己经流逝了的生命。在这方面,陆象山的论述颇为发人深省:“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栽贼之耳,放矢之耳。
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 … 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 (《 与舒西美》 )假如说,这里的“栽贼”、“放矢”指的是“遗忘”,那么,“存心、养心、求放心? 保养灌溉”又指的是什么呢?显然是“反刍”。“反刍”是生命的“为学之门,进德之地”。只有经过反刍,过去才成其为过去,生命也才成其为生命,而未经反刍的过去不是真正的过去,末经反刍的生命也不是真正的生命。
所谓“反刍’,用准确的美学范畴来表述,应该称之为:回忆。
在美学研究中,很少有人论及回忆,尤其是很少有人论及作为美学范畴的回忆。人们注意较多的只是记忆,并且,只是心理学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记忆。正象卡西尔曾经指出的:十九世纪最为卓越的生理学家之一赫林固执这样一种看法:记忆应当被看成是所有有机物的一个一般功能.
记忆不仅是有意识生命的现象,而且是所有自然生命的现象。根据这一看法,塞蒙建立起了一个一般心理学的定律:通往科学的心理学的唯一道路就是“记忆基质生物学”的道路。
“记忆基质”被塞蒙定义为一切有机物的易变性的保存原则.记忆和遗传是同一有机功能的两个方面。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刺激都在有机体上留下了一个印迹?、一个明确的生理学上的印迹,并且.有机体一切未来的反应都依赖于这些印迹的系列,依赖于有关的“印迹复合”。
不难看出,这正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关于记忆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的说明的理论根据。然而,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的记忆就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吗?在这方面,卡西尔的反洁显得十分尖锐,充满了力量: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了赫林和塞蒙的一般论点,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解释记忆在我们人类世界中的作用和意义。人类学的记忆基质或记忆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记忆理解为是一切有机物质的一个普遍功能,那仅仅意味着有机体能保存它从前的经验的某些痕迹,而且这些痕迹对它以后的反应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要使记忆这个词在人那里具有意义,仅仅有“对刺激物的以前反应的一个潜在残迹”那是不够的。单凭这些残迹的存在,单凭这些残迹的总和,并不能说明记忆的现象。
记忆包含着一个认知和识别的过程,包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观念化过程。以前的印象不仅必须被重复,而且还必须被整理和定义,被归在不同的时间瞬间上。(卡西尔《 人论》 第64 页)
再进一步,卡西尔从人类学的意义上(即本体论的意义上)推出了自己关于记忆的深刻洞见:
在人那里,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象或摹本。它与其说是在重复,不如说是往事的新生;它包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仅仅收集我们以往经验的零碎材料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回忆亦即享受组合它们,必须把它们加以组织和综合,并将它们汇总到思想的一个焦点之中。
只有这种类型的回忆才能给我们以能充分表现人类特征的记忆形态,并把它与在动物或有机生命中的所有其它现象区别开来。(同上.第65 一66 页)
应该说,卡西尔的这一看法是十分深刻的。他对记忆中“能充分表现人类特性”的回忆的强调,? 或者说,他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人所独具的回忆同一切有机生命所同具的记忆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从更为广阔的背景看,卡西尔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在中国占典美学和西方本体论美学中同样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同忆的论述,遗憾的是并未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以西方为例,柏拉图认为:回忆就是灵魂的自我轮回,就是“回到天内,回到它的家”.
“回忆就是假定知识可以离去… … 回忆就是唤起一个新的观念来代替那个离去的观念,这样就把前后的知识维系住,使它看来好象始终如一' (《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第122 页,268 页)弗洛伊德认为回忆是抵御刺激的保护场所;阿德勒认为回忆是某种激励或警告的语言;马斯洛认为回忆分占有的和存在的两种,后者是积极的活动,是以与生命悠关的活波方式进行的;雅斯贝斯把回忆作为哲学反思的本质功能之一;狄尔睽把回忆作为新的时间观的要素;马尔库塞把回忆看作否定现实的武器;尼采认为正是回忆带回了失落的感觉世界,并深情地吟咏说:“回忆!
那比我美丽的东西的回忆,―旦看见它,并且就在此刻死去!”这当然都是从人类角度对于回忆的阐释。但是,对于回忆论述得最为详细、最为典范的还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把回忆看作最高的价值器官,看作人的家园的看护神。并月相信,只有回忆才能拯救思、才能使人站出来生存:
显然.回忆绝不是心理学上证明的那种把过去牢牢把持在表象中的能力。回忆回过头来思已思过的东西。但作为缪斯的母亲,“回忆”并不是随便地去思能够被思的随便什么思的东西.回忆是对处处都要求思的那种东西的聚合。是思念之聚合。
这种聚合在敞开处处都要求被思的东西的同时,也遮蔽着这要求被思的东西,首先要求被思的就是这作为在场者和已在场的东西在每一事物中诉诸了我们的东西。回忆,众缪斯之母,回过头来去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海德格尔:《 讲演与论文集》 第136 页)
具体来说,海德格尔关于回忆的论述,最具启迪的有下述几点。首先,回忆是对“那种把过去牢牢把持在表象中的能力”的拒斥.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能力”就是“不追问在本身的真理”, 也从来不间人的本质是以什么方式属于在的真理,的能力,亦即对象之思的能力。
于是,“人就是把自己通人敞开者中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从意志上而且是完完全全地堵塞了’。(《 林中路》 )“人是无保护的”,过去也是无保护的,“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状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这样强调:“回忆就是告别尘嚣,回归到敞开的广阔之域。”其次,“回忆是对处处都要求思的那种东西的思的聚合.”那种处处都要求思的那种东西是什么呢?正是那被污染殆尽的失落了、遗忘了、漠视了的生命的意义。
回忆就是对这生命意义的“聚合”。海德格尔指出:“回忆只是彻底使我们从意愿性和意愿的对象返身回到心灵空间的最幽隐的不可见上去。… … 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心向我们打开了敞开的柴扉。
只要我们把握住内心的东西,我们也就知道外在的东西。在这内心之中,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超脱了与我们四周林立的从表面看来是保护我们的种种对象的关系。”(同上)在我看来,这里的“不可见”、“内心的东西’,都是海德格尔用他那惯用的隐晦语言直指生命的意义。
最后,回忆是“回过头来必须思的东西”,它要把所有的实在世界都悬置起来,要为所有的外在对象加上括号,回到人自身、回到与世界源初同一的生命自身、回到生命意义的显现、还原和澄明。
综上所述,从人类学(本体论)角度讲,回忆并不是心理学或认识沦意义上讲的所谓“重复过去感知过的形象”,所谓“对过去感知过的东西,通过形象的方式再现出来的一种心理活动”, 而是人企达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人为生命辩护、为过去辩护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回忆是对过去从而也是对生命的拯救。我已经分析过,人不能只占有现在,现在转瞬即逝,假如没有过去,假如过去已丧失殆尽,那么现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假如过去得不到拯救,那么现在也得不到拯救,而且,人的整个生命也得不到拯救。
既然如此,过去怎样才能被拯救呢?在我看来,只有在回忆中才能被拯救。回忆,只有回忆,担当着拯救被现在遗忘的过去的天命。它是呼唤者,呼唤着这个世界上无名和失名的东西、应该有而又没有的东西,它是转换者,把陷人历史迷误中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沦人占有的生命转换成怡然澄明的生命。
要强调的是,回忆之所以能够拯救过去、拯救生命,除了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上述三点内在规定外,还有其更为根本、更为源初也更为核心的根据。这就是:回忆能够把过去从实在内容中剥离出来,赋予过去一种意义、一种形式,从而为过去命名。
为什么呢?这正折射出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的深刻差异.就人而言,他的世界既是物理的又是意义的.人的物理世界象动物的物理世界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不可能重建,也不可能在纯物理的意义上使之再生。
人的意义世界却是一个人所独具的世界,它以物理世界为媒介,但却并非物理世界本身,(参见我的《 美是自由的境界)) ) ,而直接关联着人的生命中最为内在的东西和最为真实的东茜。它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形式世界,不是可见的世界而是不可见的世界。
它是生命创造的切入,是实在与形式的交换,是意义的回溯、拓展、凝聚与深化,是永恒的瞬间生成。毋庸置疑,这个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是不允遗弃也不能遗弃的。一旦遗弃,人灵就会漫世飘飞、惶惶然无家可归.而回忆之所以能够拯救过去、拯救生命,之所以能够把过去从实在内容中剥离出来、赋予过去一种意义、一种形式,并且为过去命名,正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物理的世界。
因此,回忆正是对过去的重建。它通过与过去的不断的对话、交流,使之聚合为“活的形式”, (本节所说的“形式”或“活的形式”,均指生命意义的感性造型。)从而不致再次消失在线性的历史之流中,不致再次因循旧态,成为虚幻的和遮蔽的。
于是,过去就有了另一种模式,不再仅仅是一个后果。?‘我们有过经验,但未抓住意义,面对意义的探索恢复了经验’。(艾略特)流失的过去在回忆中被赎回,被给予一种形式,成为普鲁斯特所谓的“追回的时光”,成为活的形式,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神话的人类学意义可以得到应有的肯定,神话中被小心翼翼地在吟咏中保护下来的过去,显然并非僵化了的历史事实,而是作为源头活水的活的形式。列维一布留尔在《 原始思维》 中对原始人“既是十分准确的,又是含有极大情感性的”回忆曾深表惊叹。
并转述罗特的所见所闻说,他亲自听一个原始部族花了五天五夜演唱他们民族的历史。令他不解的是,他们虽然唱得惊人的准确,但却无人讲得清歌词的具体内容。
今天看来,这歌中所吟咏的很可能并非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是他们对过去的一种理解、一种阐释,或者说,所吟咏的很可能是他们赋予过去的一种意义、一种形式。在我看来,所有的神活都可以而且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解读。
进而言之,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碰到类似的情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发现: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所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而且还诗化了回亿。
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于很悲惨的现实的以及很粗野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成更美丽、更艺术的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 第2 卷第275 一276 页)这其实正是回忆对于过去的实在内容的剥离的真实写照。
从表面上看,是时间“诗化了回忆”,实际上,则是回忆“诗化了”过去。所谓“更美丽、更艺术”,也正意味着过去从流逝走向重建,从实在内容走向活的形式。众所周知,歌德把他的著名自传命名为《 诗与真》 。
诗中有真,真中有诗,歌德为什么这样作呢?显然并非要为自己的过去追加一点虚幻的色彩,而是要从诗的、亦即形式的角度来重建自已的过去。同样是这个歌德,在一封信中曾经盛赞赫尔德。
歌德说,他在赫尔德的历史叙述中所看到的不再是那个作为“人类的表皮外壳”的僵死过去,而是过去的再生。因此,歌德极度钦佩赫尔德对于过去的“清扫法”: “不仅仅只是从垃圾中淘出金子,而是使垃圾本身再生为活的作物。”(《 书信集》 第2 卷第262 页)不难看出,这里的“清扫法”正是我们所说的回忆。
弄清了回忆的更为根本、更为源初也更为核心的根据,回忆的美学意义也就不难弄清了。在我看来,回忆正是人类自由的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象前面所讲的,生命本来是一个全面、丰富的整体、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经验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却被分割、剖解了。
对于现实的存在、经验的存在的片面推崇,把人带离了自己的根,抛舍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法则,致使人只知钱是什么、权是什么、电冰箱和洗衣机是什么,却不知何为真挚的爱、何为祟高的信仰、何为情感的幽秘、何为人生灼天命、何为灵魂的归宿… … 从这种纷扰的现实喧嚣中脱身而去,要靠回忆,正象诗人吟咏的: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我迄今对少年时代读过吴伯箫先生的名作《 歌声》 记忆犹新。.吴先生在作品中对峥嵘岁月中那感人的歌声给他的影响所作的描述何等动人:
感人的歌声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欲畏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路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 … 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会一幕幕放映起来。
在这里,过去的歌声显然已经不仅仅是歌声,而成为生命意义的聚合。它象征着对过去的一种理解,并且正是因为这种理解,歌声被融化在生命之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托尔斯泰关于母亲的回忆也是很好的例子。他曾经充满深情地陈述说:“无比幸福而又长逝不迫的童年时光!… 我怎能不热爱、不珍惜有关你的一切回忆!这些回忆照亮和提高了我的精神境界,是我幸福欢乐的源泉。’这正是对回忆的美学意义的揭示,在母爱中,托尔斯泰找到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它是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给人以活力,给人以灵感,给人以安宁,给人以温馨,甚至使人可能终老于此。
难怪康? 洛穆诺夫要如此评价:“他的天性中最美好、最纯洁的特点也是和这种回忆紧相联系的。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回忆是人性的富矿、生命的富矿。因此,在回忆之谜中蕴含着生命之谜.回忆即生命.回忆使人返本探源、? 寻回自己的本真,重返深远源初的根基、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据。早已在井然有序的平静生活中死寂的生命,突然被激活了,一度狭小、充盈险阻阴冷而又晦暗无光的天地再一次变得宽敞、明亮而又畅通无阻。
余光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与一座颇具原始风味的大山的宏大无比的约会,假如我们把这大山看成人类生命意义的聚合,那么.这约会给我们的启迪就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山,在那上面等他.从一切历书以前,峻峻然,巍巍然,从五行到八卦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
树,在那上面等他。从汉时云泰时月从战国的鼓声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此鱿蟠蟠,那原始林、那太阳,在那上面等他。赫赫洪洪荒荒。太阳就在玉山背后。新铸的古铜锣,哐地一声鼓响,天一下就亮了。
这个约会太大,大得有点象宗教。一边是,山、森林、太阳,另一边,仅仅是他。
就是这样,回忆推动着人从沉沦的背景上场,肩负起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使命,进人生命之旅、自由之旅、创造之旅。而且,既然回忆是人类自由的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在回忆中凸现的就并非简单的生命历程或生命故事,而是超迈于这一切的生命永恒和人类的普遍价值。
在回忆中,人类通过认可过去中所蕴含的永恒意蕴和活的形式,从而使生命得以全面呈现。因此,马尔库塞才认为:“同忆并不是一种对昔日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这种时代从未存在过),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对原始人等等的记忆口倒不如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能,是一种综合,即把在被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断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
就此而言,理由的一段话很有点美学意味:“我的记忆象是不严密的筛子,总是容易漏掉那些不愉快的东西,反射出淡盔色的色彩。”而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已对童年时代的水乡经历和故居后院的那些名不符实的回忆时所说的一段话,就也可以作为美学论文来阅读了:“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们时时反顾… … 然而现在我只记得是这样。
”确实,这种在回忆中对过去的物理世界和实在内容的误读,有助于我们更加生动地理解在回忆中物理世界和实在内容的作为媒介和意义世界和活的形式的作为对象这一根本特性。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回忆不仅与审美活动关系密切,而且与在审美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创作活动密切相关。在创作活动的研究方面,应该说,在对回忆问题的研究上比美学界更为深人的压研究主要体现在“情绪记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上。但也应看到, ’情绪记忆”的研究毕竟无法等同于对回忆的研究。相比之下,后者是本体论的,前者却只是心理学的;后者才是范畴性的,前者却只是概念性的。
具体来看,正象巴乌斯托夫斯基指出的: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金蔷薇》 )确实如此,我们经常强调作家在创作时要“休验生活”, “积累生活”,然而,创作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呢?似乎没有.
仍然是即使都占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还是有人能写出不朽之作,有人却只能写出三流四流甚至不能人流的作品。为什么呢?看来,问题必然涉及到对回忆的美学理解。
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否写必真正的作品,关键并不在于占有生活阅历的多少,而在于能否对过去的一切保持“诗意的理解”:能否对过去的一切加以反刍,能否对过去的一切赋予一种最为深刻同时又最为独到的活的形式。
王履《 华山图序》 中说:“既图矣(指实地写生),意犹未满,由是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一日燕居,闻鼓吹过门,怵然而作日:‘得之矣夫’。
遂靡旧而重图之。”王履不断追寻并且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正是从过去的实在内容中剥离而出的活的形式,也正是以过去的物理世界为媒介重建的生命的意义世界.这样看来,作家在创作中寻找的主要并不是一些情绪性的生活阅历,而是寻找对于过去的? 诗意的理解”,寻找最适宜于显现这一“诗意的理解”的生活的实在内容,寻找以鲜活的实在内容作为媒介去理解和解释过去和生命的最佳形式。
以普鲁斯特为例:三十六岁以后,由于瘤疾哮喘病日益严重,他不得不把自己囚禁在严密封闭的房间之中。怕吹风、怕见阳光、怕室外的噪音,甚至怕宝外的花草香味… … 这使他在十五年内足不出户,不但门窗紧闭,窗上挂着厚厚的帷幕,而且墙上、楼板上、天花板上,都贴上一层厚厚的软木片。
不难想见,这哪里是病室,这简直是坟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普兽斯特追忆着过去的三十六年的时光,写下了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品《 追忆逝水年华》。
于是,间题就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究竟是被幽禁在病室中的普鲁斯特的生命是真实的?还是当时那些在世俗的泥淖中奔走甚至打滚的世人的生命是真实的?进而言之,究竟是普鲁斯特在回忆基础上的创作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在东拼西凑基础上的创作是真实的?显而易见,普鲁斯特的生命和创作是真实的。
这个“奇怪的孩子”虽然与世隔绝,无法涉足现实,但却不甘毁灭、更不甘沉沦,他反复追忆着逝去的年华,寻觅着其中的意义和活的形式,因此而进人永恒,并且涉足真实的生命,创作出不朽的名篇。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确实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三十六年的平淡无奇的生活阅历,经过普鲁斯特的反刍,竟然酿成艺术琼浆。在此意义上,傅雷的话讲得更为透辟:真正的艺术家、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多半是在回想和想象中过他的感情生活的。唯其能把感情生活升华,才给人类留下这许多杰作。(《 傅雷家书》 第123 页)
但愿我们的作家和理论家都能牢牢记取这句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