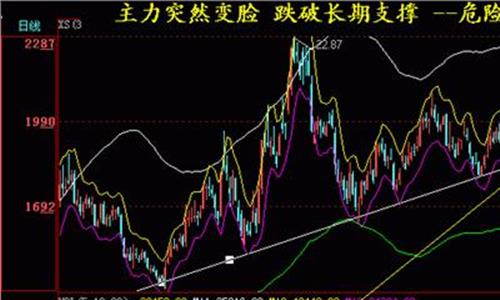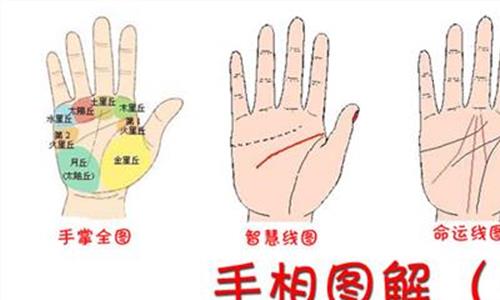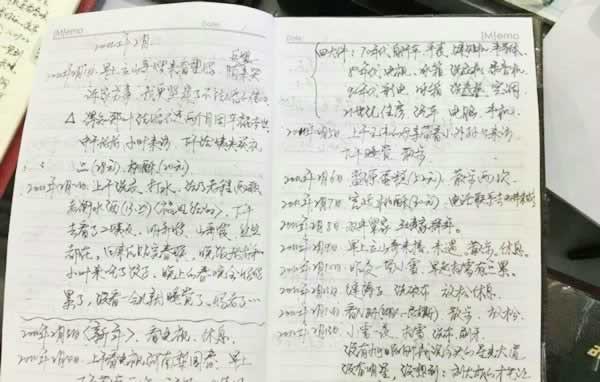那个男人手干净得让我一生难忘 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新的渴望
透过新鲁院四楼明几的窗子,可以看见湛蓝的天空以及天空下长高的楼群。书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籍,其中我写的六部小说也夹杂其中,它们阶梯一样排列在一起,构筑起一个向上的趋势。
我的手还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给我的思维施工一条路,这使得手成为我生命里最富表情的背景,超过了笑容。就像十四岁那年,在江边,我见到的第一双城市的手——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的一扇门。
十四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从学生一跃成了农民。有一天早上,我在江边洗衣服,迎面的铁船上下来一位穿着花衬衫的男青年,这个青年满头卷发,优雅地迈着江心洲从不曾见过的步子,向我走来。他有一双漫不经心的眼睛以及一幅有郁郁寡欢的神情,许多年过去后,一想到城市人,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他那张淡淡哀怨的脸。我停止洗衣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最为吸引我的还是他那双摆动着的手。我留意到那双手手指修长,手背上的皮肤白皙干净,指甲修剪得短而整齐,后来我知道,他是因为失恋心情不好,到江心洲来散心的,我早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城市”,而如果我们要到达那个地方,考上大学是爬出江心洲这口深井的惟一一条绳子,所有的乡下孩子都有爬出这口井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是朦胧的、无形的,直到见到这个真正的城市人后那种隐隐约约的渴望突然涌上了喉咙。我在瞬间才确定这世上有一种人跟我们截然不同:他们长得干干净净,在我们弯腰驼背或汗流浃背的时候,他们迈着悠闲的步子在江滩上散心。
我伸出自己的手。那是怎样一双手啊,我十四岁的手心全是厚茧,手背因为在水里浸泡太久,肿胀发红。手指因为握锄而粗大,指甲里也藏污纳垢,酸楚和自卑一瞬间紧紧的裹挟了我,我深深地低下头,没有敢再打量他一眼。
那天晚上,我开始盘算怎么样脱离这种生活。我开始趴在小桌子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一笔一画地临贴。我听说临村有个男孩子因为字写得好去了北京。许多洁白的纸被我写黑了,许多衣裳上沾上了墨汁,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有去北京的可能,三个月之后,我母亲断然不再允许我做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我书法家的旅程戛然而止。
后来我写诗。我把诗寄到上海的《文学报》。一位叫李连泰的编辑给我回信。他说,这诗太白了,有想法,但不够。
邮递员每周送一次信到村里的学校。妹妹拿着信飞舞着奔向我的时候,她把“上海”带到我的手上,很快我们全村都知道我收到了城里人的来信,他们不在乎你收到的是不是退稿信,他们只知道你和上海联结上了。
这时候,写作仅仅是为了发泄。
十八岁那年我进了城,在服装厂做缝纫工。身边不时出现真正的有着干净指甲缝以及白皙手背的城里人,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但无形的墙竖在那里,我们从来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相反,那段日子,我倒是常常留意到在女工宿舍围墙外的年轻男孩们。他们盲目地等在工厂外,穿着沾满了洗不脱泥浆的衣裳,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手污迹斑斑,因为砖块和钢筋,污渍渗透进皮肤,以及太阳底下一日又一日的暴晒,他们的手背青筋暴突,跟他们的年龄严重不符,清晰地暴露着他们的来处,不能使人多加幻想。他们敏锐地嗅到和他们同一来处的姑娘们的地盘,每天晚上盲目而耐心地等在外头,偶尔有个别大胆的,壮着胆子朝着女工的窗台喊:
姑娘啊,妹妹啊,下来逛逛吧!
一日又一日,不停地有人放弃,亦有人跟进。除了保安过来恫吓几声之外,鲜有姑娘回应。
意外的是,手持电筒的保安在吓走外人之后,仰起和民工们一样的头颅,对着姑娘们的窗台轻声地呼喊:
姑娘啊,妹妹啊!
然后也迅速逃去。
后来我遇到许多双类似的手,街边摆点心的大婶、修鞋的大叔,跟我年纪一般大的钟点工,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都淋漓尽致地写在他们的手上。
同样的境遇使我对他们深感同情,我看到他们孤寂的漫漫长夜以及我自己的长夜孤寂。我忽视他们的唐突、粗俗,只发现他们粗糙的手以及那些手所承载的重量。那时我的文章里对城市充满了敌意。发表在当地日报上的散文和杂文,每一句都幼稚地尖锐地摆着战斗者的架势。
这个时期的写作是对命运不平的揭示,我们对浅表性的不公耿耿于怀,自以为保持战斗姿势是惟一的选择。我的作品没有诗意,紧张、不安,这种委屈和躁动如实地反映在当时的每一部作品中。
再后来,我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公司,我握过许多双形态各异的手,每双手都有自己的特质。或温暖或冰凉,或友善或敌意,有的手毫无诚意,有的手满是故事。我见过一位医术精湛的脑外科医生的手,掌心肥厚、骨节粗大,爬满了黑毛,但他用他的医术享誉整个城市;我也见过一位五十多岁的领导,他长着一双绵软无骨的手,一经接触,不可遏制地使我产生一种错觉,这个人一定温柔随和,然而不,这是一位真正在我的职场将我打败的人。我任职过的一位大公司的董事长,长着一双比农民还农民的手,然而他的手的确只用来签名和握手。我也见过一位缺手的年轻人,嘴里叼着毛笔在纸上写字,倔强地想写出一条新路来。
一双手就是一个舞台。正是这些形态各异的手增加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阅历,使我逐渐成熟。我内心的敌意以及泾渭分明的判别开始淡化。我的写作开始走向“担当”。除了发泄,除了不满之外,我还在思考种种现象背后的问题。这时,我已快三十岁了。
紧接着,我生了病。绚烂之后平淡光临,飞速向前的世界关在了门外。年华最好时的静止,带我重新进入了全新的地带。前,是缥然一片,后,已是回不去的故乡。
在养息中,过去悄然回访。这世上的真相一层一层每天被时间和空间覆盖着不见天日,这世上有许多人都不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真相,这还是次要的,他甚至不了解自己身上的真相,自己性格的真相,自己需求的真相。惟有那些写满了故事的手留在记忆深处,将我的意识一一唤醒。近十年来,我与我的手相依为命,我身体最糟糕时,不能坐,不能站,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那无力的双手握着铅笔写出了一行行字,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由此开启的新的门。
站得愈高,愈知自身卑微;
走得愈远,愈晓山险水深。
这八年来,我写了七部长篇小说,发表六次,出版五次。换句话说,我在文学界共抛头露面十一次,很显然,我被关注和阅读的机会也仅有这么几回;更糟糕的是,每写完一部小说,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没有脸再翻开。人最可怕的是生命中不可抹煞的过程被否定,人最可贵的是勇敢地否定自己,最重要的是,否定之后仍旧重新出发。
不是所有的探求都有结果,但所有的结果都必然是漫长的探求而来。
我欣喜的发现,正是这些现象,体现了我的纯度。写作虽是有计划的行为,如同在野外开车,方向盘怎么打,陷坑怎么避,油门怎么加,每一个动作都能产生种种意外的后果。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每个阶段老老实实地忠实于自己的思想、见识、境界和情怀。写作者既是一个操纵者,也是一个被操纵者,有时,他主宰了主人公的命运,而另些时候,他被裹挟向前,带着岁月的温度。
我们的理想和认识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在探求中重新确立。此后我的作品开始有了新的意味。我明白写作关乎涵养、经历、气质、趣味和胸怀。我不再刻意追求对立,而是担当。我的写作也渐显自身的个性,写作不再是简单的发泄和发问,写作更是对时间的挽留,对世事的洞见,写作,更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
纵然怀着理想,不一定能到达理想的所在。
此刻,我端祥着自己的手。细腻、白嫩,老茧褪去,显然轻易看不出来路。正是生活,正是在我的少年时期遇到的那双与我截然不同的手对我的刺激,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新的渴望,以至我喜欢通过人的手发现生活对他的打磨,也正是对千千万万双手的不同角度的观摩和发现,使我的手摆脱了它以往的模样,摆脱了它原有的命运,有了新的形象和使命。然而,我记得我十四岁那年见到的那位不知道名字如今显然已是中年的男人的手,以及我所见过的每一双手。我为它们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