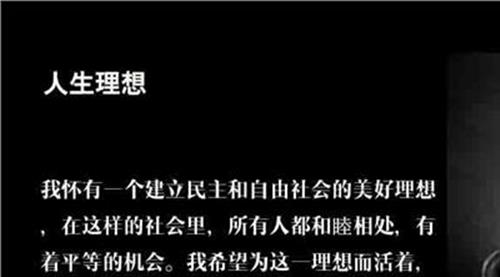曼德拉与黄家驹:穿越二十年的祭文
17岁时,他捡到邻居搬家剩下的一把吉他,从此如痴如醉。他想唱歌给世人听。
他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在醉生梦死的香港,摇滚乐是边缘地带。人们更习惯听男声女腔的歌手唱那缠绵不休的情歌。黄家驹不喜欢,他希望音乐能传递更多力量。
乐队组建后,几个年轻人在奶茶店畅谈理想。因为没钱,每次只点一杯奶茶,奶茶越冲越淡,最后已经不看不到颜色。
黄家驹从家里借出几百元,开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从搭建舞台到绘制海报亲力亲为。他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假借在街头做音乐调查,实际上是推销演唱会门票。票价很低,仅仅10元。
从一场场地下音乐会启程,beyond开始书写自己的神话。然而最初,组建乐队在外人眼中只是一个笑话,
黄家驹和同伴辞去工作,四个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内。每天只是练习音乐,没钱吃饭,便靠面包充饥。吉他琴弦断了,也只能凑合继续弹。
“父母觉得搞这些是没有前途的,不如找一份踏实的工作,父母问我想成为谁,我答不出,但是我不能没有音乐,总之没有音乐我会死。”
3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曼德拉从来没绝望地等待死亡。在罗本岛,漫长的抗争之后,曼德拉甚至拥有了一个小小的菜园。狱墙边的泥土中,番茄和洋葱放肆生长,享受着阳光的味道。
他一点点照亮周遭晦暗的世界。他给麻木的囚徒布道,为他们勾勒未来崭新的南非;他安慰家属遇难的白人狱警,听狱警倾诉悲伤,甚至在多年后,成为狱警孩子的教父。
他的影响力从栅栏之中远远扩散开去。他的一举一动成为世界焦点。1981年,1万余名法国人联名向南非驻法使馆发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全球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50多个城市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英国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恢复曼德拉自由。
1990年2月11日,波尔斯摩尔监狱门前,乌压压的人群焦急守候。这一天,是曼德拉的释放日。他走出铁门,迟疑片刻之后,高举右拳,欢呼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的眼睛在罗本岛上时被石灰刺伤,害怕闪光灯的光亮,但面对期待的人群,他还是坚持说完了斗士的宣言。
“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让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那一年,曼德拉71岁,他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4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22岁那年,黄家驹的音乐征途也开始起步。终于有经济公司和beyond签约,但只是看中乐队成员的青春外形,对他们的音乐并不认可。1985年,黄家驹和同伴用打工的钱自费出了第一张专辑《再见理想》。
黄家驹从未和理想再见,哪怕嘲讽和指责如影随形。一片情歌声中,他的目光始终在更广阔之初。
1988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黄家驹以时政为背景创作了歌曲《大地》, “我会比较留意社会时事,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没感觉,但听到外国的新闻,如战争或政治问题,我会留意,别人未必有兴趣,我会很自然去关心感觉它。”
《大地》很快走红。此后,黄家驹的琴弦上,一首首批判现实或传递亲情的金曲陆续诞生,beyond也最终坐在了香港乐坛的第一排。
成名之后,黄家驹开始了与商业模式的长久抗争。无休止的颁奖典礼,无休止的出版限制,歌迷疯狂的追捧,娱乐节目和电影导演的一再邀请让他感觉痛苦。“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班人,你在谈论音乐,周围人在聊化妆品,购物和跑车,虽然不情愿沦为别人的赚钱工具,但是也渐渐明白这就是这里的生存法则,每当回到band房,已经精疲力尽,但我们至少还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重拾自我。”
那个时代,香港正处于彷徨的十字路口,对回归的恐慌引发移民浪潮。殖民政府对时局的神经长期绷紧。打压的阴影笼罩着黄家驹。
“我们只是有话要说,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我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没有谁对谁错,我们做音乐从来不是为了要打倒谁,但是要我装聋作哑的去扮偶像歌手,我反而更辛苦。”
他从不屈服。1991年,beyong终于登上香港最著名的红馆舞台。在台上,抱着吉他的他说:“我们beyond永远会弹奏到手指不会弹为止,坚持我们,坚持乐队的信念。”
可是,无休止的商业炒作占用着他的创作空间。当时歌手为了成名,只能到电视节目中扮演小丑。失望之余,黄家驹说了那句名言:“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
同行因此猛烈抨击,他不为所动,“只要身为音乐人,便有资格发表意见。”
他的眼界早已不限于狭小的海湾。1990年,他和慈善团体前往非洲,并创作了著名的《Amani》,祈福世界和平。歌声永别于凌厉的批判,带着温暖的颜色。
他说,音乐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光只有愤怒。
5“可否不分肤色的界线,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愤怒从来不是曼德拉的抗争手段。他习惯用隐忍和宽恕对抗不公的世界。
“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多年之后,他举办画展,展示在狱中的蜡笔画作。画作从不用“黑暗、阴沉”的颜色,只有用鲜艳轻快涂抹出的乐观。
出狱后,他为缝合肤色间的裂痕四处奔走。他在贫民窟前演讲,在白人警局前演讲,在暴乱的现场演讲,直到站在总统的讲台前。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5月11日,他宣誓就职。
宣誓当天,除了各国政要,还有几位特殊来宾。他们是罗本岛上的白人看守,曾对曼德拉殴打虐待。
然而,曼德拉将他们邀请到了就职现场,并在演讲前起身向他们致敬。世界在那一刻,变得如此安静。
就职演说中,他说:“……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人民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此刻起,曼德拉的理想变成现实。崭新的非洲开始迎接世界的审视。无人能及的声望,让他本有望连任总统,但1996年新宪法通过后,曼德拉明确表示不谋求连任非国大主席,并将在1999年任期届满时辞去总统职务。
比对抗牢狱岁月更艰难的是拒绝诱惑。但曼德拉很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追求的平等和自由已深入人心。
退休后,他投身公益,创办儿童基金,展开艾滋病预防运动,并成功推动南非举办足球世界杯。
他拒绝神化自己,“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
年轻时,他曾参加过拳击比赛。他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成为一名世界级拳击冠军。事实上,作为斗士,在命运的舞台上,他早已没有敌手。
晚年岁月中,他有时会讲起出狱那一刻的心情,“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们能接受生命中的挑战,连最奇异的梦想都可实现!”
6“缤纷色彩显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我很佩服曼德拉,20多年的牢狱,不知他怎样耐过这段孤独岁月,但我知道一定有坚强的信念支撑他。在香港做音乐,做乐队很难,很孤独,这条路注定是long way without friends(乐队早期一首作品),我这辈子不会转行去干别的,就是做音乐了,我亦相信人定胜天的,终将有那一天……”
1990年,曼德拉出狱,黄家驹为此写了著名的《光辉岁月》。面对媒体时,他如是评点他和曼德拉的关联。
那一年,黄家驹正被鲜花和掌声簇拥,可是他并不开心。
香港乐坛并不尊重音乐,到处充斥着翻唱歌曲,“哪里有音乐,都是商业,音乐只是用来赚钱的,音乐人和乐队根本就是没地位的,你看看每年获奖的都是什么人,都是红艺人,唱两年歌就去拍电影了,谁还管什么音乐的好坏?”
一度,beyong试图去适应这种法则,“做的久了,半夜会惊醒,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音乐人,还是一只鸡?那时beyond获奖无数,但是最高潮并非在颁奖礼上,而是在我们的band房,一个个XX最佳团体的奖杯,被棒球棍砸为几截,然后丢到垃圾箱里,那一刻,我们才重拾自尊。”
黄家驹将他的音乐定义为革命。当革命的脚步受阻,他选择突围。
1992年,beyong转战日本发展。一切又回到创业初的景象。1993年,迫于发展,黄家驹参加了一档日本游戏节目。因不慎坠落,匆匆离世。天才的音弦就此崩断。
他倒在了向自由朝圣的路上,但他的理想并未因死亡而消散。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摇滚音乐注入香港乐坛,他所传递的精神也被更多人铭记。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许许多多的奖项追加给这位死时只有31岁的年轻人。一代代歌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他致敬。
每逢周年,香港地铁内总会张贴印有大大“驹歌”的海报。海报下有一行小字,“我们都是听他的歌声长大的”。
许多年后,beyond剩余的歌手谈起他们的兄长:“有时会想,如果家驹活到现在,面对如今的乐坛他会怎么做?哪怕再无助,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到底,因为那就是他。”
黄家驹的墓地安置在香港将军澳的山头上,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生命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做过什么。”
7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2010年,南非世界杯召开。央视在转播开幕式时,特意播放了那首《光辉岁月》。主持人说:“据说中国使馆的朋友曾拿这首歌给曼德拉听,并把歌词内容翻译给他,老人听完不禁动容。”
此时,距离黄家驹辞世已有17年。许多90后开始哼唱他的歌。他们或许不知道《光辉岁月》和曼德拉的关联,但并不妨碍理解歌声的内涵——那是曼德拉和黄家驹追求一生的平等和自由。
2013年这一天,我们送别曼德拉。与斗士的告别,其实无需哀伤。只要相信他们所坚守的信念,他们将永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