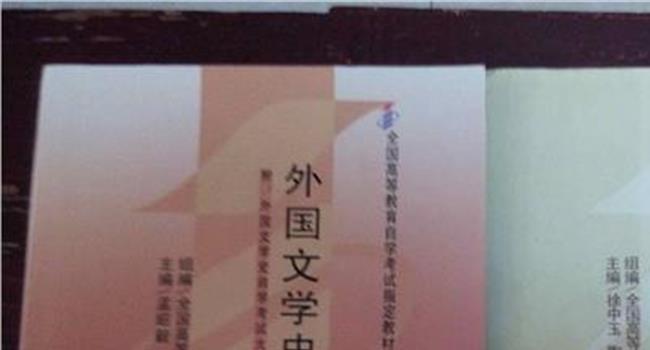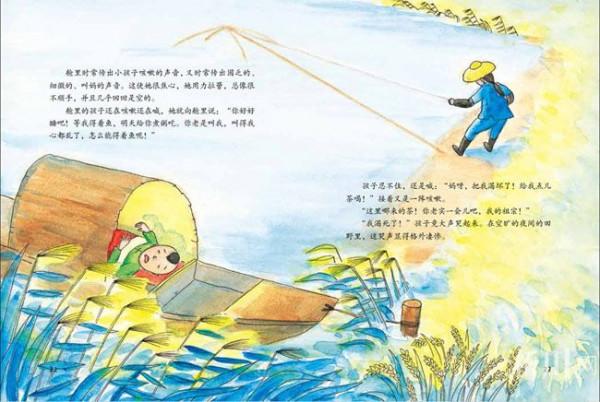黄蓓佳儿童文学作品 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
黄蓓佳,作家。1955年6月27日出生于如皋,在泰兴长大。1973年1月毕业于江苏省黄桥中学,1974年下乡插队,期间曾借调《雨花》杂志社工作。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2年毕业被分配至江苏省外事办公室工作。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底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室主任,民进江苏省文化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江苏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筚路蓝缕 17岁就踏入文学之门的黄蓓佳,从1973年在上海《朝霞》丛刊发表处女作《补考》起,至今发表《黄蓓佳文集》等小说、散文随笔、儿童文学、影视剧本三十多部、六百余万字。
曾两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全国少儿图书奖等国家级奖项,以及部委、省市、报刊各种文学奖多个。
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曾获得两次国际大奖、全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俄、英、德等国文字。 如今提到黄蓓佳的名字,常常会被冠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头衔,这与黄蓓佳囊括了全国性的各种儿童文学奖项有关。
黄蓓佳说,写儿童文学实际上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过渡,而成人文学给我的空间更大,创作的自由度也更大,更能够表达我内心的很多东西。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黄:我走上文学之路完全是偶然,写,不是我的主动行为,发表也不是我的主动行为。
我的处女作应该是1972年的《补考》,1973年发表在上海《朝霞》丛刊上,发表、写作都是第一篇。当时才17岁,中学生,完全是糊里糊涂的,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发表的。
问:大概是怎样一个过程? 黄:当时我在黄桥中学,我们中学举办征文比赛,我参加了,我写得比较长,而且它具备了一个小说的特征,就是已经超越了中学生作文的范畴,然后我们班主任就非常欣赏,把它贴到了学校的宣传橱窗里面。
后来大概是泰兴文化馆的人到我们学校去干什么事情,偶然看到这篇东西,就把它要走了。当时“文革”期间泰兴有一个铅印的小册子,叫《革命文艺》,后来就在这上面发表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扬州地区也有一个地区级的“革命文艺”,它从各个县里面选,就把这篇选上了。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结果第二年,很出乎意外的,我收到了上海《朝霞》丛刊寄来的印得很漂亮的书。
当年泰兴文化馆有个辅导业余创作的上海人,叫唐燕能,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文革”当中分到泰兴文化馆,后来据他说,是他把这篇作品送到上海的,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撞着了。
问:作品发表之后,对你触动一定很大的。 黄:发表出来的时候,我正高中毕业,面临着插队,父亲就跟我讲,说你既然有了这个蛮好的开端,不如继续写下去,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出路吧。
所以当时写东西,完全就是为了插队以后能够早点把工作调到城里来,是抱着这样一个非常功利的目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文学,或者有文学才能,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我抓住了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
问:当时的文学环境是怎样的? 黄:那个时候就是“三突出”的八个样板戏,然后就是浩然的《艳阳天》系列,以及很少的几部长篇小说,我的范本基本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的作品,里面无论是人物,还是情景的描写、背景描写,甚至语言,完全都是北方味的,比如说我们都是俺们。
然后父亲就嘲笑我,说你怎么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浩然味的?当时完全就是一种摹仿啊。 问:考进北京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 黄:进入北大以后,随着《班主任》和《伤痕》发表,我们班上很多有志于文学的学生都非常震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还可以写伤痕,还可以揭露阴暗的东西,写悲剧性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脑子里面原来没有的,所以,很长时间里,大家都处于一种焦灼和迷茫当中。
问:就是知道别人的好,自己也想学,但受的那种教育根深蒂固,一下子转换不了。 黄:是啊,一下子找不到自己应该走的路,所以我就转过来写儿童文学,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吧,我主要的力量就放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上,那段时间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的很多,读我小说的人也很多。
问:其实北大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无论是思想潮流和文学潮流,它都是处在最前端的。
黄: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刚刚开禁,一下子传播进中国,我们也是最早接受到这些新鲜的东西,第一时间就能读到最早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
当时各种各样大量涌进来的思潮,和我们原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奇异的冲突,所以我一方面在写儿童文学,一方面也不甘心放弃成人文学的创作。当时我受美国作家欧茨的影响比较多一些,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我基本上就是一种文风。
问:浪漫主义的文风? 黄:说浪漫主义也不全对,不光是浪漫主义,还比较新潮,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如果放在现在那就是一种时尚的写作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的很多东西,包括《请和我同行》、《去年冬天在郊外》等等,一大批写青年知识分子、写大学生生活的,都比较前卫,也是比较浪漫的,那时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嘛。
然后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自己走上社会,结婚成家,年龄在增长,社会阅历各方面都在增长,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那种完全写个人感情的很浪漫的风格不适合我了,这时我的文风发生了转变:从浪漫的转为比较现实的,从个人情感转为关注社会。
问:有评论说你的中篇小说《玫瑰房间》是由“梦幻”文体转向冷静现实的叙述文体的一个转折。 黄:其实这种转变不是从《玫瑰房间》开始的,我觉得应该是从发表在《文汇月刊》的中篇小说《冬之旅》开始的,然后《玫瑰房间》可能是完成了这个转变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年代,是我中篇小说发表最多的时候,中篇的创作比较旺盛,从90年代后期开始,基本上我就不大写中篇,短篇尤其不写了,主要就是写长篇。
因为每个作家对文学创作的体裁都有其适应性,在各种文体都尝试以后,我发现我写长篇的时候,感觉非常舒服,最得心应手,这个尺度最适合我的创作。
问:有一段文字,说你曾经讲过,喜欢叙写20世纪70年代那种缓慢的调子,说这种是你最擅长的? 黄:可能我说过这话,我有不少写的都是那种的,比如说《目光一样透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年出的一本《没有名字的身体》,那里面不全是写70年代的,但是从70年代开始写起的,时间跨度很长。我手上正在写的一个长篇,主要的时代背景也是在70年代。
可能70年代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最重要的成长时段,所以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就最深刻。再一个,我觉得文学创作还是应该要有距离感,近距离发生的东西写到作品中,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感觉总是离得太近、太真实了,缺少了那种可以虚构的比较大的空间,你只要稍微虚构一点,稍微假一点,人家马上就知道了。
问:作家曹文轩这样评价你和你的小说:“她将自己的才情很有分寸地控制住,细水长流地灌注于那些来自她内心的,绵绵不断的文字中间。
她对人性的深切理解,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悟,与她一贯的美学趣味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感,对立却又和谐地构成了她的文学世界。”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你觉得这个评价是否也涵盖了你的儿童文学? 黄:我蛮认可的,这是他在我的一本儿童文学的封底上写的一段话。
其实我觉得不单是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也是,是我自己有意这样为之的。
从1973年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觉得我这人好像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呢也没有像很多作家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问:当今中国少儿文学的不景气,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你怎么看待? 黄: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我们国家,起码在建国之后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儿童文学的地位一直不够高,提到儿童文学总觉得是不入流的,小儿科,然后所有的当代文学批评史,提到优秀作家,没有哪个提儿童文学的,儿童文学是单立的,批评也是单立,它不属于文学那个圈子里面,那么很多写儿童文学的人,必然就会有寂寞之感吧。
其实在我走过的世界很多国家,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都非常高的,跟我们开座谈会介绍的时候,很多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儿童文学作家,非常尊重他们。前不久我去印度,跟印度文学院的作家们座谈,我当时就问了一句,我说我是写儿童文学的,希望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作家也写儿童文学,结果有四五十名作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写儿童文学。
就是说很多国外优秀的作家,他们同时也都为儿童写作,但是我们国家对儿童文学这一块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高度,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优秀的作家他没有走到儿童文学的这个行列里面来。
或者一开始是写儿童文学起步的,在积累了经验以后,马上就转为成人文学,再也不回到儿童文学里面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孩子看童书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负担太重嘛,只能偶尔看一点点,所以就必须选择他最喜欢的。
大量的儿童文学并不那么畅销,并不那么受欢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拦了作家往这个方面去迈进。 问:你的《中国童话》,对一些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比如《牛郎织女》、《神笔马良》等等,进行了重写,怎么会想到去重写的? 黄:从我的孩子、亲戚的孩子开始,我发现现在孩子对外国的童话啊,包括传说啊接受得很多,但是对本民族的东西,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几乎不了解,而我们小时候最初的文学启蒙,其实都是童话和传说,都是听老人啊、祖母啊乘凉的时候摇着芭蕉扇给我们讲的故事。
现在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氛围了,没有夏天在那儿乘凉的,现在都是空调了,也没这种时间,他们都是从网上、从电视上接受的快餐文化,不可能听一个老人慢悠悠地给他讲这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对于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民族的、很经典的、很古老的传说太欠缺了,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就希望给孩子们来补上这一课,就是你必须对自己民族的东西知道一点,即使将来你在国外工作、生活、成家,但你还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跟外国人交谈起来,你还是要说一些自己民族的东西吧。
再一个呢,就是那段时候我忽然看到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写的《意大利童话》,我就觉得,卡尔维诺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大作家,他也肯俯下身来,为本民族的这些口口相传的童话做收集整理的工作,我觉得很了不起,所以我想,我也有这份责任来做这样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民族很多传说、童话故事是一种原始的记录,有的就是民间工作者下到基层去,然后听人家讲记下来,文笔粗糙,故事简陋,而且大量重复,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肯定缺少吸引力,没有可读性。
所以我就把这些故事阅读一遍,从中筛选了十个比较经典的,然后把相近的故事结合起来,加以我自己的创造。而且我尽量用华美的文笔,把这十个故事写得非常华丽,我希望在文字上能够给孩子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
问:据说你女儿给过你很多创作灵感。 黄:是我女儿直接促成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集中写了三四年的儿童小说,后来我有15年时间没有碰过它,到1996年又写《我要做好孩子》,我女儿是直接的一个动因。
因为陪伴她长大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感慨、感想,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我想,不写出来好像也蛮可惜的。
当时很冲动,写的时候非常顺利,因为这个生活太熟悉了,写出来以后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好评,受到那么多孩子的喜欢,所以就促使我一本一本地继续写下去了。
这是一个契机,没有我的女儿,我就不可能再去写儿童小说。 问:她有没有评价过妈妈写的小说怎么样? 黄:没有,从来没有,我也没有问过她,我要是问的话,估计她也不会给我太高的评价。
但是《我要做好孩子》这本书,因为写的是她嘛,我想她一个人起码看了有十遍,经常趴在床上看,看着看着自己一个人笑,过了几年她长大了,回来以后还拿出来看看,还是笑。
她还把我的书带到澳大利亚去,她的同学看后还很激动,然后她写信回来,说妈妈你再给我寄几本书,其实她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问:不少作家都有“触电”的经历,你也不例外,最初涉足影视创作是你主动的吗? 黄:不是我主动的。
我的第一个电视连续剧《瞬息存亡》,是1995年写的,当时南京电视台找了几个作家,说要侃一个电视剧,他们拉了银行的一笔赞助,就想写一个跟银行有关的,侃着侃着,最后说谁来着笔呢?大家一致就指着我,说我最适合,说我的作品故事性比较强,比较适合改编。
当时我也有种兴奋,觉得很新的一个文体嘛,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我觉得大家都认为我适合写,是不是我就可以写呢?那我就写了这个。
因为很多人写电视剧,写很多都是没用的,而我第一次写就用上去了,也很幸运。第二年我就写《新乱世佳人》,写了一大半有30万字的时候,当时范小天已经下海搞电视剧了嘛,我就给他看了,他看了以后非常兴奋,觉得非常适合改电视剧。
其实写这篇小说从落笔的时候,我心里就抱着这个愿望,要把它改编成电视剧,就是往这个上面靠的,所以它的故事性确实是非常强,在人物塑造上面就带有影视剧的痕迹了。
那么他就策动我,说你这个小说先放下来,先弄影视剧,因为影视剧从写到拍出来再到播出,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你先把这个电视剧弄出来,然后回来再把小说弄出来也不迟。
在他的策动之下我开始弄电视剧。当时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反响很大,很多电视台都一播再播,一直到现在,偶尔有电视台还在非黄金时段播。当年在四川还是在湖南吧,创下了百分之五十几的收视率,不得了,简直是惊人的收视率。
问: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都是你的强项,对你来说,这三种不同的写作状态是怎么安排的? 黄:我是专业作家,平常也不上班,很少跟外界接触,有时候一个人在家写作还是很寂寞的,那么这三种写作状态交换以后,我觉得对我的生存状态很有好处,比如说我写儿童文学的时候,就非常地放松,觉得这是一种快乐,那么写影视文学的时候呢,它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因为影视文学它必须要跟外面交流,它必须要跟制片人、制作公司、演员、导演,各方面都要沟通,参加到影视创作当中,我就可以走出我的书斋。
而且影视文学和文学创作完全是两码事,文学创作有时候它要淡化情节,要避免情节的大起大落,不能把情节弄得很剑拔弩张的。
那么影视文学恰恰相反,它强调的就是这方面。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写,觉得很没劲,或者陷入到轻度抑郁状态的时候,我去搞影视创作,我就会兴奋,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情节去想、去构造,人物的命运,人物的社会背景,在一节剧本里面去把它怎么交错起来,暴力也有,情感也有,故事也有,误会也有,什么都有,我觉得蛮刺激的,所以这也满足了我另外一方面,就是追求刺激和惊险的天性。
基本上这三种写作状态,在这十年之间我是交错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