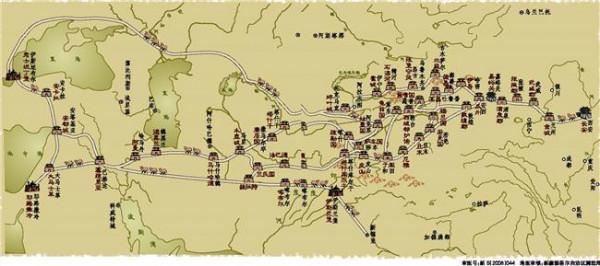电影大国的老传统与新格局
最近,阿米尔·汗出演的一部《摔跤吧!爸爸》燃起了中国影迷对印度电影的热情,也让我们借此机会审视一下印度这个电影大国的老传统和新格局。
电影神话与全民特性
印度电影的规模一直是个“神话”,年产一两千部影片,总票房一千多亿卢比,论产量甚至超过好莱坞,论观众数也就中国能有一拼。若算年均观影数,30亿人次的印度还能甩开中国一截了,毕竟他们的票价极为便宜,通常只有10到50卢比,最高不过150卢比(也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日均人次最高可达千万,全国1.3万家影院能达到这种收入,说是“电影大国”不算虚言。正是由于印度人对电影的由衷热爱,才支撑起偌大的市场,各阶层都把看电影当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穷人也愿意排队买最便宜的前排座,只为在老旧的戏院里耗上大半天,感受银幕上如痴如醉的梦境,顺便把冷气吹过瘾。
宝莱坞是印度电影的代名词,但印度电影不只有宝莱坞,除了孟买,还有班加罗尔、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好几个电影制作基地,由于各邦地缘文化和教育程度不同,从中北部的印地语区到西南的卡纳塔克邦,从喜好英语片的精英阶层到草根的贩夫走卒,口味不尽相同。宝莱坞因为商业上的成功更具覆盖性,也凭借海外输出拥有国际知名度,孟买电影城自然是最著名的“梦工厂”,数百家电影公司在那里搭景开机,摄影棚与恢宏的宫殿林立,杀青后又被拆得一干二净,如此往复,无非是为广大印度人民制造梦想。
印度电影 “动辄三四小时,一言不合要跳舞”的标签,在宝莱坞的推波助澜下更加凸显,从没有强制规定影片中必须要跳舞,一些严肃的作品中也没有舞蹈场景,这个所谓传统更多是市场催生的。既然广大观众喜欢看,那制片方就纷纷加入这种商业元素(就像港片里多有动作戏和武术指导),演员不会唱不会跳没关系,有专业编舞、配唱和替身。真正对影片内容加以限制的,还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政府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既然电影放映算得上是社会活动,当局就不可能放任不管,印度早在1918年的《电影法》中就存在了审查制度,独立后更是沿袭这种管控,有来自警方、海关、教育界,以及宗教团体的审查人员,把印度全国上映的影片分为四个级别,从最公开的U级,到限定18岁的A级,12岁下家长陪同的UA级,以及最严格限制观众的S级,可以任意删减影片内容,片方若对审查结果不满,上诉的最终裁决权归属联邦法院。
神话汲养与重金特效
多年来印度电影一直从神话、史诗中汲取养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文学巨作贡献了取之不尽的灵感。一如去年的票房大片《巴霍巴利王》,印度观众习惯于看到自己的祖先被“神话”,扛着林伽,上天入地,无往不胜。印度电影中崇尚神力,任性开挂的欣赏传统自从有了CG特效的加持,更是如虎添翼,从《阿育王》到《巴霍巴利王》,十几年来不断创造视觉奇观,这种对恢宏场面的调度能力和审美趋向,在中国也仅有张艺谋能一较高下。
有了技术和资本的保证,印度人如今完全有能力在银幕上实现“七香四洲三千世界”,耗资17亿卢比的《巴霍巴利王》才刚刚拍完,下部尚未公映,就传出了要拍《摩诃婆罗多》的消息,预算高达100亿卢比(1.5亿美元),陡然把印度电影的成本纪录提高了6倍。《摩诃婆罗多》这样煌煌“二十万行”的民族史诗,即便拍成上下两部影片,也不足以涵盖其庞杂的内容,只需取其中婆罗多两族夺位的主线,用耀眼的特效和扎堆的明星来满足观众的民族热情,以《巴霍巴利王》的票房成绩来看,这部计划明年开拍、2020年上映的神话巨作,并不难实现其商业目标。
但高投入的精品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印度电影都有模式化的毛病,经常是帅哥爱美女的爱情戏,好人受冤终复仇的苦情戏,再插入大段的歌舞,追逐打斗,乐此不疲。架不住这种组合一直受到普通观众的喜爱,他们对艺术性的要求不高,更多的是在电影院找寻娱乐和放松,最好是大团圆结局,能让他们带着愉悦的心情走出影院。
然而,在这股砸钱上大片的热潮中,印度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难免有些落寞,挑战积弊多年的社会问题需要勇气,尤其是印度女性常年低下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哪怕出现了《炽热》和《女生规则》这类呼吁妇女保护的作品,也架不住此起彼伏的强奸案给印度形象带来的恶劣影响。毕竟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半神的英雄,能保护妻女的,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开放的现代文明。
“明星制”与商业性
与这种模式化的情节搭配的,就是从早期好莱坞学来的那套“明星制”。如今的几位印度大腕儿,所谓“三大汗”:阿米尔·汗、沙鲁克·汗和萨尔曼·汗,就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拥有巨大的群众基础和公众影响力(《脑残粉》里的疯狂场面可见一斑),印度人骨子里的“偶像崇拜”情结,足以轻易转换为政治资源,不少影星当上了政党领袖,参与社会活动,这在印度比西方更为普遍。当然影星之间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老前辈一旦渐露颓势,就要受到赫利尼克·罗斯汉和阿克谢·库玛尔等年轻一代的挑战,阿米尔·汗为了拍《摔跤吧!爸爸》拼命折腾自己,又是增重又是减肥,除了敬业,一部分也是源于这种压力。至于女星,则很难有如此常青的地位,“宝莱坞头号美女”的名号转得飞快:卡琳娜·卡普,普雅卡·乔普拉,卡特琳娜·卡伊芙,索纳普·卡普,艾斯维亚·雷……她们就像众神的曼妙化身,招之即来,足见印度电影业的风顺轮流转,不亚于好莱坞。
自20世纪初,以萨达达拍猴子开启了印度电影史,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古鲁·杜特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到如今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印度电影长期自给自足的欣赏模式也在悄然变化。虽然好莱坞大片在印度市场的份额只有10%,但带来的冲击是全方面的,尤其是1997年《泰坦尼克号》的上映,造就了英语电影在印度的票房纪录,给故步自封的印度电影人以震撼——原来大片应该这么拍!
上世纪90年代后的印度电影逐渐有了改变,虽然还无法摆脱爱情苦情那一套,但明显加重了社会反思的主题和枪战飙车等动作戏,男女人设也出现了一些边缘人群。相比价值观的更新程度,印度电影在技术层面的进步更加明显,各种拍摄手法、特效技术向好莱坞看齐,阿米尔·汗的《幻影车神》的飙车戏足以比肩《速度与激情》,各种动作片、惊悚片、科幻片也层出不穷,想象力之奇诡,足以挑战任何自然规律,网上那些脑洞清奇的GIF,其实都截自《雄狮》等本土动作片。
然而,在出口商业片的同时,印度电影的艺术性却被遗憾地忽视了,常年缺席戛纳、威尼斯等国际影展,提起大师级名导,也就资深影迷能想起萨雅吉·雷伊,可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传奇了。大量的印度裔海外移民,也为印度电影的出口创造了条件,但多是宝莱坞主导的商业大片,小成本文艺片也就《午餐盒》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导演也会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各大电影节(包括北京、上海),但多数水准尚不足。
“黑涩会”与贪腐
别看印度电影的产量高,观众基数大,却是个高风险的行业。有数据显示,98%的印度影片是亏本的,遇见市场行情不佳,放映和发行公司内耗,甚至是流感爆发等因素,全国市场都会受到严重的波动,2009年就曾发生过票房大盘下跌14%的“惨剧”。在创新匮乏、设施陈旧等各种弊病中,印度电影的资金来源,一直是让电影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别看年产量高,共需数百亿卢比的投资,但政府并不会给这些影片拨款,各邦政府还征收30%到50%的娱乐税,商业银行也很少给片方放贷,因为大部分影片还是赔钱的,风险不小。导演和制片人只能自筹资金,其中不少是来自于黑社会的赃钱,也就是说拍电影主要是为这些走私、贩毒者“洗钱”。假如影片无法盈利,还很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曾有制片人因此被黑帮折磨致死,导演住所被炸毁,编剧被枪顶着脑袋改对白,女演员不得不去陪大佬跳舞,甚至集体给通缉犯们祝寿……从孟买到班加罗尔,许多电影人背后遭遇的是外人不知的屈辱。黑社会对于印度电影业的渗透,还造成了银幕暴力的泛滥,他们可以直接插手导演的创作,肆意在影片中诋毁政府和警方,侮辱妇女,把自己美化成英雄,这也算是一种“虚构的社会奇观”。
当然这种被黑社会操控的印度影片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大多是雷同的情节,但社会影响恶劣,对现实中的暴力犯罪推波助澜,许多电影人一直在大声疾呼,希望摆脱这种状况。可偏偏印度负责电影管理的部门也不干净,譬如主宰电影生杀大权的印度审查委员会,决定一部影片的分级和上映资格,前年该委员会主席拉克什·库马尔就因受贿罪被捕,家中被抄出大量现金。许多印度影片为了能尽快通过审查,不得不向审查委员会的官僚们行贿,通过指定的代理中介机构送审,否则会遭到各种名义刁难。
此外,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在印度民间产生不小的影响力,也担负着引导意识形态的功能,常会受到复杂的政治势力、宗教组织和民族主义的拷问。1999年有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火》,揭示了印度女性的悲惨地位,控诉落后保守的包办婚姻,虽然获得了上映资格,还是遭到了攻击。
还有一部影片《危险》,原是讲述锡克族男青年爱上了穆斯林女孩的“爱国主义”作品,上映后却引发了孟买和德里穆斯林的大规模抗议,骚乱一度升级到政治层面。毕竟在南亚次大陆这片土地上,电影有其复杂的宗教和民族属性,并不只是“谈谈情,跳跳舞”就能让所有人都欢愉的,像“蒙巴顿方案”这种历史遗留的敏感问题,一旦触及,激起争议就很难平息。由此可见,越是历史悠久,越是民族成分复杂,创作者要躲避的坑就越多,唯独阿米尔·汗敢于挑战此类症结,借《我的个神啊》用喜剧方式来对印度文化进行反思,呼吁跨族群的和睦相处,甚至与巴基斯坦人步入婚姻殿堂,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真是难能可贵。
中国销路与文化互探
在中国的亚洲邻居里,印度恐怕才是最陌生的,不要说日本、韩国等东亚近邻,就连新马泰也因旅游市场的开放显得熟悉亲切,《泰囧》的成功就是例证。虽然印度拥有世界产量最高的电影工厂,但对中国市场的输出一直很少,除了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缺少移民基础,不依从世界主流(也就是好莱坞)的叙事手法,独特的口味偏好,也是阻碍中国人理解的重要原因。
中国影迷所知的寥寥几部“印度大片”,大多还是通过互联网获得的,断断续续看个热闹。《宝莱坞生死恋》、《阿育王》等具有史诗片的噱头,繁复的歌舞,恢宏的战争场面,视觉上的夸张也颇为直接,人海战术用起来得心应手,同为文明古国,倒与咱这儿的“盛世奇观”不谋而合。
近年来印度电影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进入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同时规避本就不多的“外片配额”,与中方签订了中印电影合拍协议。像王宝强的《大闹天竺》、成龙的《功夫瑜伽》和黄晓明的《大唐玄奘》,都是在这个协议框架下操作的产物。影片最后的成色暂且不论,但能去印度实地取景拍摄,数百人的中方团队与印度同行合作,确实实现了文化上的交流,对彼此的品位和技术水准有了更多的了解。反过来,印度电影人也拍摄了《月光集市到中国》、《阿辛哥的奇妙之旅》和《私奔到中国》等喜剧,以功夫和熊猫等中国元素来吸引观众,毕竟印度人的好奇心也不小,想知道隔壁的“成龙”们是如何变为买遍全球的土豪的。
对于印度电影来说,在中国这片早已群雄逐鹿的平原上,能争取到公映的机会已算成功了,纵然是上映一年的买断批片也为时不晚。这个美好的开局来自于阿米尔·汗的《三傻大闹宝莱坞》,2011年该片被中影引进,虽然网上早有资源,但由于爆棚的网络口碑,仍然吸引不少观众去影院一睹为快,最终在中国取得了1404万人民币票房佳绩。中国观众突然发现,印度人并不只会拍古装史诗片,他们的现实题材同样具有想象力和深度,纵然传统风俗差异巨大,印度大学生、白领和工程师的日常生活与中国同龄人并无太多不同,《三傻大闹宝莱坞》中讽刺的教育问题在中国似乎也存在。在《三傻大闹宝莱坞》上映成功后,陆续有不少印度电影登陆中国院线,阿米尔·汗的另一部杰作,《我的个神啊》更是在2015年收获了1.1亿票房,创造了印度电影在中国的最高纪录。这两部印度现实题材喜剧在中国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其中营销宣传抓住口碑造势的功劳不小,可以说为阿米尔·汗在中国影迷中建立了个人品牌,也为其新作《摔跤吧!爸爸》引进中国,奠定了乐观的票房预期。
不过,阿米尔·汗的两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中国市场就大度地接纳了印度电影,2016年引进的两部印度大片《巴霍巴利王:开端》和《脑残粉》,虽然质量也属上乘,由于缺少足够的宣传,最终在中国的票房惨淡,可见风险并不比本国小。《巴霍巴利王》并非产自宝莱坞,而是南部的泰卢固语出品,同样展现了印度人拍摄史诗片的工业水准,数码特效之铺陈,直逼好莱坞同类影片。但由于中国观众对印度历史和神话系统不了解,出现了认知错位,逻辑踏空,导致笑场连连,上部的票房仅有749万,下部的引进恐怕遥遥无期了。
另一位“天王巨星”沙鲁克·汗主演的《脑残粉》,虽然是商业片,但也严肃探讨了明星与粉丝“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剧本构思巧妙,一人分饰二角的演技出众,讽刺的虽然是印度疯狂的偶像崇拜,放在当下中国社会也具有警示意义,然而由于宣传不力等各种因素,中国上映后知者寥寥,票房区区153万人民币。由此可见,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商业电影,想要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路途遥远,偶然性极大,还不如通过合拍方式,用一部卖座的“印囧”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印度,培养出更多的文化爱好者,再图长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