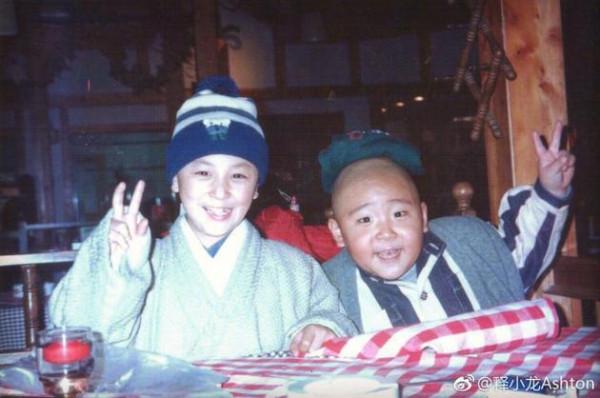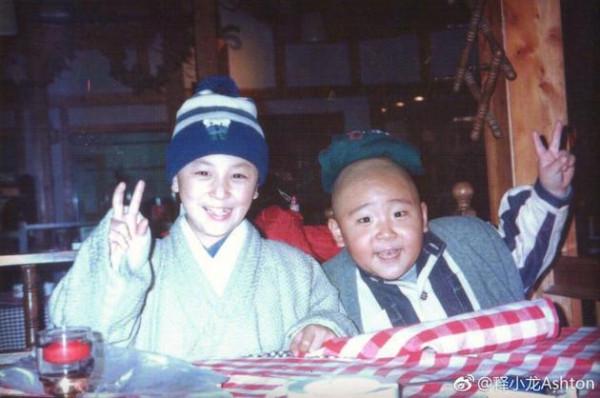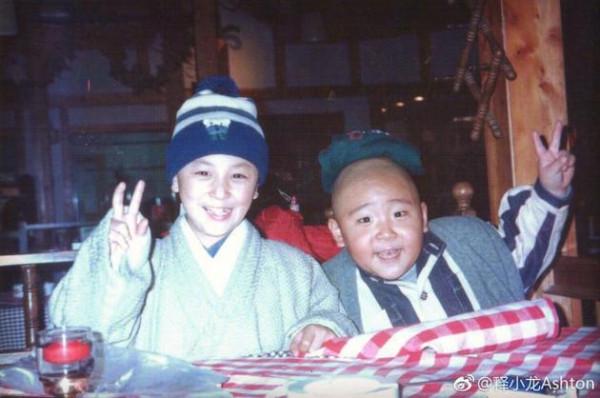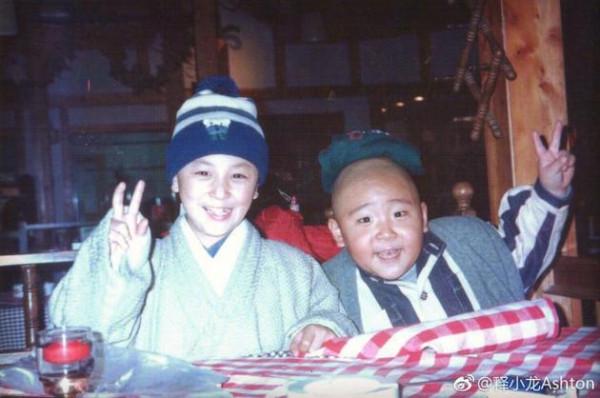我爱过的青丝如今已变成白发
年少轻狂我们总能留下很多美好的事情,而青春时期的爱情往往是最甜蜜的,它值得我们一生怀念。我曾经爱过这么一个少年,他温文尔雅、白净帅气,成熟中又有着几分逗趣,让我爱不释手……
6月的异国他乡,李皎然拆了一个包裹:两包方便面。是几年前最便宜的那种。她立刻红了眼眶。
那是她从前的感情,好得像从不曾真正拥有。他们并肩作战,最困苦的时候吃的面,市面上大约已经停产,杜微白费了苦心寻来,用于破冰。
这么一想,原来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李皎然第一次见到杜微白是在她大四的时候,那次她作为助手陪影视系主任庄老师参加一个影视投资广场沙龙,中场休息时他过来递名片。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他简单又随便,T恤、牛仔裤,没有穿皮鞋。
据说,一个男人如果到了30岁还没有学会穿皮鞋,那么他不是混得太差,就是混得太好。那一年,杜微白刚好30岁,他属于后者。
他很有名,是大了好几届的学长,中途因严重缺课被学校劝退,22岁有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几年后卖掉,赚了一笔钱。30岁有了第二家公司,做影视,人生风光得意。
李皎然看着他,他的脸背着阳光,有暗影,像一笔一笔的素描。
她说:“我没有名片。”
“那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写在我手上。”他摊开了手掌——宽阔,像一面海。
隔了一个星期才收到他第一条短信,喊她下女生宿舍楼。他靠着黑铜灰的小跑车,对她招了招手,从车里拎出—盒蛋糕。
“去上海出差,那里的姑娘都爱吃这个。我想无锡的姑娘应该也爱吃。”
李皎然不解风情,“我不是无锡人。”
“那美女都爱吃。”他把蛋糕塞进她怀里,轰了下油门扬长而去。2008年的杜微白在他人生的好时候,赚所有满足他野心的钱,泡所有他看得上的妞。
李皎然只是其中一个。
渐渐有了来往,他带她出去吃饭,参加他朋友的聚会。瘦瘦小小的李皎然,跟在杜微白身后,被一帮大老爷们儿起哄,要她喝酒。杜微白却截住每一杯递给她的酒,喊来服务员,给她点了一堆果汁。李皎然就着吸管吸溜着果汁,听这帮人吹牛。
是盛夏,她年轻如饱满新鲜的水果。杜微白拍了一下她的腿,她骂了他一句,嘴角却是梨涡浅笑。
后来李皎然不止一次回忆,如果那个夏天的变数没有发生,她可能只是他泡过的一个妞,而后移情,而后离散,也不会有后来的念念不忘。
但是命运突然在那里拐了一道。
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杜微白的公司突然就一落千丈,几天兵荒马乱,周遭的世界突然就安静了,30岁的他再度回到20岁时的一无所有。除了多出一个李皎然,替他应对所有公司清算、工商注销的琐事;把他从酒吧门口拖回来,放进干净温暖的床;藏起他家里所有锋利的东西,生怕他想不开……
那一年的李皎然,不是拯救地球的英雄,只作为他上天入地的女超人。
杜微白渐渐缓了过来,盘算着还有一套房产可以卖了从头再来。他问李皎然是否愿意留下来帮他。问的时候是忐忑的,他开不出诱人的条件,唯一的筹码,只是从前他对她的好。
李皎然在厨房煮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们做回杜微白最初的老本行,弄了一个很小的传媒公司。两个人到处跑着找办公地点,终于在老城区的一个民造别墅区找到合意的房子。里面够破,房租水电都便宜;地理位置适中,公共交通都方便。
那个清晨,李皎然和杜微白拿着用最后所有的钱换来的钥匙走进这里。屋内一片萧索,唯有阳光的铺洒带来些许生机。她靠着结着蛛网的门框,看着杜微白走进阳光里。他的背影很坚实。他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地站着,静默了许久。
那或许就是这座已经老得白发萧然的房子里,初始的幸福吧,是一片废墟里开出来的一朵花。
2008年的李皎然蹲在地上,拿着一把刷子,把地面擦得干净发亮。
她和杜微白的2009年和2010年,可以用一些气味来回忆:六神花露水、夜深煮沸的泡面、夏天养在茶碗里的洁白栀子、12月隆冬时晒在阳台上的被褥……
后来,杜微白当然翻身了。
第—年,他们把家搬出了办公楼,杜微白给李皎然找了一个不错的住处。适逢她的父母来无锡探望,他特地跟朋友借了辆车,载着这一家三口,宾主尽欢地玩了两天。李皎然玩得有滋有味,杜微白却心有愧疚,“小皎,辛苦你了。”
李皎然眼睛望着他,“是我自己乐意的。”
他们赶项目进度的时候,没日没夜地熬,李皎然累得趴在地上画设计稿,完成的时候腰几乎直不起来。他连忙来扶她。她穿着他的旧T恤,远远看去,两个人像一对兄妹。
那两年,他们是越长越相像,没有发生的爱情,变成了另外一种养分滋生进他们的生命。李皎然有时悄悄望着杜微白,心里难过。她知道他们是错过了。那个她跟在他身后,满是啤酒清香的盛夏,永远地过去了。
第二年,公司越来越好,又投了几个项目,杜微白渐渐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还是喜欢那种瘦得电线杆一样的女孩。买了一辆车,偶尔带李皎然出去兜风。那一阵,李皎然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长久的失眠令她脆弱而敏感。她望着窗外的景象,只觉满眼苍凉。她说:“杜微白,我还是喜欢你。这么久了,还是喜欢。”
他有些愕然,好像突然才知道她的想法一样,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小皎,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啊。我视你为一生的挚友,最珍视的朋友、事业伙伴。没有你,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李皎然侧过头,微微笑了一下,“我知道,我只是想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
那个傍晚之后,他们尴尬了几天,之后又相安无事。李皎然还是失眠,杜微白托人从国外带回了一些天然成分的保健品给她,第二天她面色好了很多,说:“药效很温和,服下后一小会儿就能入眠,还能做到很美的梦。”
那温和美好的感觉,像被那个黄昏温暖的湖水慢慢覆盖上来,像轻轻的被子,像他宽阔的手掌,像初见时,手心里的那片海。
李皎然终于要走了,这几年,她像一叶被系在伤心地的孤舟,现在,缆绳终于松开了。杜微白送她去国外深造,她选了布鲁塞尔,学习艺术与哲学。
临出国前,他们约好一起吃顿饭,选了一家新开在半山腰的餐厅。他晚到了一会儿,隔着落地窗看着她赖在沙发里,用iPad在看电影,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毛衣,头发又长长了很多,散在瘦削的肩膀上。杜微白隔着窗户凝视了她很久,心中也难过。想到这几年,他对她亦师亦友,如兄如父,偏偏没有做恋人的缘分。
她扭过头,隔着窗户看他,眼中有泪光。
纵然心中怀缅往事,也知道来路不可追。
他最后握了握她的手,柔着声音说:“上楼吧,今晚好好睡一觉,明早我来接你去机场。”
那晚他也没有走,静静地在车里坐了一晚,也不觉得累,想着这可能是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难过,好像送走的,是整个青春。
李皎然走后的那4年,他们联系寥寥,仅止于一声新年快乐或是生日快乐。杜微白不知道她有没有回过国,只是再没有来和他见面。他也有过几段情事,只是都没有结果。却渐渐怀念起李皎然,心里像手植了一棵无花果树,从不曾开过花,果子却已悄悄成熟。
如果不是医生说他患上了视力渐退的病,他也不会下定决心联系李皎然。心里就一个念头,趁着目光还清明,想再看一看她的模样。
隔了四五年的会面,李皎然迟到了一会儿。看到杜微白坐在不远处的藤椅里,视力大概衰退了很多,呈现老花眼的症状,所以把手机拿得远远的,一个字一个字拼着。不一会儿,她收到信息,问她到哪儿了,是否迷路。
她不近不远地望着他,那张二十多岁就装在心中的脸,是一张感情丰沛、动人的脸。这几年风雨飘摇的委屈,就在那一声是否迷路中,如晨雾,轻轻消散。她走到他面前,轻轻坐下。
时隔经年,该聊些什么呢?
就从他们各自长的第一根白头发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