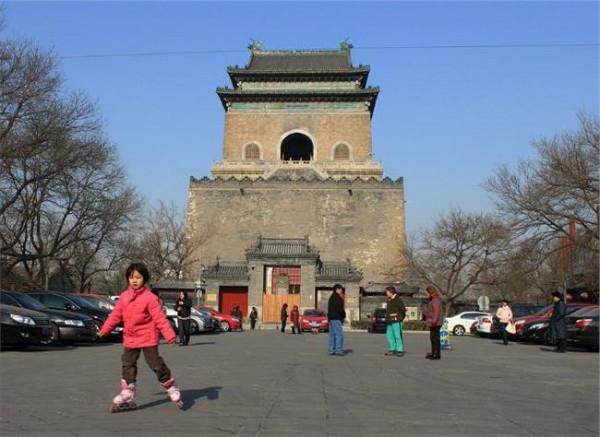蒋筑英的子女 从蒋筑英之死看知识分子的生态
八,逍遥派不逍遥 残酷的路线斗争没有常胜将军。今天盛气凌人,明天被挂上牌子游街,后天可能成为阶下囚。当时最响亮的口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领袖的部署瞬息万变,谁也难跟得上。红卫兵中有一句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要求站错队的人及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站队,这个名词已经深透到日常生活中。有一次,我买蔬菜,卖菜的女人动作很慢。我讲:“站错队了。”有人正经八百地用领袖的语言教导我:“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
”我觉得队伍太长,重新站队不合算。我只好顽固地坚持我的错误路线。等到轮到我买菜的时候,卖菜的女人狠狠地瞪我一眼:“你不是站错队了?”卖菜的人掌握“卖”或“不卖”的权利,一点也惹不起。
我屁也不敢放,忍气吞声地听她教训。政治要站队,生活要站队。愈站队愈糊涂。 有人什么队都不站了。一位坚定的钢杆保守派,几次站错队,大声讲:“我再也不押宝了。”参加逍遥派的行列。
这位昔日的革命派,用“押宝”这样的赌博名词描述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当坚定的保守派与激进的造反派纷纷参加逍遥派的时候,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已经不能为“纲”了。写到这里,我有点羡慕蒋筑英了。
蒋筑英重任在身,不可能逍遥。如果我们有沉重的科研任务的话,决不会无所事事的逍遥。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两次大规模的以群众为斗争对象的运动,使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而近于崩溃。
也许这是思想解放的开始。我称逍遥派为身居闹市的隐士。逍遥派的诞生是大好事,它说明人们对政治运动的厌倦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失败。 文革前,逍遥是有罪的。为什么不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去,为什么要逃避阶级斗争。
这些都可以成为批判的语言。“为什么不?”是批判会上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革命派用来指责他认为必须做,而被批判者没有做的行为。有个冶金专家专门研究刮胡刀片,因为刮胡刀片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课题;可是革命派指责:“为什么不研究工农业生产必须的产品,而研究理论脱离实践的刀片,典型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
” “为什么不”也是一根棍子,可以用它打击逍遥派和中间派。革命派决不允许逃避现实。当逍遥派大量产生时,正是人们开始觉悟之时。
革命派企图批判逍遥派。人们已经饱尝形形色色的恶毒攻击的语言的时候,谁在乎不痛不痒的批判。 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明清之际的八大山人隐于书画,逍遥派隐隐在何处。 平民百姓不可能隐于朝。
朝中是你死我活的高处不胜寒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学陶渊明隐于山林,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农村的阶级斗争更残酷。 陶渊明可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研究院位于岳麓山下,湘江之滨,一叶小舟可达橘子洲头。
这是城乡交界处的幽雅地方。但登岳麓山不敢舒啸,临湘江不能赋诗。有例为证: 一位爱好文学技术水平很高的才子。才子有点怀才不遇,喜欢读鲁迅的诗,才子手书鲁迅的《解嘲》诗,挂在寝室的墙上。同住一个寝室的大学同窗,向党支部回报此事。
爱好鲁迅的诗有罪,在全国神化鲁迅的时代几乎不可思议。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听到梁漱溟先生的奇谈怪论:“不怕共产党的唯物论,只怕共产党的辩证法。”用辩证法来解释这种现象就很简单了。
鲁迅的诗写于旧社会,发泄对旧社会的不满是革命,生活在新社会的年轻人喜欢“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只能说明对新社会的不满。鲁迅的这首诗中除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外,其余每一个字,都可以成为仇恨新社会的根据。 有趣的是告密者也是领导心目中的落后分子。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标准衡量那时的价值观,告密者的内心世界不完全是阴暗的。靠拢组织,向领导回报思想和周围人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先进的,光荣的,理所当然的不容置疑的。
当然其中包含损人利己的向上爬或者改变自己地位的想法。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往往是大杂烩,不是容易摸透的。 告密者的下场很惨。一次开会,不知那个觉悟特别高的人,突然讲:“发现反动标语”。
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会议主持人请大家传阅,以辨认是何人所为。传到告密者面前,告密者讲:“我写的。”实际情况是两人写了两行字,一行写的是“消灭”,另一行是“毛泽东”。两行字勉强连接在一起凑成一句反动标语。
其中一行是正在失恋中的告密者写的。 那时造反派掌权,会议主持人正是被告密的才子。才子不计前隙,诚恳地,全面地,得体地,按当时的政治标准解释告密者不是故意书写反动标语。
才子为此冒了一定的风险,小心谨慎地为告密者辩护。 告密者参加逍遥派,成了钓鱼能手。有人说,他情场失意,鱼场得意。垂钓之余,还写点诗消遣。 逍遥现象是文革中非常优美的风景线。从中可以看到,群众对现实的不满;也可以看到领导对群众的无奈。
其中不乏大彻大悟者;附庸风雅者,读书,写字,弹琴……;从俗者,下棋,打牌;更多的是实用主义,学木工,修钟表,做裁缝……;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几乎万事不求人。
逍遥派中不乏清醒者。他们一点不逍遥。他们是冷静的观潮派,看潮起潮落,观云聚云散。管他天翻地覆,我自岿然不动。 这些人的行为,不禁使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走到《智通寺》看到的那副旧破的对联: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些人正如贾雨村所想到的:“其中必有翻过筋斗来的”。大多数觉悟太晚了,毕竟觉悟了,总算好事。 不参与政治,关心政治。这些人开始懂得,国家、民族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形势一定会变化,如何在变化中求生存。
学外语,钻研科学技术也在静悄悄的进行。 逍遥生活不平静,随着运动的深入。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告密者在劫难逃,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才子遭受打击,罪状之一是包庇反革命分子,包庇写反动标语的告密者。
告密者的诗,理所当然应该批判。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引用毛主席的诗:“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边。”也受到批判。我实在听不懂革命派的批判语言。牵强附会地将“冷眼”解释为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这可以算得上辩证法的成功应用。 经过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乱写,不瞎画,不乱丢废纸。学书法,只写那些“风雨送春归”,“春风杨柳万千条”等一些既革命,又中性的诗句。
逍遥生活不逍遥,隐居日子不好过,毕竟活了下来。活着就是胜利。蒋筑英生前的悲哀,死后的荣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 2001年9月14日 第一稿 2011年12月25日 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