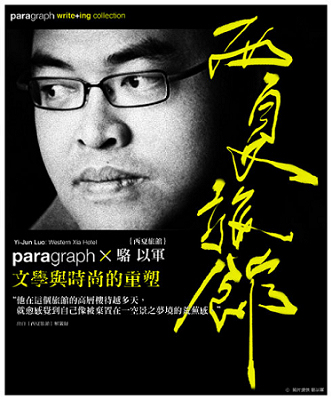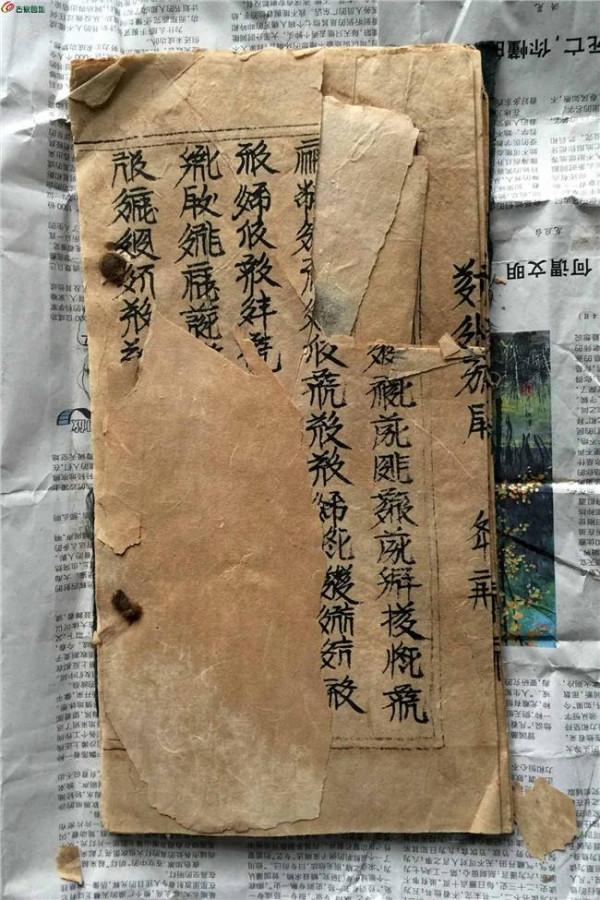骆以军三体 《西夏旅馆》试读:第三届“红楼梦”文学奖得奖感言(骆以军)
二百五十年前曾有一个天才写下了一本奇书,那本书赋予了“小说”一个全景:一种将时光冻结,让我们可以慢速微观人类黑暗之心的纹脉;对美的艳异惊叹;对超过单一个体的劫毁崩坏心生恐惧与哀戚;一个微物之神所照看的繁华文明。
只有小说才可能演绎的、迷宫般的完满宇宙。 当然,那正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而经过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百年,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到后来的莫言、阿城、王安忆、李锐、余华、苏童、韩少功等人,无一不是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以小说为视窗,所幅展的疯狂躁郁之梦,倾城之梦,人命如刍狗悲凉之梦,生死疲劳之梦。
作为一个台湾创作者,能在各位尊敬的评审先生及浸会大学的钟玲院长手中,接下这个似乎包含了中文小说之神秘咒语名称的大奖——“红楼梦”,我的激动和感激难以言喻。
在我所承接的小说时光,另有一条不同时间钟面的“梦的甬道”,因为百年来的战乱、大迁移与离散,有另一群人被历史的错谬,脱锚离开了“中国”这个故事原乡(这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在一个异乡、异境,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抛离处境中,慢慢变貌、异化,在他们的追忆故事中长出兽毛和鳞片,形成另一种“歪斜之梦”的孵梦蜂巢。
在台湾,譬如朱天文的《巫言》,朱天心的《古都》、《漫游者》;譬如舞鹤的《悲伤》、《乱迷》;郭松棻的《月印》;在马来西亚,譬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大河尽头》;张贵兴的《猴杯》、黄锦树的《刻背》;在香港,譬如启蒙我那一整世代的西西,或我同辈的董启章的《天工开物》……又譬如更早的海外的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与李渝的《温州街的故事》…… 这于我是一个乱针刺绣,一个南方的、离散的,因为彻底失去原乡而绝望妖幻长出的繁丽畸梦。
像是宫崎骏《神隐少女》里,父母变成猪之形貌,而我的名字被神收走了,唯一救赎之路,便是凭空再创造一个梦的结界。像V.S.奈保尔《抵达之谜》里,那永远的渴慕、永远的哀愁,那是一张永远无法回到画像最初时光的雾中风景。
关于“旅馆”,在我初始的朦胧想望,想打造一座像《霍尔的移动城堡》或《神隐少女》那个“神鬼之汤屋”的极域之梦:里头每一个住客、每一个服务生、经理、走廊推车打扫房间的阿婆,他们各自的回忆在填塞、修改、变形着这整座旅馆的边界。
我大学时曾读了巴斯(John Bath)的一个短篇《迷失在欢乐屋》,非常着迷,大约是一趟家族旅行,大人之间有其心机,小孩之间也存在着干拐子的轻暴力,这个主人翁的小男人则暗恋同行另一家的一个女孩,总之之后他们是在游乐场的一座欢乐屋(有点类似镜廊迷宫或惊异屋这样的设施)进入一种奇异的时光困陷,他们(也许只有他)困在里面出不去了。
他似乎跑到欢乐屋甬道隔板的另一侧了:那些管线、机关、偷窥孔、通风孔道……我对这个故事既着迷又恐惧,他在墙里可以听见其他同伴远近错落的嘻笑脚步声,但他却像那些“游乐场鬼魂”永远出不去了、离开不了,一直踟蹰打转在那个欢乐屋时光里。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禁锢住所有人物的一个结界。
像伯格曼的那些仲夏夜之梦,所有人在一封禁剧场将所有疯魔、恨意、嫉妒、伤害全彩色毒液喷洒出来。但这样的昔日梦境全景蜡像馆对我这样的创作者是近乎不可能,其关键还是老话题:经验的贫薄、教养的匮缺。
我不仅如默片般并不能真正理解上一代本省长辈内心的哀愁、繁华、灰暗和幽默;事实上我对老外省的内心景观不也总是印象画式的摹拟? 但我实在太喜欢“旅馆”这个场所了。这里的人全是过路客、侵入他人土地者、无主之鬼,在时空暂时抛锚的漂浮感恓惶地寻求庇护。
我觉得旅馆和土地的关系就如同我这样迁移者第二代面对严格检查认同之主体形貌的困惑:注定缺乏足够的时光资产。父亲(或他的那一批流亡者)带着大箱小箱的流浪汉传奇,但我们是在片场般的空间聆听他的幻丽唬烂、仪典、做人的道理、我族的历史。
从他记忆中翻印出来少三落四的祭祀程式、封禁的审美趣味,但这一切其实是绝后的──如果你被设定为“往事并不如烟”、“追忆逝水年华”的故事传递人,那就注定是一无性生殖、单套染色体,如麒麟、骡子、狮虎……这些“一夜之恩”的无后时光胶囊。
教养的匮缺(胡人)使我打造的这座文明或时间之屋的违(伪)建,像火影忍者里查克拉不足而勉力造出的幻影,处处滴流粘答、剥落;也使得我企图探问的伤害源头,设定了一个不拿手的接触现象:对对方文明(感性方式、收藏的记忆,不喜欢被篡夺或假非己之口说出的伤痕、层层聚累的阴影、原本稳定的人际结构)的不理解而粗暴犯错;如何体会他人之痛苦(而非从好莱坞电影、上网Google,或昆德拉误解小词典的,让人不寒而栗的“爱”)…… 我觉得隐藏在我这世代心灵图像后面的瘟疫,无感性无同情无理解他人痛苦之能力,真正可怖的反而是大江《换取的孩子》里,那个被地底小精灵抱走,而伪换惟妙惟肖的冰雕小弟弟。
如何在上万眩目的赝品中,换回那个“真正的”、“未来的”婴孩。 “胡”这个身份给我极具创造力的一个视野。
我觉得那种意识到无论个体如何努力,终无法进入一个“想象群体及其文明”,其实是一种学习。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们给予《西夏旅馆》这个肯定和荣耀。而我更深深祈盼,这个华文小说最高的荣誉,不只是每一个各自孤独奋力创作的小说家们的“红楼梦”,它更是给华文小说“下一轮太平盛世”,交换不同身世、记忆、不同心灵史的“梦的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