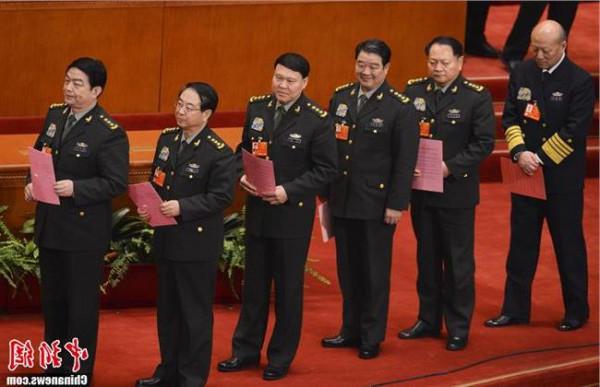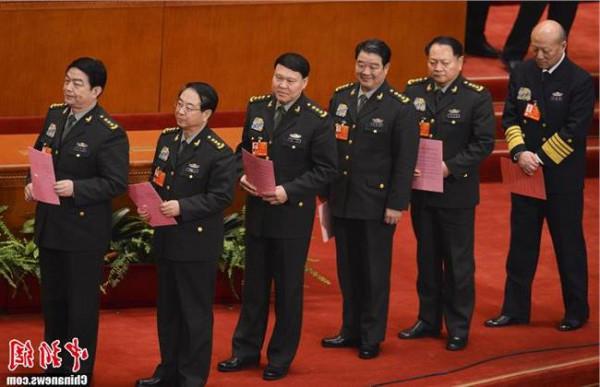黄克功简历 黄克功案的历史与法理
1937年10月的一个夜晚,陕北延河边的几声枪响,初始似乎并未引人注意。直到第二天,一夜未归的陕北公学学生刘茜,让人觉出一些异样。她的同学董铁凤去抗大找寻未果后,在回校的路上猜想,“或者黄将她关了,或者将她打死了”。(《董铁凤的证词》,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15-543)
随着延河边刘茜的尸体被找到,事情很快就震动了延安城,也吸引了来自全国的目光。因为枪杀案件涉及恋爱、婚姻等敏感话题,又牵涉军队现职人员,很快受到重庆国民党报界、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这个案件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黄克功案”。
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法治建设的任务更为紧迫,这件在当时轰动全国的案件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12月4日电影《黄克功案件》的公映,可以说恰逢其时。然而,电影毕竟对案件进行了艺术处理,我们需要重新通过档案回归历史,仔细品读黄克功案的历史与法理。
现存黄克功案的相关档案,主要集中在编号“全宗15-543”的《毛主席、边区高等法院关于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刘茜案的材料》中,该档案原件现已移送中央档案馆收藏,陕西省档案馆保存有影印件。该档案包含此案的判决书、毛泽东的信、刘茜的死亡验伤单、证人证言、来往书信等。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是陕西省档案馆近代部分的大宗,编号“全宗15”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黄克功案”在此下专作目录,单独编纂整理,足见其重要性。此外,陕西省档案馆于2001年还收到被害人刘茜家属捐赠的部分历史文献,包括刘茜摄于1934年前后的多幅照片及当时寄给哥哥董家宝的亲笔信件,反映了刘茜奔赴延安时的感想和沿途见闻,这些史料也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佐证。
红军黄克功
黄克功,时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这一职务看起来像是学校里的一个学员,或者是政治委员,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军事院校的普通学员。依据现有文献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红军将领黄克功的早年经历。
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南康县的黄克功,少年时就参加了红军,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黄克功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战役,已经表现出超出一般人的军事才能。后来,黄克功又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多次参加战斗,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等著名的战役中立过功勋,肩部等多处负伤,可以说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战功卓著。
红军到达延安后,他又多次参加战斗。由于出众的军事才能,黄克功在军中成长很快,从红军战士、排长干起,历任连长、营政治教导员,红1军团第4师第11团政治委员,尤其是担任红军师团政治工作,更体现了党对他的充分信任。因此,他年仅26岁,就出任了正团级干部,即便按当时的标准,也属于年轻有为者,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不过,黄克功调任红11团政委后不久,红四师就经历了一次干部调整,包括黄克功在内的原任干部被调入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原来优秀的学员都被留校担任大队队长。抗大“大队长”的短暂经历,只不过是黄克功人生坦途上的一个小曲折,他很快就要上战场,再立新功。即便是抗大,作为大队长,他也不仅是一个“学员”,更因丰富的战斗经验,参与了学校的教育管理与教学工作。他既是学员,又是教员。
青年董秋月
黄克功案的另一主角是刘茜。实际上刘茜是化名,她本名叫董秋月,出身山西望族,祖父是董崇仁(字子安),民国初年即任晋南镇守使,掌握半个山西的军政大权。董秋月的父亲董晋魁虽未担任官职,但因家世优越,亦过着小康生活。
董晋魁的第一位妻子生下一女后,因为感染产褥热不治身亡。他续娶了高荷清为妻,婚后第二年生下一子,取名董家宝,后于1920年深秋生下董秋月。作为家中的小女儿,董秋月自小被董晋魁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抗战之初,作为民主的、抗日的根据地,延安很快就成为全国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由于希望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太多,陕北公学不得不于1938年1月致函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函称:“来信询问‘陕公招生’的人是太多了,本处实答复不暇。故奉上此信及另外简章一份,敬希在贵刊发表为盼。”
附信陈述了延安物质条件匮乏,无力扩大办学,为了“不愿使求学心切的青年失望”,商请西北青年救国会在西安附近的云阳办短期“青训班”,建议青年人到青训班就学。不久,青训班的学员就超过万人,经短训后的不少年轻人转赴延安。
董秋月便是无数向往延安的青年人之一。由于董晋魁保守的性格,董秋月幼年被关在家里做女红,没有机会上学。后来,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姨妈刘映荷帮助做工作,她才得以进入太原友仁中学读书。上学期间,恰逢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她在学校参加了“民先”组织,编写抗日宣传材料,思想非常积极上进。
那时董秋月就给自己起了笔名“刘茜”,“刘”是引导她成长进步的姨妈刘映荷的姓,“茜”则是象征革命的红色染料茜草。抗战爆发,在万千青年奔赴延安的背景下,刘茜于1937年8月即舍弃了舒适的家庭和学业,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重重封锁线,抵达延安,应该说殊为不易。于是,历经艰辛到延安后,她就正式以刘茜为名,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亦表明与旧的封建家庭彻底决裂。
延河边枪声
在延安,在抗战的特殊岁月里,董秋月与黄克功这么两个原本不可能有人生交集的人相遇了。1937年,黄克功26岁,董秋月只有16岁,一个是战功累累的青年将领,一个是充满理想的革命青年。不可否认,在只经历过学校、家庭简单生活的青年学生刘茜眼中,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黄克功是令人“崇敬”的,虽然“崇敬”与“爱”还有很大差距。
而在久经沙场的青年将领眼中,活泼又上进的革命女青年是十分可爱的,特别是在当时延安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社会环境下。
1937年8月,来到延安的刘茜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被分配在15队,队长便是黄克功。恰好,刘茜的住处又与黄克功相邻,在相互的爱慕下,两人不久就进入了一段短暂的热恋。在往来信件中,刘茜称黄克功为“小阳”“我爱”,自己则署名为“黑格格草”,信中不乏甜言蜜语:“你一定在挂念着我,我也在想着你,爱的!”
但随着两人接触时间的增多,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习惯和理想很快使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刘茜渴盼的爱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恋,在信中,她说:“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这件事,这里许多人都知道了,真讨厌啊!”“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黄克功则更实际,因战局紧张,更急于建立和拥有婚姻家庭。他用送钱、送物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但遭到了刘茜的婉拒。在另一封信中,刘茜表明爱情需要两人共同的认识和意志:“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用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
”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刘茜在信中说:“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她表达了更广博的爱情观:“我们还是谈谈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刘茜给黄克功的信》,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15-543)
这样的婚恋观,显然是黄克功所无法接受的,他还是期望早点结婚。刘茜曾对陕公的同学、好友董铁凤说,她对黄克功最不满意的便是“觉得他只认识一天,便要求她结婚”。尽管这样想,但一个年仅16岁的青年学生,毕竟对婚恋之事缺乏经验,更不知道如何表达心意,“含混的拒绝态度和方式”反而使黄克功感到了隐约的希望。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刘茜等转入陕公继续学习,两人关系开始疏远。性格开朗又具现代思想的刘茜,因工作和学习的原因,在陕公与其他男生不免有些接触。这些事传到黄克功耳中,导致他妒意横生,甚至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并因此追问刘茜。刘告诉他“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
此后,刘茜又以多种方式拒绝黄克功,而黄克功似乎深陷爱河不能自拔,刘茜不理他,他竟然气得不吃饭,甚至不能入眠。刘茜听闻后,又去信劝慰:“来信可以看到你的情感十足之盛。朋友,你的理智呢?为了一个人而失眠,值得吗?你简单把恋爱看成超过一切了,冷静点!”之后,黄克功又连写三信给刘茜,刘回信一封表示拒绝。黄克功又到陕公找过刘茜几次,但没有找到。
是年10月5日,黄克功携带手枪,与抗大干事黄志勇一同外出,在陕公附近碰见刘茜、董铁凤等人。黄克功支开董铁凤等人,约刘茜单独谈话。谈话显然没有实现黄克功的愿望,刘茜的再度拒绝激怒了黄克功。
黄克功在法庭的陈述书中说,她“眨眼无情、恶言口出……谓今晚你不杀我,我即返校报告你拦途劫抢”。这些话更让黄克功倍感痛苦,深受刺激,于是枪响了。后来,现场捡获手枪子弹壳两颗,子弹头一颗。勘验结果表明刘茜身中两枪,第一枪为擦伤,第二枪是致命的。
死刑的法理
1936年以来,逐渐在延安站稳脚跟的中国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以及革命战争的锤炼,思想更趋成熟。在法律思想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教育感化”的新刑罚观,迥异于之前盛行的“报复性”刑罚观。新法律观重视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更注意从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立场来看待犯罪,施行刑罚。
曾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王子宜在一次司法会议上提出:什么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假如不当人看待,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
(王子宜:《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总结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8-5-85)在这样的法律思想指导下,边区一度废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死刑也极少使用,仅在颠覆政权、破坏抗战、间谍、抢劫等重大犯罪中保留有死刑。
1941年,有关边区刑法的一篇文章谈到:边区废除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五年……死刑,(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根据地……它是联合各军各派各阶层而对付当前共同的敌人(日本)——所以边区对给一个犯人判死刑,一定是到了万分的无可争取,一定是大多数群众的要求,虽然是这样,而仍需要以十分审慎,因此边区对于判处死刑的数目字,差不多到了零号。(朱婴:《边区刑罚的特点》,《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就黄克功个案论,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些人认为陕甘宁边区刚刚成立,刑法等尚未制定,黄克功案无法可依。针对“杀人偿命”的天理式刑法观,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抗大训练处处长李兴国就搬出了苏维埃时期的《红军纪律暂行条例》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刑法草案》。
前者规定“犯恶罪者,则为入于军事刑法以内”;后者则对“故杀同志”的行为,特别规定,“曾受苏维埃功勋奖章或在革命战争中负伤或社会成分为工农贫而犯本刑法者,得酌量其犯罪情况而减轻之”。
包括黄克功本人在内的一些人甚至还提出刘茜“玩弄军人”,“刘先允结婚,后反悔并拒绝结婚是玩弄革命军人”(《庭审笔录》,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15-543),这几乎要有破坏抗战的嫌疑了。这些质疑不能不说是构成对其定罪量刑的重要挑战。再加上黄克功屡有功勋等因素,为其减轻刑罚留下了十足的想象空间。
在边区之外,嗅觉灵敏的重庆国民党报界很快捕捉到了这一消息。如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日报》就对黄克功案件大肆渲染,称之为“桃色新闻”,并借机指责中共和边区政府搞“封建割据”,边区是“无法无天”。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我们也能从毛泽东与西方记者安娜的对话中看到重庆国民党媒体的观感。“中央电台已经广播了,延安发生了桃色凶杀案。”她引述报道说,“广播说,在对日决战时期,共军一名高级军官黄克功开枪,打死拒绝与他结婚的十六岁女生,此事震动延安,民众愤慨,说黄是井冈山的赤匪,匪气不改,看共产党如何处置……”这些外部舆论,在国共合作刚刚达成,边区政府甫一成立的大背景下,也要求案件必须尽快得到公正的审判。
边区政府需要以边区司法的公正在最短时间内给予有力的回应,以确立边区政府地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当时确实有部分人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老红军干部,并立有战功,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将功折罪。黄克功本人也几次上述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主席,请求:“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心。”
毛泽东接到边区高等法院转呈黄克功的信后,于1937年10月10日复信雷经天,认为“他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革命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正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等对法治的坚持,才有了10月11日公审中死刑的判决。
从法理的角度看,陕甘宁边区不能被看作“法律真空”地带。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达成了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边区政府,属于民国合法的“特别行政区”。这意味着,民国的法律制度亦适用于边区,雷经天于1938年在《解放》发表的《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中指出:现在边区法院,取三级三审制。
县政府的承审员是第一级的初审,边区高等法院是第二级的复审,中央最高法院是第三级的终审。(《解放》第50期(1938年8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号A12-2-106)
尽管边区从争取政权独立性的角度,更倾向于争取边区高等法院的终审权,但这并不代表对民国实体法律的拒斥。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之前,边区各级法院还不时援用“六法全书”,并一直持续到“整风运动”之时。因此,1935年民国刑法第282条、第284条中“杀人罪”的条文完全可适用于黄克功的犯罪行为,其中第284条明确规定杀人“出于预谋者”,处死刑。
从边区司法的特性看,黄克功案的处理也有理有据。抗战以来,边区的司法经历了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的转变,“司法民主化”是这一变革重要的方向,司法反映人民意愿,司法保障人民权利,也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司法最大的特色。
黄克功案的审理,在法庭组成中,以陪审员的方式直接吸收群众参与审理,又通过公审的方式,让现场群众在审判中直接发表意见。在边区“大众化司法”模式中,民意得以发挥,“杀人偿命”之天理亦纳入其中,这也直接决定了黄克功案的死刑判决。
回顾历史总是令人喟叹,中共对有功将领的依法处理,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对照。1936年,胡宗南的嫡系,亦是黄埔高材生的张宗灵因无故怀疑其妻,趁其不备拔枪射击,当场杀死妻子。这样一件事实清楚、法律明确的案件,却被“和稀泥”,仅仅是处以监禁。
一年后,抗战爆发,蒋介石就借机特赦了他。张宗灵改名张灵甫,继续担任军职。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案件,却反映出两党对待法治截然不同的态度。而这,也间接决定了十年之后两党在整个国家的迥异命运。“法治兴则国兴,法令驰则国衰”,来者能不鉴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所、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