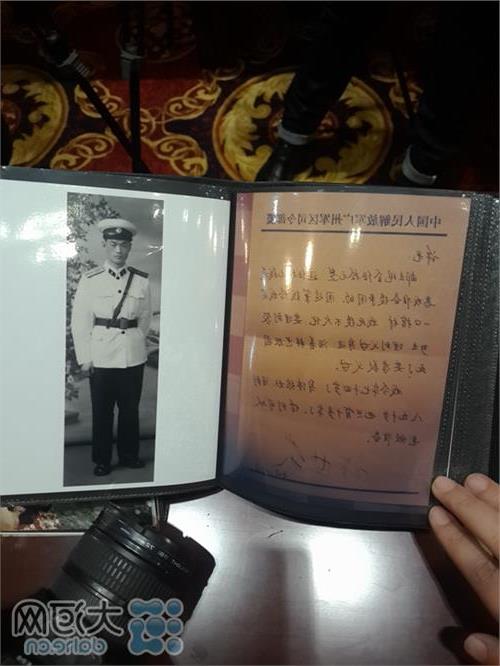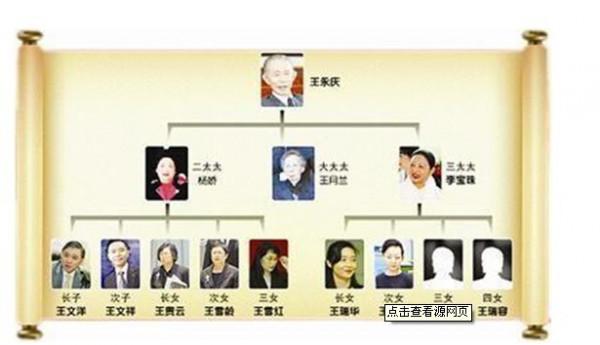许子东作品 许子东:莫言作品对文革批判尖锐 挑战文学主流
许子东:《红高粱》我那时候80年代去日本的时候,一批日本汉学家就围着我,跟我较劲,说《红高粱》里面的日本人抓到了一个老头,就剥皮,他说这个剥皮不是日本的刑法,他说日本有各种刑法,但是没有这个凌迟,剥皮这个,他说这个是你想象出来的,加在日本人的身上。
查建英:中国有。
许子东:他说是莫言想象出来的。那一批汉学家,我当时印象很深,那批日本的汉学家这么爱国,他们对于牵涉到他们文化的东西,他们很计较,但是他们也都看到了他的作品。我觉得莫言在这些地方,包括《檀香刑》里面有很多细节,它是比较粗,比方他的《生死疲劳》写的四十几天。我当年也跟他说,你这个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大的问题,大的背景的问题,大背景的问题就是莫言也好、王安忆也好,他们对于文革的否定,对于1957年的反右,甚至对于土改的政策,在文学里都有尖锐的批判。
查建英:你是从政治的角度。
许子东:从最近的十几年里,把这些文学边缘化,而且在主流的画面,继续贯穿原来的所谓《小兵张嘎》这种所谓红色经典,我觉得这个奖至少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有这么多好作家。
窦文涛:他这个角度也是有理的。
查建英:你是政治性的解读,我是文学性的解读。
窦文涛:所以说查老师这个观点,我感觉就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
查建英:什么意思?
窦文涛:我还真觉得。
查建英:你把我归哪堆儿了。
窦文涛:我瞎说一句。
查建英:他是挖坑专业的,我随时可能跳进去。
窦文涛:我认为在莫言的问题上反映了阶级问题,查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家庭对不对。
查建英:他也是知识分子家庭。
窦文涛:但是他在农村待过。你看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半、一半,我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你看,我跟你说阶级不光是政治的,阶级还是趣味、品味的,甚至于不同的阶级,可能它有不同的品味,你看我身上,我说我就算一半农民,所以我看莫言的小说可读性很强,我基本上都能看得下去,我不会像这个人说看不下去,但是我老想摆脱自己是农民,我也看几本书,所以我身上也有另一面,另一面就是我也会觉得好像语言什么的,所以我就瞎想一个什么呢,我举例,过去咱们老讲“文人气”这个词,文人气大家老是说这是酸,其实在中国古代,文人气不是指的这个,它指的是这种精神或者是一种境界,它不是说你多像,而且它这个里边反映出一种什么气韵,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我就找出一个文人化的代表,就是元朝不是有四个嘛,黄公望是一个,很有名的,还有一个叫倪瓒,倪瓒我专门找出倪瓒的画,我们可以看着说。
查建英:他这个讲的好。
窦文涛:你看,这个倪瓒,咱们外行就觉得这个模模糊糊的,这有什么好,对吧,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可是你知道,中国画讲究看了之后你生出远意,就像老干部家里挂那个对联,叫“宁静致远”,就是你看了你觉得不是那么贴近,不是那么淋漓,可是远。倪瓒的这个笔下被人称作平淡天真,笔下传递出那种悠远,甚至是萧然之意,我们把它挪用在文字和语言上,中国自古有文人气,就讲究你写的不光是故事,不光是主题,而是说这个语言本身是不是能呈现这种品味,甚至语言是非常节制的,语言除了表达本身的意思之外,能让你觉得就像人穿衣服,穿出一种品味,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大地上产生出来的作家,跟土地关系很密切的这种作家,他们不是说绝对的,不是说左右的,但是他们往往表现出跟这个不是特别认同,就是他们觉得文学的东西,我们跟这个不太在意。
许子东:当代文学概括是用一个更通俗的字,叫一派是“知青下乡”,一派是“农民进城”。阿城就是“知青下乡”,韩少功,阿城。那个莫言就是“农民进城”他就把农村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泥沙俱下的东西来批判城市,某种程度上沈从文也是“农民进城”所以周作人那种就是文人下乡,但是“农村进城”又有不同的路相。贾平凹这个农村进城他后来渐渐个人性格有关系,他就有文人气的学习。
窦文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懂,因为我也不懂外语,我不懂得中国所说的这种文人气,中国人追求的这种宁静致远的这种逸韵,诺贝尔评委会他们懂不懂这路,这也是一个审美范畴。你好比叫你说的,相比之下,似乎感觉到你比如也有人往好里说,说莫言这个人人家没有学者气,没有才子气,就是很朴实,像土一样朴实的农民,这是一种审美,但是相比之下我们也可以说好像贾平凹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文人气,阿城更是,甚至王朔,你别看他写那个小说,我认为王朔有文人气,甚至咱们说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写那种60年代的这种小说,他也是文人气,我不知道怎么说清楚这个概念。
查建英:其实西方也有。
窦文涛: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查老师,你接着我这是瞎白话。
查建英:不,我觉得你讲的很好,触及了很多问题,文人画你讲的这个,比如要用枯笔,要用留白,你不能画的太满,要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其实这都不是民间的那种,比如你要画一个年画,怎么能是这样呢,你要喜庆,北京话讲要现活儿,这颜色要饱满、要亮,什么叫不白不红,这叫什么,你就得大红,这是两种。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高低,说实话,我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阶级偏见,虽然我可能有显好,但是确实就像你们俩人都说的,子东也说,知青下乡以后,他了解了民间,他还带着一些本身的习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可能画一个萝卜、白菜,但是你愿意画得它很雅,你可能画一个村姑的衣服,但是你画出来还是很讲究的,还是有一个样子的,我喜欢比如说东北乱炖,你在一个大雪纷飞,在东北的热炕头上烧的暖暖的,但是你不要给我搞的到处我都各应,弄的好像很不讲究,我觉得就是这种区别了吧。
许子东:同是1985年出来的两个写乡土的作家,韩少功就是一个学生下乡,他的《爸爸爸》不管怎么样,他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角度。
查建英:他本来就是。
许子东:来观察中国的文化的根,可是莫言他真的是带着另外一种力量,你知道他《红高粱》最后怎么写的?我愿把我的心,我们的心都被酱油腌了,我们用来祭祖宗,这个很粗犷,很不讲道理,它是极有魅力。周英雄(音)台湾那个评论员,陈映真也是,他从来看不起大陆的文学,直到莫言的小说出来,他说不得了,这个超过我们台湾了。他这种气魄。
窦文涛:这个审美,你比如就像我给你看的倪瓒的画,那咱们外行就觉得这有什么力量,看都看不清楚,传递出来的那种逸韵。
查建英:包括他们说到,而且说他是鸡蛋和石头这个,他生来就是鸡蛋,只有你是高墙,或者你很强势,你才站在鸡蛋一边,就是村上春树和莫言这个不同,人家生下来已经不同了,我就是鸡蛋,你还要我什么,我就是要变成鸡蛋,有什么,很正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