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话剧 谈谈夏衍的“第一个剧本”——析话剧《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谈谈夏衍的“第一个剧本”——析话剧《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谈谈夏衍的“第一个剧本”——析话剧《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显现出他平淡朴实、自然深远的艺术风格。作者截取的是上海某弄堂房子五户小人物一天生活的横断面。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反映历史的黄梅季节,传递出“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
”(《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对于这部剧作,夏衍曾说:“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摸索。
”正如他所说,《上海屋檐下》的确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各有各的不幸和苦楚。报贩李陵碑因独子捐躯沙场,晚境异常凄凉,只能酗酒解闷,孤吟消愁;耿直的知识分子黄家楣,失业居家,恰逢老父远道来视,不免悲喜交集。
为博取培育自己的父亲的欢心,不惜典衣当物,借债度日;海员之妻施小宝,更是无依无援,为流氓小天津挟持,被迫沉沦堕落;相比之下,小学教员赵振宇和工厂职员林志成的生活稍有着落,但赵妻在生活煎迫下,时有衣食住行的愁虑,林志成也要担心饭碗是否牢靠。
他们在抗战到来之前,都过着苟且麻木、忧郁悲伤的生活。沉重的黑暗缩短了他们的目光,扭曲了他们的性格。
他们在咀嚼自已不幸的同时,往往向更弱者转嫁自己的不幸。赵振宇夫妇在卖菜者处获得若干小便宜,竟“露出微笑”。林志成、黄家楣不堪忍受社会的折磨,妻子就成了发泄自己苦痛的对象。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弥漫着庸俗、灰色的小市民气息。
夏衍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在于,既嘲讽小人物思想性格的弱点,——但仅是含泪的微讽,——又清醒地看到,小人物的种种不幸和畸形社会的黑暗投影。他把艺术的锋芒指向病态的社会。对小人物的善良正直本性,从来是肯定的。
且勿论林志成处于亦“牛”亦“狗”的境况中,内心是多么痛苦,一旦“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面解放出来”,又有多少兴奋。即如有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消极思想,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无味生活而意足的赵振宇,也终究不能无视李陵碑的被人欺辱。
小人物内心的善与社会的恶的冲突,与自身卑琐思想的矛盾,如同一股股潜流,在奔涌激荡。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催他们觉醒的萌芽。因而,他们不甘久安平庸的生活,在怨愤、挣扎之中,就包含着对历史的黄梅季节的厌倦,对新的生活的一丝向往。
早在二十年代初,在小说《故乡》里,鲁迅就借“我”的口道出自己对劳苦大众的深厚祝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夏衍承继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不仅悲小人物之悲,更努力增添亮色,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那就是革命知识分子匡复和葆珍、阿牛几个孩子。如果说,在剧本中,小人物不是新的生活的开拓者,那么,这些新的人物就犹如“灿然的阳光”,射进了浸透霉气的可诅咒的生活。
有了他们,小人物摆脱苦难生活是可能而且必然的。戏剧的主线是林志成、杨彩玉以及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匡复三个人的感情纠葛。革命者匡复入狱,把妻子女儿托付好友林志成照顾,林在与杨长期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组成了家庭,而匡复的归来,使他们三人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作者无意把任何一个塑造成恶人,而是强调现实环境对人的折磨。林志成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了与朋友之妻组织家庭而过着自己不情愿的“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生活,并备受良心的谴责。
杨彩玉曾经是一个热情的,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离家出走的少女,生活的磨难使她变成了劳碌、庸俗、苟安的家庭主妇。
而在监狱八年受尽磨难,渴望从妻子、女儿那里寻找爱抚的匡复,面临的是妻子与好友同居的残酷现实。他们身上都带着过去留下的创伤,但新的力量也在阴郁的环境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匡复的归来使杨彩玉重新回忆起火热的青年时代,消沉的心焕发新的活力;女儿欢快的歌声使匡复重新恢复战士的激情,他毅然重新出走,割断缠绕自身的绵绵情丝,是为了告别沮丧的婚姻。
在主线一侧,穿插了教书匠赵振宇夫妇一家、农村娃黄家楣一家、妓女施小宝和流氓小天津、兵哥父亲李陵碑等等,一副上海生活画面层层展开。
志成,是弱者里面的一个! 剧中你,我,他,都是弱者!戏剧结尾葆珍与阿牛领着大家唱“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
救国家!”号召人们不怕“碰钉子”,不做忍辱负重“没有的大傻瓜”,而应“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具有促人振作、给人希望和信心的作用。这声音也压倒了李陵碑悲哀的曲调,激发人们从压抑、沉闷的氛围中走出来的决心。
《上海屋檐下》在戏剧结构上颇有特点,通过主副线的形式将五户人家的家事,五股相互交错的生活之流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舞台上,充分体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每一个家庭中独特的生活旋律,共同构成了一个曲折多变、内涵丰富的乐章,体现了特定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具有较大的涵盖面。
诚然,作者寄托希望的人物,也有若干缺点或不足。夏衍对剧中的人物、事件不作任何情感表示,不对它们指手划脚,而是将一切客观地展示出来,将裁判的权利交给观众和读者,让他们来评判。
剧本似乎只透着剧中人物的悲喜欢忧:杨彩玉的无奈两难,李陵碑的变态潦倒,施小宝的求援无望,林志成的烦闷和惭愧等等。作者的感情似乎丝毫都没有介入,其实并非如此,实质上,作者渗透在剧中的情感是炽热而强烈的。
作者始终怀着强烈的爱憎之情,细致深刻地体会着生活,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这样剧本显得更加真实,没有呐喊与高呼,没有呼天喊地的哭诉,整个舞台气氛是非常平淡的,但这种淡又并非是淡而无味的,读者与观众都明白:那样的生活与黑暗、反动的统治是分不开的。
“淡化的情节”是《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另一表现。普通市民生活这一题材类型决定了这一点。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不是险象环生,充满着种种激烈的矛盾的。
它更多的是平平淡淡,寻寻常常。非常平淡而又普通的一天生活能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呢?因而剧作家并不追求情节的紧张,而是多方处理,缓和剧中即将出现的戏剧种种冲突。
如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的情感纠葛,如在其他剧作家的笔下,很有可能被处理成浓烈的戏剧冲突。但在夏衍笔下,这一戏剧冲突被冲淡了,淡得出乎意料。作者有意避开浓烈的场面,使匡复、杨彩玉、林志成三人不出现在同一舞台空间。
匡复找到林家时,杨彩玉出去买菜了;杨彩玉回来了,林志成却又被拉到工厂去了。当三人再次见面时,观众关注的焦点又转移到了林志成的工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冲淡了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不仅仅在林、匡、杨三人的身上,在其他人物形象,如施小宝与赵妻及小天津之间等等都采取淡化戏剧冲突的方法,突破了传统戏剧情节高度集中的限制。
作者意在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的展示,淡化戏剧冲突,调和生活矛盾,用舞台形象来引导人们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把握生活的本质,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活的思考:人不能这样活着!
作者以独特的现实主义手法,淡化戏剧冲突,以异常冷静的态度,客观而不动声色地描写了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展示了小人物的性格、心灵和悲惨命运。
夏衍说他写戏“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直到写《上海屋檐下》之前才“认识到戏要感染人……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所以作者说是从《上海屋檐下》才“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因而把它称为“第一个剧本”。











![包身工夏衍猪猡 包身工[夏衍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https://pic.bilezu.com/upload/d/4a/d4aaa53b392fcb5d1be3eb362a04d7e1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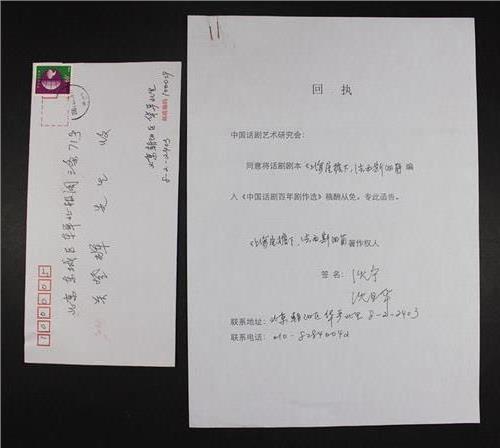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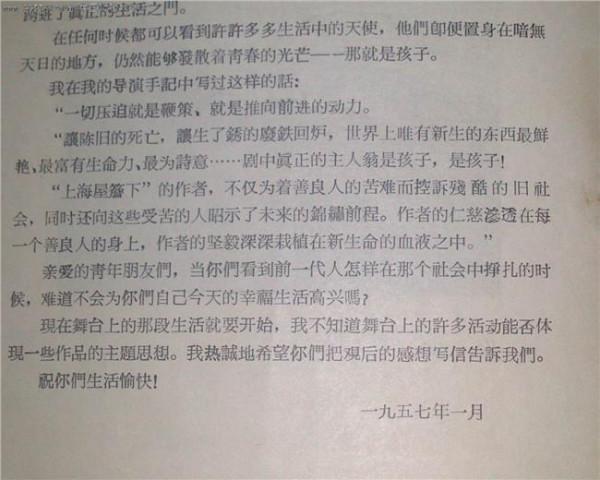

![>周斌复旦大学 周斌[复旦大学教授]](https://pic.bilezu.com/upload/d/7d/d7d15cee01645085ac2cfd3310bd4f7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