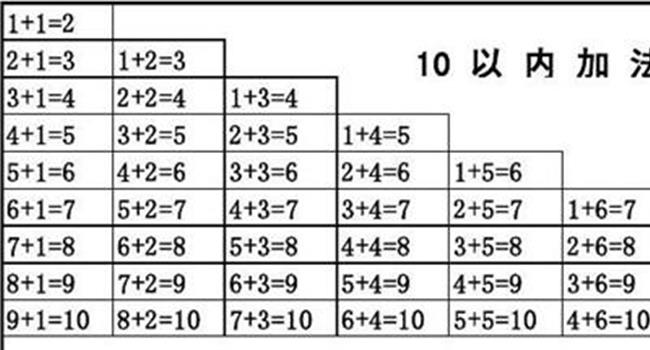堂堂正正打一肖 上海星期日工程师:从“偷偷摸摸”到“堂堂正正”
30年前,一则“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的百来字消息登上了解放日报头版。从感觉“偷偷摸摸”到“堂堂正正”,“星期日工程师”们走过了一条颇为跌宕的心路。
科技人员能不能兼职?业余劳动的收入是否合法?“星期日工程师”韩琨的遭遇,曾在全国范围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事情还得从1979年说起,当时上海郊区奉贤县一家工厂连年亏损,打算开发新产品。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受聘担任了技术顾问,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赶往奉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使得该厂绝处逢生。不料,因为3400元劳动报酬,他以受贿罪被检察院起诉。最终,韩琨的行为被中央政法委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人才难以自由流动,生产力第一要素得不到完全释放——这曾是历史的真实。星期日工程师的出现,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犹如冰冻的河床在春寒料峭中开始暗流涌动。
【亲历者说】
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挥余热了

刘忠云(原上海华通开关厂高级工程师):我今年75岁,算得上是一名至今还在一线的星期日工程师。1964年,我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作。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开关厂,方圆一平方公里,有6000名员工。
那时候,上海和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刚起步,技术是个门槛,总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过来。我都是悄悄地去做,不好给厂里晓得的,我自己也很注意,用到的技术和厂里的工作是完全不搭界的。1988年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简称星工联)成立,提倡无边界服务,我很自然地就加入了。
不夸张地说,当时一些遭遇困难的企业找上门来,都把我们这些工程师当“财神”。“又去‘扒分’了!”总有人这样半真半假地说。那时候做星期日工程师,我的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生活条件也确实比一般家庭要好。但我更看重的是,有一技之长,能为社会多做点事情。
我记得某个夏天,安徽芜湖供水总公司一台600千瓦的进口电机坏了,没人会修,全市二层楼以上几乎都停水了。十万火急之下,他们向星工联打来了求援电话。我立即组织上海的技术力量赶到芜湖,通过“会诊”列出了需要解决的9个问题,最终抢修成功。那些年,我还经常去甘肃、新疆、内蒙等地,为当地钢厂、矿山等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好几次因脑缺氧昏倒,最严重的一次造成手臂骨折,我却还是乐此不疲。
星期日工程师对社会来说是个“补缺”,人才本来不好流动,突然有了一块“自留地”,生产力一下就释放了。这就好比卡拉OK,憋了许久终于唱出来了,我还是蛮怀念那个时候的。如今,我租了一间旧厂房当工作室,每周至少去3次,有时忙起来在施工现场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尽管现在很多设备都有售后服务,但社会对于工程师还是有需求的,比如一些设备需要升级改造。等到哪天思路不清楚了,就不做了,回家读我喜欢的唐诗宋词。
庄瑞云(大学教授):在加入星工联以前,我在学校里教书搞科研,总觉得人生还缺了点什么。1992年,苏州市吴县黄桥镇占上村找到了星工联,这个村以前主要是做鞋垫,想要对接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项目,改变贫困村的面貌。
我第一次到村里去,他们扛着红旗、敲锣打鼓来迎接。我在学校教的是厚膜集成电路课程,这个工艺当时在社会上也很稀缺,于是我指导村里建了厚膜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不到两个月,就创建了一个高科技微电子公司。那时候,我差不多一周要跑三次村里,一大早先搭火车到苏州,然后骑上寄放在火车站附近的自行车往村里赶,一路都是土路,颠簸得很,要骑上一个多钟头。
记得当年在火车上,经常看见和我一样背着挎包去往长三角的星期日工程师,虽然素不相识,但遇到了都会用眼神打个招呼。
那个年代,计算机还不普及,生产线上所有的图纸都是我手工设计,熬通宵那是常事。组装设备时,也是我自己钻到炉子底下去接线、焊接。虽然条件艰苦,但心里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觉得特别来劲。看着课本上的东西变成了真正的产品,我第一次尝到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乐趣,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当时,这家村办企业很快就接到了一家知名公司的程控交换机用户电路的订单,以往他们都是依赖进口。紧接着,又接到了大批量电动工具调速电路的生产任务。一时间,订单太多,都来不及做,企业第一年就达到了120万元产值。12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上世纪9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有个几十万元的产值就很了不起了,这120万元的产值轰动了整个吴县。
白海临(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原秘书长):上世纪80年代,浙江湖州的乡镇企业想制造电视机,但面对接收信号的高频头技术犯了难。我当时20多岁,在上海星际无线电厂工作,企业先来厂里取了经,又邀请我们到当地去上课。
那时候每周只有星期日休息,于是星期六下班后,我和一位同事在十六铺码头乘船赶到湖州。上课的教室设在了大祠堂,依然挤不下,就把大喇叭拉到院子里。吃饭时,乡镇领导来了,最有威望的老红军也来了。临走时,对方塞来200元,这可是一笔“巨款”,那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才40元,实在不敢要。
对方说什么也要我们拎回一条黑鱼和一只甲鱼。不知咋的,两条鱼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支部书记还专门找我了解,让我写了一个情况说明,我当时正申请入党,还是蛮紧张的。后来,支部书记把这个情况说明还给了我,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之后,机缘巧合,我来到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工作,见证了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的成立,这应该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星工联组织之一。报名消息传开后,科学会堂一下子挤满了来报名的人。有一位工程师,早上三点多就起床从闵行赶来了。
她说业余时间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但不知如何去做,现在机会来了。还有一位因业余兼职遭遇过麻烦的工程师感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挥余热了。3000多人报名,最后注册的是1700多人,但全市的星期日工程师我估计有好几万人。
【四十年来】
一块“金字招牌”
南昌路47号,这是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所在地。就在它成立前的4个月,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尽管韩琨事件促发了对“人”这一生产要素的松绑,但社会上关于人才、技术的不同看法乃至冲突还时有发生。白海临回忆,星工联刚成立时,一些工程师不愿意留下单位联系电话,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顾虑。星工联首任会长、中国电光源科学泰斗蔡祖泉,生前曾说过:“我那时心里也不太踏实,成立大会上市委市政府领导在主席台上一坐,我的心才放下来了。
”上海工业用呢厂技术人员胡汉荣,加入星工联后,经常乘长途车到太仓去指导企业。有一天,他在车站发现身后一直有厂里人在“盯梢”。星工联几次派人到他的厂里沟通,说明他的行为是国家允许的,这才得到理解,不再有“盯梢”的事了。
逐渐地,当星期日工程师成为一支“科技轻骑兵”,并为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之时,冲突自然就少了。某船舶公司为外商加工一批高压管道法兰,由于对工艺难度估计不足无法完成,眼看要赔偿违约金四十万美元。星工联接到求援后,组织力量协助进行技术攻关,最后企业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不但没赔,还盈利十万美元。
由于一大批外文资料来不及翻译,1992年市政重点工程中山北路内环高架的进度受到影响,星工联组织多学科专家突击翻译,只花了八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一年夏天,上海一家化学品仓库接二连三发生醋酸爆桶,保险公司中午12时急切请求支援,下午2时星工联专家已出现在勘查现场并提出一系列防爆措施,迅速控制了局面。
星期日工程师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上海淮海照明灯具厂是一个区属小厂,工艺比较落后,原材料消耗大,蔡祖泉几次到厂里指导改进工艺,就使得原材料节约了70%;胡汉荣担任了太仓工业用呢厂技术顾问后,仅用了半年业余时间就使得该厂的合格率从40%提高到了95%,当年企业就扭亏为盈,增加效益330万元,荣获轻工业部的金龙腾飞奖。
星工联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人才的创造力不再专属于某个单位,开始流动起来。不同于以往的单打独斗,星工联涉及多学科,完成了单个工程师难以胜任的工作。“我们为多家企业做了风险评估。就拿宝钢风险评估来说吧,当时保险公司要求一年左右时间完成,我们组织多名专家,用了一个半月就拿出了高质量的评估报告。
宝钢还为此专门开过现场会,非常认可我们提的整改意见。”现星工联常务副理事长、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梅向群说,星工联的服务项目多时达到1300余项,并获得过中国科协颁发的科技咨询最高奖项金牛奖。毫不夸张地说,苏浙沪地区一些乡镇企业的第一桶金,也包含了星期日工程师的智慧。
记者翻看过去的报纸,即使在2000年的郊区宝山,星期日工程师都还很“吃香”。那里的专业技术人才市场十分热闹,不少在职工程师公开到市场登记,寻找工作之余的发展空间。月浦镇还建立了星期日工程师制度,聘请宝钢的专业技术人才到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指导。
今天,星工联的活力已大不如前,星期日工程师这一称谓,在年轻人听来陌生而又疏远。市场经济更成熟,人员流动成常态,星工联原来所具有的保护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作用也已淡化,其使命是否也就结束了呢?采访中,一位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不会。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转化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科技中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说,星工联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中介组织。
20年前,年仅29岁的乐群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名星期日工程师,如今他已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有一个想法,他已经酝酿了6年,那就是打造一个“技术服务的淘宝”。就在采访当天,他还约了合伙人谈这事。“现在比以往更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革新,以及流程的技术改造。
如何利用互联网,为年轻工程师提供项目、再教育和法律保护,甚至是融资服务,可能会是一条新的路径。我打算第二次创业,正在申请注册一家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在乐群看来,星期日工程师身上有一种情怀,那就是学有所长服务社会,他想把这样的情怀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