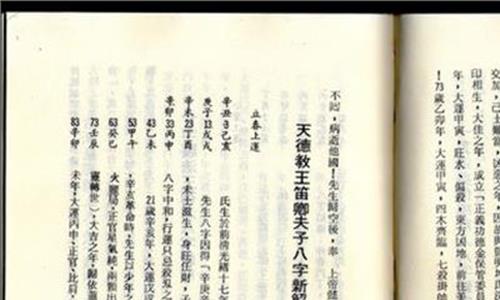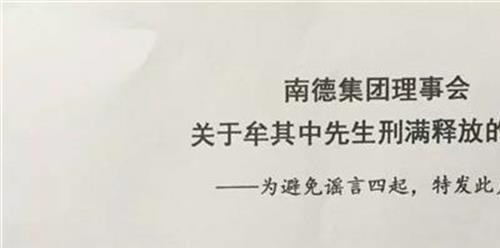牟宗三良知坎陷 牟宗三的“假定”困境: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
经济有经济内在的独立法则,而政治亦有政治内在的独立法则。光从修身齐家这个道德法则(moral law),推不出经济和政治的法则。道德法则和政治法则不一样,和经济法则也不一样。这三个法则各有其独立的意义,这就是现代化的精神。
假定要充分的展现现代化的意义,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历史上出了多少圣人,讲文化讲得如何高妙,都是没有用的。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可由此看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
经济现代化,就能够迫使我们必然地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假定经济不现代化,那么政治上要求现代化,要求自由民主,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辩不清楚。……所以,政治现代化,必从经济现代化着手,而由经济现代化进至政治现代化时,所表现的自由民主,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
这就是所谓敞开的社会(open society)。 私有财产与自私是不一样的。自私是罪恶,私有财产是人格尊严的一道防线。
人之所以为人起码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由他人干涉,不由政府支配、控制。……同样,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也是不一样的。人只有在自由经济的制度才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为社会创造财富,经济才能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了,便也可连带地促进、加速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 经济建设最容易,因最具有实质性,同时也最单纯;政治建设因牵涉到的方面太多,必须要解决却在现阶段绝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太多,所以就比较难些;文化建设实在是最难的,因最“空洞”,最无实质性,最难在具体的成绩表现出来。
经济的、政治的现代化固然很难达到,一旦达到,也就很自然的有文化建设的要求。文化建设就是要配合这政治、经济现代化而使我们在生活中、在意识中头脑现代化,而这现代化再反过来稳固(justify, confirm)我们的政治的、经济的现代化。
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台北:联合报社1983年,第37、34-35、35、116、123、40页。
牟子讲解得非常明白,不需要另外的阐发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条柔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上升之路,而不是暴力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下贯之路,仿佛颇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亦可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相贯通。
但必须注意,牟子坚持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李泽厚也根本不能同意牟子的唯心论。其中曲折,在此不能详细辨别。 这种柔软、配合性质的良知坎陷足以消解来自右边的批评。
不过,正如坎卦所指出的那样,一阳爻落在二阴爻之中,需要面对重重险阻,其坚持必定不易。人们会怀疑,一阳爻还能坚持多久?良知坎陷能够保证道德本心不被资本主义、现代技术以及与之共谋的那种穿上新衣的极权政治消磨掉吗?良知坎陷能够保证儒学不丧失自性而变身为所谓的“西学”吗?这样的良知坎陷难道不正是向美国的投降吗?这正是蒋子从左边所发起的攻击。
面对暴力与柔顺同在、被左右夹击的局面,牟子可能也会认为,中国文化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是一场持久战。
然而无论如何,牟子的结论一定是说,绝对的胜利必然属于儒学。 三、一个“假定”:现实政治中的良知坎陷 无论是“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收缩下降堕落”)还是“摄智归仁,仁以养智”,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32、4页;《历史哲学》,第126页;《道德的理想主义》,第90页;《人文讲习录》,第111页。
同时参阅前引杨泽波老师文。
也不论是“消极地说”还是“积极地讲”,良知坎陷都表现出迥然相异甚至相反的两种面相:一种是刚性暴力的、坚持中国文化主位性的良知坎陷,另一种则是柔性无力的、向西方靠拢的良知坎陷。二者都可以是土堆坎窞,也都可以是水。
所以一方面,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暴力的良知坎陷是情感式的山洪暴发,欲冲毁一切随现代性而来的西方的土堆坎窞;无力的良知坎陷则是理智性的潺潺细流,思谋通过拥抱亲近西方的土堆坎窞来融入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二者实际上又互见:后者表明,前者对自家传统的执着最多只是一种徒劳无功的乡愁,所谓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更多地只表达着一种审美情感;前者则显示,后者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民主科学等实质上只具有工具的意义。
前者的暴力要求教化那些“庸众”(mass)或“物性的人”(das Man),要把他们从堕落气化(科学一层论、泛民主主义)中强行拖拉解放出来;后者的无力则只可以希望普遍放纵溃烂的现代人(理应包括在位权要?)还能够残留一线直立向上的人性血脉(道德的理想主义),以精神的(spiritual)道德之“贵”来自我提升。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3-154页。
这样,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争执中,牟子演绎了他良知坎陷之暴力与无力的辩证法。 暴力与无力的辩证法让政治问题深入到了儒学的内部。这里的问题是:当今的儒学主要是一种学术,还是一种政治?教政合一,抑或政教分离,究竟哪一个有资格成为原则? 牟子曾明言,儒家“德化的治道”能够“拆散”皇帝“现实上权位之无限之抓紧把持与胶固,而使之让开一步”,从而令“物各付物,各正性命”。
即是说,“让开一步”的良知坎陷是一个“定常之有”(Constant being),对于任何人,包括以前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的大皇帝等,都构成“一种制衡作用”。
这意味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即“神治形态”,它同时便即是一种政道。
牟子一方面认为无论何种政治形态,皆各有其政道(“关于政权的道理”),因而所谓“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等说法只能是一个错误;另一方面又认为“政道者政治上相应政权之为形式的实有,定常的实有,而使其真成为一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之‘道’也”,因而又判定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均因其“不能恢复政权之本性”而“皆无政道可言”,而“惟民主政治中有政道可言”。
前者只要是政权的道理,无论是力或德,也无论定常与否,均可说政道;后者则不是一般地讨论政权的道理,而只有民主政治的政权才有道理,其他的道理都是歪理。两说之间,一经一权。参阅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1、14、21、61页。
这实际上已经是以中国历史上“原始形态”的、“紧说”的“政教合一”也即“君师合一”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68页。
为极致,而将其理解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了。不过,牟子又清楚地知道,这“政教合一”的“神治形态”只是某种一厢情愿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它往往只能演变为“家-国-天下”一体的那种“家天下”的公共生活型式,而为世所诟病。
因而,牟子话锋一转: 假定相应政权有政道,民主政治成立,使政权与治权离,则此种治道当更易实现,且反而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32页。
牟子相信,政治应该有某种更高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某类人,不是“家天下”一乱一治的翻烙饼,而是为了全人类,为了“整个社会上保持一谐和之统一”,因而它应该接受道德的“限制”和“指导”。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68页。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牟子强调儒家“德化的治道”“反而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然而,“假定”二字又充分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无奈和心酸:家天下的现实政治是否愿意接受道德的“限制”和“指导”,那却定非道德所能决定。这是秀才与兵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