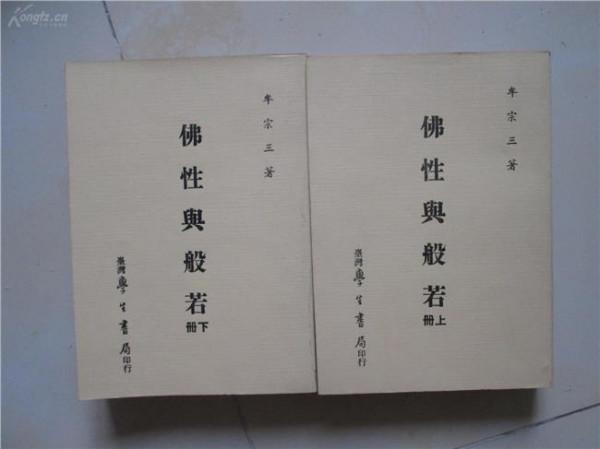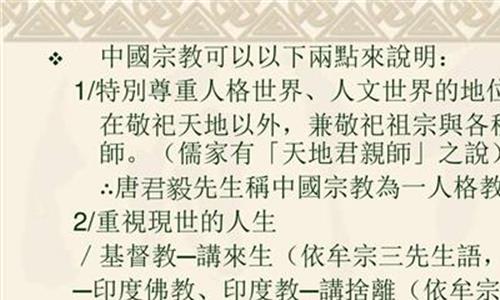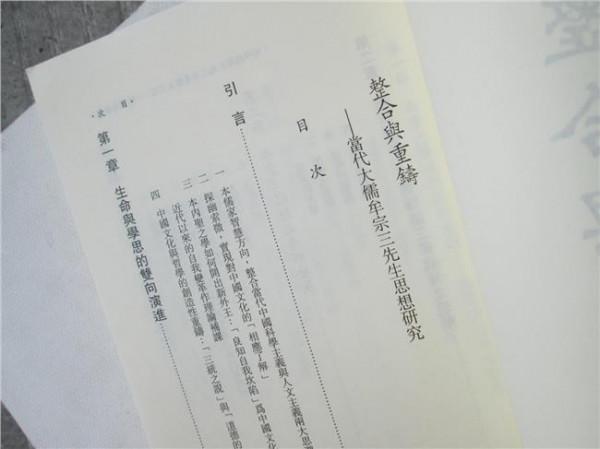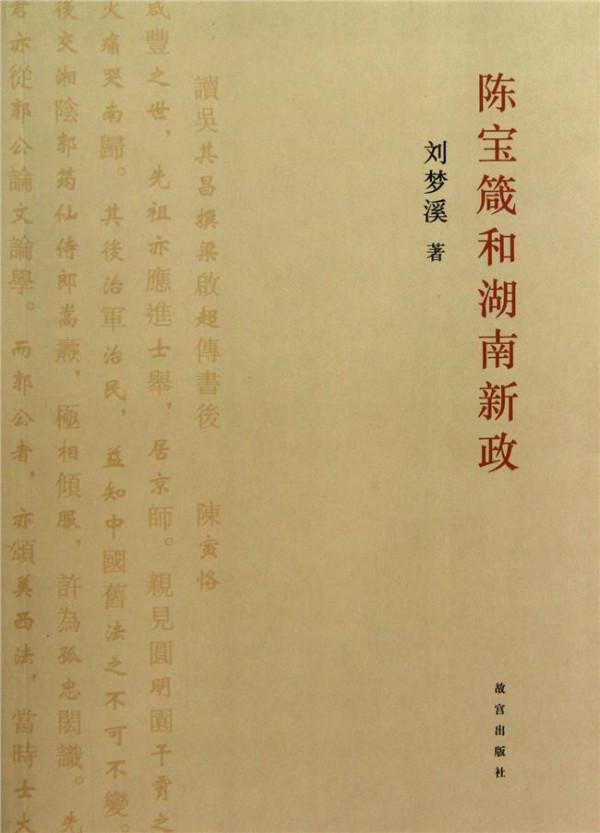牟宗三佛性与般若 略析《佛性与般若》在牟宗三哲学思想进展中的位置
《佛性与般若》是牟宗三先生六十岁以后写下的一部巨著,具体写作时间是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七年六月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全书一千二百余页,计一百余万字。此书是牟先生继《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等书之后又一部阐释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巨著,同时也代表牟先生晚年哲学思想进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过,关于此书在牟先生哲学思想进展中的位置问题,一直是牟先生的后学以及一般新儒学研究者普遍忽略的一个问题。
牟宗三重要门人之一的蔡仁厚先生在《牟先生的学思历程与著作》一文中,曾将牟先生思想及学问的历程,细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作“直觉的解悟”时期,是指牟先生三十岁以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时期;第二阶段叫作“架构的思辨”时期,是指牟先生三十、四十之间研究罗素《数学原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段时期;第三阶段叫作“客观的悲情与具体的解悟”时期,时间是牟先生四十至五十岁之间,这是对民族文化命运作悲情地了解的阶段,也是其学问思想臻于成熟的阶段;第四阶段叫作“旧学商量加邃密”,这是牟先生对传统心性之学作彻底疏导、整理的阶段,包括《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三书的写作,时间是牟先生五十至六十岁之间;最后一个阶段即第五阶段叫作“新知培养转深沉”,此阶段也包括三部书的写作:诠表南北朝、隋、唐佛学的《佛性与般若》,疏导基本存有论建立问题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融会中国思想与康德哲学的《现象与物自身》。
此阶段时间是牟先生六十岁以后的时期。蔡氏此文把《佛性与般若》同《心体与性体》等书分别安置在“商量旧学”的第四阶段及“培养新知”的第五阶段,且认为《佛性与般若》、《现象与物自身》等书代表牟先生学思历程的最高阶段。
不过,牟先生在写作《佛性与般若》前,曾写出《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九六八年),在《佛性与般若》写作中间又写出《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一九七三年),如果严格按照这三部书的著述顺序叙述牟先生“培养新知”的第五阶段,则蔡氏自当先叙《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二书,最后再叙《佛性与般若》的学术成就。
蔡氏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先叙《佛性与般若》的学术成就,然后再叙《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在中西哲学会通中的贡献。
蔡氏这种处理方式说明,他虽然依著述时间为据,承认《佛性与般若》是牟先生学思发展第五阶段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但他显然忽视了此书在牟先生哲学思想进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又,蔡氏在评述《佛性与般若》时说:“先生以中国哲学史的立场,疏导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并从义理上审识比对,认为天台圆教可以代表最后的消化。依着天台的判教,再回头看看那些有关的经论,先生乃确然见出其中实有不同的分际与关节。
顺其判释的眉目,而了解传入中国以后的义理之发展,将其中既不相同而又互相关联的关节展示出来,这就是先生撰着此书的旨趣。”即判定牟先生撰着此书的立场,是依“中国哲学史的立场”疏导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牟先生撰着此书的旨趣,则是“展示”中国佛教不同思想系统之间“既不相同而又互相关联的关节”。
依这种了解,则《佛性与般若》仅是一部诠解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纯粹学术著作,其与牟先生个人哲学思想之进展无关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