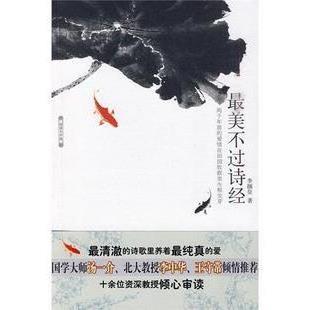汤一介三代学人 读汤一介《我们三代人》
这是一部家族史书,记述了汤氏祖孙三代的身世经历;这是一部学术史书,浓缩了中国学人在百年动荡变迁中的学术操守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守望;这是一部自传,作者以平实、中性的笔法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讲述了个人的悲欢得失及学术生涯。

读完汤一介遗著《我们三代人》之后,笔者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感叹汤一介先生的真诚和自我解剖精神,也更加理解先生为什么不屈从出版社的要求,将自己辛苦三年写好的书稿毅然放回抽屉,让其“沉睡了”十多年。也从内心感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能有如此眼光和魄力将先生的这一心血之作以原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先生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我的父亲汤用彤
如人们所知,作者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家、佛教史家、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在作者眼中,汤用彤是位慈父,“父亲从未对家人发过脾气,为人一团和气”。据钱穆在《忆锡予》(汤用彤,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在汤一介的印象中,父亲与当时的学者大都相处得很好,与朋友相聚论证、论学,从不喜争论,亦无门户之见。
“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溦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好友;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 故朋友们给汤用彤起了个“汤菩萨”的绰号。
汤一介认为,汤用彤治学之严谨世或少见。“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故其代表性作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据胡适在其《胡适日记》中记载:“此书极好。
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汤用彤这本书最高奖,父亲得知此消息后很不高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
”汤用彤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信,但对金钱却全不放心上。汤一介记得,1946年,傅斯年请父亲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亲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1949年后,汤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夫人颇不高兴,但汤用彤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汤用彤在解放前一直教书,先后在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1931年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父亲平时主要只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二是学生选课。”季羡林在世时,对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为不满,多次对人道:“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
”学生选课时,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汤用彤的学生郑昕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
汤一介先生评价祖父汤霖时说:“祖父对父亲影响最大的题词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汤用彤一生确实遵照祖父的教训,传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处事,忧国忧民。这也成为汤一介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书中,汤一介谦虚地评价自己说:“我虽无力传‘家风’,作为父亲的儿子和学生,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父辈们的友谊与追求
在《我们三代人》的第二部分“我父亲”中,作者用了很多笔墨记叙了父亲与胡适、吴宓、熊十力、钱穆、傅斯年等著名学者的交往故事。
在汤一介印象中,父亲不善交际,因此朋友并不多。“但吴宓伯父却是父亲最相知的亲密朋友之一。”吴宓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早年曾留学哈佛大学,与汤用彤、陈寅恪交往甚密,人称“哈佛三杰”。书中作者回忆,1919年6月,汤用彤从美国汉姆林大学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曾选修了白氏的《比较文学》,吴宓先期至该校,“父亲随之亦去,我想这是受到吴宓伯父的影响所致。
”留学哈佛期间,汤用彤、陈寅恪与吴宓三人常聚而谈读书及学问,吴宓在其《日记》中说:“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正因为三人志在“读书学问”,而远离“功名权利之争”,为当时在哈佛留学生中的皎皎者,故有“哈佛三杰”之称。
在吴宓之子女吴学昭的《吴宓与汤用彤》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两位大师的交往。“我父亲吴宓与汤用彤伯父相知相交,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两人都极爱好文学,并以文学的根(氏)在于思想为共识。父亲常说,非有真性情、真怀抱者不能作诗。
用彤伯父则更加明确:‘无道德者不能工文章。无道德之文章,或可期于典雅,而终为靡靡之音。无卓识者不能工文章。无识力之文章,或可眩其华丽,而难免堆砌之讥。无怀抱郁积之知识,非有天生之性情,不能得之。’”
“像老一辈学者能保持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并在学术上相互支持,是不多见的。”汤一介记得,小时候,吴宓常来家里,“每次总要抱抱我和妹妹,并用他的胡子刺我们的脸玩,我们非常喜欢他,叫他‘大胡子伯伯’。”“吴宓伯父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学者,他情感丰富、为人正直,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外经典无所不读”“我们的父辈学者都已故去,他们的为人为学有许多方面我们是学不来的。
”“我们这一辈子无论在‘国学’或‘西学’上都远远不及上辈。”“我们的后辈,看来问题更多,是否能比我们在学术上的造诣更强也很难说。……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中华民族何时才能真正复兴而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等待着。”
汤氏三代的文化情结
在汤一介先生的墓地上,一块长20多米、高约3米的墓碑矗立在苍松翠柏间,碑文上醒目地刻着:“汤氏三代论学碑”: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返本开新中会通中西古今之学,重新燃起思想火焰,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责任……
汤一介生前时刻牢记“事不避难,义不逃则”的祖训,并以“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为行事立身的座右铭。在笔者与汤先生的接触中,也深感先生为人为学之儒者风范。
他生活很朴素,对吃穿不太讲究,冬天总是带着一顶毛线帽,跟学生在一起,是先生最开心的时刻,他总是面带微笑,并勉励学生抓紧时间做学问。如其父亲汤用彤一样,先生不喜交际,不爱应酬,除了看书写书,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
在笔者印象中,汤一介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称自己是“哲学工作者”。“我们这批人在学术根底上不如老一代。”“在做学问上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汤一介在书中认真剖析自己“没有成为哲学家”的原因。
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他也曾梦想过成为一位哲学家,但是到1949年后,“我想当哲学家的梦破灭了,甚至对哲学做点真正研究的可能也因政治原因丧失了。”“我父亲自回国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的二十余年中,正是他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这应该是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间,他得以全心地做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加之他此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汤一介记得,父亲在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至少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虽然历经政治动荡,汤一介曾经有过心灰意冷,想扎在故纸堆中做些学术研究打发余生。但其内心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希望中国早日富强的愿望从来没有熄灭过。因此,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热”中,汤一介并未超身事外,凭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先后写了许多文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中国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并在大家的推举下,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终身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全面走向世界前列的努力中。
最后两年,汤先生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儒藏及其相关事务上,日程表排得满满的。虽然经常被疾病所困扰,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只要精神好一些,他就要去工作。因为“这是他最大的梦想,最后的心愿。”
值得关注的是,该书首次披露了汤一介与“梁效”的来龙去脉。这事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但在先生的心中“始终是个问题”,汤一介以其真诚、不回避问题的一贯风格对自己做了个交代。作者以其做学问的严谨态度,用纪实性的手法、中性的笔触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其学术及历史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