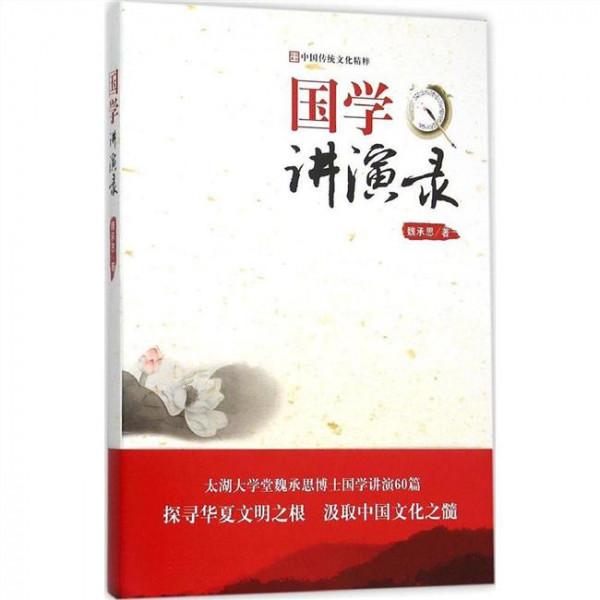牟宗三女弟子 牟宗三:《孟子》讲演录(八)
上次讲“心之所同然”。这是肯定人(照康德的说法就是一切理性存有)皆有心之所同然这个本心。这个本心是义理之心。这个“然”作动词,是“肯定”的意思,“同”是同时。“同然”就是同时肯定。再下面那一大段是讲工夫。
前面讲人心之同然,有这么一个普遍的义理之心存在于每一个理性的存有。光承认一个普遍的义理之心摆在那里,没有用的,还要有工夫,要显出来才行。下面一段就讲工夫。前面所讲都是属于实有问题,就是“性善”的这个“性”的存有问题。
说“实有”可以,说“存有”也可以。这个“有”是先天的有,每一个人、每一个理性的存有都如此。而且,所存有的这个“性”是普遍的,不是心理学的。心理学的是纯粹主观的,没有普遍性。因为它是普遍的,所以,它也有客观性。这个主体是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的主体,客观性就是以普遍性来规定。这与external object的这个“客观的”意思不同。下面接着讲的就是“性”的呈现的问题。
从义理之心所表现的性善的这个“性”如何呈现出来?这就讲工夫。下面都是一步一步的,很有层次,很有次序。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牛山是齐国都城郊外的一座山。牛山上的树木原是生长得很好的,可是它邻近大国,人们常常到山上采伐,天天拿斧头去砍伐它的树木。它还可以美吗?它的树木本亦有日夜的生长,雨露的滋润,并非没有一些芽苗、旁枝生长出来。但是,牧牛羊的人又赶一些牛羊去嚼吃它。因此之故,牛山就成了那样光秃秃的。人看见这座山光秃秃的,遂以为它根本不能生长木材,这岂是山的本性呢?
山的本性能够生长木材,人也如此。所以,下面又说“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子这个例举得很恰当。“是岂人之情也哉?”这个“情”就是性之实,说“是岂人之情也哉?”与说“是岂人之性也哉?”是一样的。头一段讲过,“情”、“才”都是虚位字,“情”不是情感的情。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虽然人都是有良心,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生活放纵恣肆,就像斧斤砍伐树木一样。“平旦之气”就是清明之气,因为人晚上睡觉,到早上醒来的时候头脑最清楚,所以,平旦之气最清明。因为有平旦之气,心里清静了,良心才会表现。
所以说,“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好善恶恶从平旦之气的那个义理的本心呈现,有清明之气,良心就呈现,有良心呈现就有好恶。“好恶”是良心的作用。“好”是好善,“恶”是恶恶。
放其良心者与没有斲丧良心的一般人相似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这个地方呼应上面所说“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几希”就相应“萌蘗”。“萌蘗”就是发出一个芽,还没有成树。放其良心者也有日夜生息的平旦之气,其平旦之气的义理本心呈现发出来的好善恶恶之情(情者,实也)与一般人相似,但很少的,只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良心发现,但白天又把它梏亡了。“梏亡”就是窒息的意思,就是拿一个东西拘束它,把它愍死。就是你刚刚生长的那一点平旦之气又缩回去了。翻来覆去地梏亡之,夜气就不足以存,夜气不存,则良心不显。良心不显,这人亦离禽兽不远矣。就是跟禽兽差不多了。“违”字解作“离”。
人看见这个人与禽兽一样,就以为他未曾有才。这个“才”就是原初的质地。“是岂人之情也哉?”这个“情”当“实”讲。这里,“情”与“才”都是虚位字,指人的最初的生命之实。“最初”是虚泛的说法,它隐指性善的那个“性”。
性善的那个“性”还是个客观字,再具体说就是心。那就是说,“最初”就隐指那个义理的本心。所以,在《孟子‧告子章句上》这段文字里,“性”、“情”、“才”都是虚位字。“情”是实,“才”是原初的质地。这个原初的质地是指“性”说。
“性”还是客观的。最后,“情”、“才”、“性”这三个东西都指仁义之本心说,这才是实,这才真正落实了。所以,“是岂人之情也哉?”也可以说:“是岂人之性也哉?”这个“情”字相当于英文的real case,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实质情形”。这个“实质情形”可以到处应用,也可以说社会的状况。这里说的是人的实质状况,人的实质状况就是性善。孟子这个地方说“情”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就表示说,人之实情是有义理的本心,有良心。就是说,人的性是善。但是,你不要斲丧它,不要旦旦而伐之,不要梏亡它。那么,这就涵着要做工夫。就好像牛山之木之美是要养的。你不培养它,你不给它时间生长,它生长一点,牛羊又把它吃掉。这样牛山是不可以有茂盛的树木的。所以,点出这一段是讲工夫。故曰: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任何东西假定得到它的滋养、培养、陶养,没有东西不生长的。“苟得其养”的主词是任何东西(anything)。假定失其养,没有东西不消亡的。“消”与“长”相对而言。“消”有下降的意思。
孟子引孔子的话,“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这句话不见于《论语》,《论语》里没有这句话。孔子有许多话是一代一代互相传下来的。“操”是持,操持。这句话指我们的本心讲,就是说,你要操持你的良心、本心,不要把它放失,它就存在,它就在这。“舍”就是不操持。你不操持它,它就没有了,跑走了。所以这个“操”就表示工夫。后来理学家就讲操存、涵养。
理学家讲“操存”就是根据孔子说的“操则存,舍则亡。”这句话。“操”连着“存”,谁存呢?就是我们的良心、本心。你要操存它,这就表示我们的生活要正常。你做操存的工夫,你的生活正常了,那么,你的本心可以在这。
你不操存它,这表示你的生活放纵,那么,你的本心消失了,没有了。这是无声无息的,所以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出”是跑出去,“入”是收进来。这个“出”就暗示孟子所说的那个“放”。跑出去就是放失了。所以说“出入无时”它有时候跑出去,有时候收回来,没有一定的时候。
“莫知其乡”这个“乡”可以解作“方向”;也可以解作“甚么地方”、“何处”,“乡”就是乡村的意思。“莫知其乡”的意思可以说:不知道它的方向。也可以说:不知道它存在于甚么地方。这个地方当该是后一种说法好。有存在的地方就有方向,所以,“方向”是引伸义,“乡”字原初的意思是“甚么地方”、“何处”(where)。
有人把“乡”字解为“方向”的“向”,那不是很恰当。所以,朱子批注为“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这是对的。“乡”,处所也。这是对的。
这个“心”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就像-条泥鳅,你抓不住牠。心是活动的,它可以随时跑出去,也可以随时收进来。这个“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就着本心在经验世界里面,在感性的生活中的呈现不呈现讲。这句话的层次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呈现不呈现,而照义理之心、良心、本心的存有问题,照它自身的存有讲,它总是在那。这个地方一定要分清楚两层的讲法来了解。
孔子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就着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呈现或不呈现讲,不呈现就是它受感性的影响。但就它自身存有的问题讲,我知道它有定时、有定处。那个定时就是它总是在这,“总是”(always)就是定时,那就不是出入无时了。
所以,这是两层。譬如,禅宗讲菩提,“当下即是”。假定你的菩提觉保持得住,不管你的生活感受怎么样,它总是在这。那就是“当下即是”,“当下即是”是说它自己的存有问题。你的工夫达到某种程度,就跟那实质存有的意义一样,意思相合。假定你没有工夫的时候,它就分成两层:一个就现实生活讲;一个就自身存有讲。
所以,孟子所引的孔子的这句话也不容易讲的,我们现实的人生是如此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孔子这句话都是就着现实生活讲的。那么,就这句话看,孔子承认不承认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心,那很难讲。
但是,孟子承认呀。孟子说,仁义礼智之心人人皆有,它是先天的,这就是本心的存有问题,这是孟子的显明主张。那么,孔子有没有呢?在这个句子看不出来。那照《论语》孔子全部言语看有没有?这是不是孟子进一步,你可否说,这是孟子的意思,不是孔子的思想?孟子这种说法合不合乎孔子的意思呢?这可以找出根据来,孔子也承认有呀。那么,从哪里找出根据来呢?
孔子不是用philosophicalterm,不是analytical(分解的)。他是从生活上说,他是圣人。圣人的话是智慧的话,智慧的话都是具体的。这个“本心”孔子也承认的,就在他所讲的“仁”。孔子讲仁的时候,有时候,仁就是理,就是道。
朱夫子所把握的就是这个“仁”。这个“仁”的境界高得很,也可以是心,也可以是理,也可以是道。朱夫子只能说仁是理、是道,他不太喜欢讲仁是心,假定落到人心,就变成气。但是,只说仁是理、是道,而不说是心。这不通的。
仁是心。这是孔子本来有的意思,他从哪里表示这个意思呢?就从宰予问三年之丧处。宰予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孔子问:“于汝安乎?”宰予答曰:“安。”孔子就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予出去之后,孔子说:“予之不仁也。”这从安与不安说仁,从安与不安就很容易说到心。那么说来,人人都有这个“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心,就是那个本心。
孟子所说“本心”是根据孔子这个说出来。首先是存有的问题。第二个是现实生活上的呈现的问题。就现实生活上的呈现而言,就是“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要就它自身存有而言,它总是在这。我们做一切培养、陶养的工夫,就是如何把那个总是在这里的那个本心呈现出来。所以,孔孟之教是“随机指点”。佛教讲“当下即是”,“当下即是”就涵着“随机指点”。
在现实上,这个安与不安随时呈现。我们抓不住它,那就是不能操持,抓不住。抓不住就跑走了。随时呈现就可以当机指点,在现实生活中,你说本心在哪里?当机指点熟了以后,你就可以说:就在这。这就是“当下即是”。这是在孔孟思想里面有的。孔子从安与不安指点。孟子就从齐宣王不忍衅钟之牛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那个地方指点。
下面的文章都是讲工夫,讲如何把你的本心呈现出来。这一段很重要,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观念,我给你们提出来。“当机指点”这句话根据甚么才可能呢?这句话要预设“本心”可以随时呈现。“本心”随时呈现才可以当机指点。
随时呈现不表示说总是呈现,总是呈现是我们的目标。本心随时呈现,它呈现一下子,就像牛山之木,它发一次芽,叫牛羊给吃掉了,没有了。发一次芽,那就是随时呈现。给牛羊吃掉,那就没有了。像波浪一样浮沉。但它还是可以呈现。
从“随时呈现”再往前进,就说“当下即是”。“当机指点”就涵着“当下即是”。“当机指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的本心。假定光有一个“本心”在这里,它永远不呈现,那么,你没有办法指点。康德就是如此,他光假定有一个free will 、pure will、good will,但他没有说这个free will、good will、pure Will随时呈现。
它不能呈现,那是我们设定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实上的意念(volition)并不是pure will、good will。
呈现不呈现靠甚么东西呢?靠直觉。它随时呈现,就是我可以看见它。因为“直觉”在康德原文(德文)的意思就是能看见,我亲眼看见。孔子、孟子承认我们的本心随时呈现,就是我亲眼看见,就是直觉。康德就是把直觉看作“呈现原则”,没有直觉的地方就不能呈现,没有直觉的地方就是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但我假定它。
直觉是一个呈现原则,但在这里〔本心呈现〕不能用sensible intuition(感触直觉),sensible intuition看不到这个本心的。那么,只有intellectual intuition可以,但我们人没有intellectual intuition。
所以,good will、pure will、free will,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义理的本心,依康德我们看不到。看不到是甚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不能呈现,结果它是个postulate(设准),说是postulate意思就是不能呈现。不能呈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的直觉。
但是,照孔子、孟子讲,我们这个义理的本心,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它可以呈现。它可以呈现,假定用康德的词语“看见”,这个“看见”是怎么样看呢?就是用智的直觉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儒家一定要肯定人有智的直觉。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本心可以呈现,尽管我们现实生活中,它不能总是呈现,因为我们受感性影响。它可以呈现,你不能说它只是一个postulate,postulate就不能呈现。这是关键,影响很大的。影响在哪里呢?影响我们的实践理性的动力。
它必须活动,它随时呈现,就是本心随时跳跃。它跳跃,它就突出来,那么,你这个实践理性才有力量。我把本心保持住了,我才能做依照无条件命令而行的道德实践。假定本心永远不能呈现,那么,动力不够了。
依照康德所讲,道德就是依照无条件命令而行。假定我的本心不能呈现,我怎么样能依照无条件的命令而行呢?完全没有把握嘛。你说尊敬法则,但是,假定这个人不尊敬,那怎么办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嘛。所以,康德讲实践理性的动力的问题讲得不够。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孔孟讲“当机指点”、“当下即是”,孔孟原初就承认有这个东西,本心自己会跳跃呀。所有的工夫就是把它随时可以跳跃的东西叫它总是跳跃。这个就是操存、涵养的工夫。这个工夫也与康德讲工夫不一样。东方儒释道三教最后的想法都这样讲工夫:承认我们有一个本心,工夫就是如何把你的本心呈现出来。
而本心是心,它活动的。要是像朱夫子讲的光只是理,它不能活动,要靠后天的活动去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力量就不够了。这个问题的微妙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王学,王阳明的大弟子王龙溪都喜欢根据“随机指点”、“当下即是”讲“现成良知”,它就在眼前呈现。在我们的感性生活中,它只露一点就是了,没有大露。它总是呈现,露一点是良知,大露也是良知。
王龙溪说,以一孔窥之之青天与不通过一孔所见的青天,其为青天则一。一钱金子也是金子,一两金子也是金子,都是纯金呀。这就叫做“现成良知”,“现成良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可以讲的,但是,后来的人忘掉孔子的教训,忘掉孔、孟的这个意思,他们就说王龙溪这个讲法是禅。这个与禅没有关系嘛。
我们说良知是现成的,这跟说我们是现成的圣人完全不同。说“现成良知”只是说良知本身的存有问题是个现成的,你有工夫或没有工夫,这对它的本质没有影响。工夫对它的影响是它的存亡问题,对它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存是这个良知,亡还是这个良知。
所以,一切工夫对于良知的影响只是存与亡的不同,不是其本质的问题。这个要弄清楚呀,要不然就是大胡涂。那些反阳明的人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他们说,良知哪有现成的呢?良知现成,做圣人不是很容易吗?成圣人哪有这么容易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嘛,他们搅混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分别讲清楚,就把以前的那个搅混的说法驳回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你现在再仔细看王学,受朱子影响而说陆王是禅的那些讲法完全不对。陆王倒是孔孟的正宗。
就切于道德实践而言,陆象山能切。尽管朱夫子的道德意识很强,那个道德意识是后天的道德意识。朱夫子一丝不苟,不敢越轨,那是教养的问题。那个地方,朱夫子是正宗。他很严肃,一丝不苟。所以,结果他是圣人之徒。其实那种讲法是现实生活的一些方式,不一定是圣人之道,孔子也不一定是那样。
陆象山、王阳明切于孔孟之道德意识。朱夫子一方面生活很拘谨,另方面就他的思辨的情形说,他讲《太极图》,他的形而上学的趣味重。他那个形而上学的意味重,不切于孔孟之道德意识。陆王的形而上学的趣味都不重,就是讲天道也是直接从良知讲,良知就是正心诚意。
道德意识在这个地方很真切。而朱子讲阴阳五行、太极那一大套东西,变成speculative。所以,朱夫子这一套东西很怪的。他一方面很能满足人的形而上学的趣味,那些喜欢讲太极、阴阳五行,讲形而上学的人很契合朱夫子。
陆象山不太讲这些东西。现在的人没有道德意识,不能欣赏陆象山,倒是欣赏朱夫子,因为朱夫子这方面哲学意味重。现代人看来,周濂溪、张横渠这些人都是哲学意味重。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朱夫子讲生活,讲居敬,讲涵养,把人拘束住,令人讨厌。在这个地方,那些人也就觉得陆王好。陆王也不是使你放纵,陆王也讲敬呀,他们是positive的讲法。讲道德有negative讲法,有positive讲法。照博格森(Bergson)讲道德,有是open morality,有是close morality。
朱夫子是“拘束的道德”(closemorality)。陆王切于道德,不走朱夫子那个拘束的路。所以,假定你偏向陆王,是因为误解陆王让你放纵,那也不对。陆王并不使你放纵,其关键在承认本心,这个义理之心当下即是,它自己本身有力量。本心有力量做出来,不要那么天天拘束。
但是,朱夫子也有可以令人欣赏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哲学的趣味。从这方面讲,可以满足现在的人的玄思的趣味。到实际的生活讲,现代人都讨厌朱夫子。那么,这样更糟糕了。把朱夫子变成一种希腊式的那种natural philosophy。
这就好像有人把张横渠讲成是唯物论。张横渠讲气、重气,重气不一定是唯物论呀。把张横渠说成是唯物论的宇宙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论,那就坏了。所以,在他们看来,陆王是绝对唯心论,而张横渠、朱夫子还有一点唯物论的倾向,还保留一点革命性,唯物论是革命的。
这完全成个大颠倒。这些问题你把它疏导一下,那就是philosophical argument。这就是哲学问题。你们要训练这种思考,要不然它里面的那些迷惑你永远解除不了。
陆象山让人误解他是禅,他为甚么令人生这种误解呢?朱夫子就是这样,总是说陆象山是禅。这些误解需要解开,这就需要思考。固然要做实践的工夫,另一方面,这个当一个问题思考,当一个问题讲,那也很有价值的。
朱子这边有一个两难:他一方面使人有哲学的兴趣、形而上学的兴趣,另一方面使人讨厌。这不是两难吗?陆王这一边也有一个两难:他一方面切于道德,没有那个形而上学的兴趣,他是开放的道德(open morality),这是好处。
开放的道德之所以为开放的有其根据,就是那个本心的问题。朱子没有那个本心的问题,依朱子的讲法,心就是气,是后天的。他只能讲“性即理”,不能讲“心即理”。陆象山讲道德所以是开放的,有力量,就是“心即理”那一句话。
这是不能反对的。这点陆象山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了解得不对,照朱夫子讲,那是放纵、放荡,不做敬的工夫。这是对陆象山误解。在open morality这个地方有误解,这是陆象山的好处,也是他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这个地方要给他疏导。
陆象山言“心即理”,切于道德,道德意识很强。但他缺乏形而上学的兴趣,这不又是一个两难吗?那么,在陆王这个系统里面,你怎么样安排这个形而上学的兴趣呢?他没有朱夫子那样的形而上学的趣味,但是,陆王都有那个形而上学的理境,他可以吸收进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moral metaphysics。
太极、宇宙论、本体论不是不可以讲。就好像西方的上帝,那不是不可以讲呀。神学不是不可以讲呀。但康德讲神学一定是道德的神学。而朱夫子讲形而上学不是道德的形上学,与道德这方面脱离了,放出去了。所以,顺着陆王这一条线,可以把朱夫子那套形而上学的趣味收摄进来。
这种吸收就是通过活动看存有。形而上学的趣味是存有论的问题。这个存有问题通过活动看,活动是心,活动指心讲。如果完全是speculative,那就成希腊那种、柏拉图那种讲法,那是离开心的活动讲客观的存有,那就不是通过活动来看存有。朱夫子就是这样,他先讲一个太极、阴阳五行。那个太极不是在心的收摄之中,它没有那个心来笼罩,成了一个寡头的客观。
这样一来,在陆王这个地方的两难就解决了。在“心即理”那个地方,在实践动力方面,他positive,而且成功创造了道德,开放的道德。在存有论方面,通过心的活动讲存有。
在开放的道德这里,有人误解是放荡,那是不对的。有人认为朱夫子讲居敬,使人很严格地遵守这个涵养察识,工夫很细密,而陆象山那里没有工夫。这是误解。这里头有很多问题需要你疏通,要不然永远是一个纠结,永远纠缠不清。
程朱、陆王两方面都有两难呀。有些人想调和朱子与陆象山,这边取一点,那边取一点。那是不对的,那个你调和不起来的,你没有了解这个里面的问题。你假定遵循后来那个“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议去讲,那是“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那永远不能解决的。
你说朱夫子光讲“道问学”吗?朱夫子也很“尊德性”呀,他那个“尊德性”更严肃。你能说他不“尊德性”吗?你说陆象山光“尊德性”,不“道问学”吗?陆象山读书读得很仔细。半夜三更,旁人都睡觉了,陆象山还在正襟危坐地在那里读书。
你能说他不“道问学”吗?他也“道问学”。道法不一样嘛。你说朱夫子居敬,陆象山放荡。陆象山一点也不放荡,夏天在象山讲课,尽管天气那么热,他整其衣冠。你说他不敬吗?远远望去,他俨然若神。陆象山有这气象。所以,平常很多说法都是误解。这个误解最讨厌。
用现代人的思考,这叫做philosophicalthinking。你仔细思考,把纠结解开,这就是一篇论文。做这样的论文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