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家族 何祚庥:我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
何氏家族内部显然也因“不同政见”发生过国共之争。解放后何祚庥专程去看望六伯父。这位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始愿意与他讨论共产党的理论。
何祚庥选择学物理,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抱负。
抗战胜利后,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主修化学。“我其实很喜欢物理,而且物理成绩要比化学好。为什么会选择念化学呢?因为老师跟我们说,二次大战的焦点就是争夺制空权,而制空权取决于飞机的速度,速度又主要看汽油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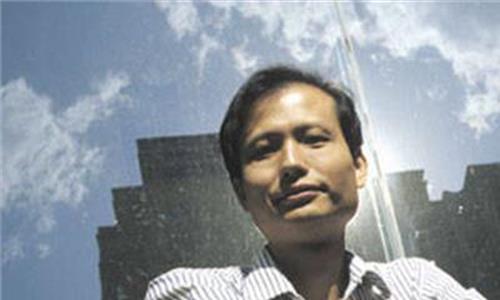
因此我认为化学可以救国救民。还有一个原因,坦率说就是因为学化学容易找工作。我两岁就失去了父亲,我的一家,全靠我母亲艰难奋斗。上海化工厂很多,我念化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毕业后谋个小差事早些挣钱养家。而那时候学物理是找不到工作的,出来只能教中学。就连杨振宁,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毕业后一时不能出国,也只能在中学里教教书。如果是我就更困难了。”

后来为什么又改行念物理,据他说还是报国。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这给何祚庥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动:“一看名单,都是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干这个!”
而在抗战胜利后,这些青年学子曾激烈地争论过,中国将向何处去。可在1947年,谁知道共产党会取胜呢?他们当时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北平、天津总是在共产党的区域内,何祚庥喜欢共产党,一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从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

“学化学,关注的是报国和出路的问题。等到我考清华、学物理,就多了一重政治的选择。这就是人生决策。”
我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
到清华的第二天,就有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地下的进步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因为这是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何祚庥回答说:“我参加!”他和一批新同学组织起来办了一份壁报《新报》,到处采访、写新闻,办得有声有色,惊动了地下党,专门来调查这个组织有没有受共产党的影响。
经查,参与《新报》工作的同学中只有何祚庥一人是“民青”成员。因而在两个月后,直接和他发生民青关系的上级,突然找他谈话,问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当时我真是大吃一惊。真没想到我的上级竟然是共产党,我参加的组织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青年团。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以后,我终于决定,申请参加地下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前夕,何祚庥已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为副书记。
他兴致勃勃地跟记者说:“我们那时候也是潜伏,做假身份证明,送学生出封锁线……余则成是用萝卜刻印章,会留下水渍,我们都用肥皂刻,你听我一说就很内行吧……”
1950年11月,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于光远回母校清华大学召开青年理论学习座谈会。那时的热血青年醉心于阶级斗争学说,何祚庥便在会上提出:“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也许这个与众不同的问题给于光远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何祚庥从清华大学一毕业,便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报道。
“我在中央宣传处是走红的干部,可以直接见部长。陆定一喜欢我,胡乔木也喜欢我。”
在宣传部,何祚庥还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做过“家庭教师”。“共产党进城以后要搞建设,很多领导干部都开始学自然科学。陆定一本来基础就比较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材生,生病期间便想再学点物理。”
何祚庥当时很直率地问:“定一同志,学物理是要用到微积分的,你还记得不记得?”陆定一说:“我还记得。没关系,你尽管用。” 每隔一天讲一课,每次讲一个小时,这堂物理课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1951年底,中宣部单独成立科学卫生处,主管全国的科学战线工作。何祚庥的工作便是搞调研、参与制定政策、做科学家们的思想工作等。
“到宣传部工作,物理专业当然是丢掉了。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我在科技界不是简单地做了一点科学工作,而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起了很多作用,争取了大批科学家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何祚庥的表姐王承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物理学家,我国核同位素分离科学的学术奠基人,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总设计师,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她同丈夫的回国便有何祚庥的“一信之功”。
“王承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做研究员。我们这些搞政治的,总觉得她和丈夫张文裕一味读书,真是一对书呆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承书很想回国服务,但国外有很多事情一下子摆脱不了,她对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之后究竟怎样也不了解。
我有一天去探望她的母亲,听到姑母总在念叨承书不回来。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要把人才争取回国,当场就说:‘我替你写封信。’我就用姑母的口气,写了新中国的种种变化,包括大表姐王承诗被评为模范教师,受到高度尊敬;姑母在北京城里怎么安居乐业。最重要的就是说物价不飞涨了。共产党来了以后,原来米多少钱一斤,现在还是多少钱。姑母抄了一遍寄过去,她一看大为感动,立即动身回国。”
何祚庥写完这封信也没多想,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好事情,心里还很得意,事先没请示,事后也没有特意报告 。没想到正好那个时候在整风审干,和外国私自通信没有报告就被当作了一个大问题。
“我怎么解释都不相信,我的党小组长就负责审查我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接到一个通知,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商量,希望我和科学院另外一位同志去深圳欢迎王承书教授、张文裕教授、郭永怀教授、李佩教授回国。审干小组长听说后哈哈一笑:‘人家都回国了,我还审查干嘛,可见你没有做了不得的事情。’”
何祚庥说:“我们当时确实是在诚心诚意地为共产党办事,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我在科技界,不完全是科学上的威望,还有政治上的威望。我以前就是地下党。物理学界党员很少,一些重要的科学家都是我发展他们入党的,包括钱三强都是我做的工作。钱三强自己都说:‘小何是我的领导,我的启蒙人。’”
当时中国科学家太少,中央宣传部胡乔木、陆定一的思维就是要团结科学家,争取科学家拥护中国共产党,反映科学家的要求、意见。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工作,便是具有“两栖身份”的何祚庥去做。“我当时虽然还年轻,但是代表中宣部去找他们谈话,科学家们也知道我上通领导,都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我前后同一百多位科学家谈过话。”
何祚庥和科学家之间知无不谈。有一次华罗庚便问他 :“小何,你马列主义学得怎么样?”何祚庥回答道:“还知道一点。”
华老说:“那你知不知道马列主义有一条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要改造我的思想,首先要改造我的经济基础。”
何祚庥马上回去汇报:华老嫌工资少了!部里立刻给华老增加了工资和特殊津贴。
2008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亲手向坐在轮椅上的92岁高龄的扬州籍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颁发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
那么昆明植物研究所是怎么成立的?何祚庥回忆说:“秦仁昌院士找到我,跟我谈了一个小时,力陈云南气候复杂、品种丰富,占了世界物种的60%-70%,应该办一个植物研究所,这是植物界的愿望。我觉得很有道理,回去便写了一个大汇报给陆定一,陆定一批给科学院,马上成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
1954年,何祚庥还曾与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罗劲柏三人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写报告建议中国搞原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