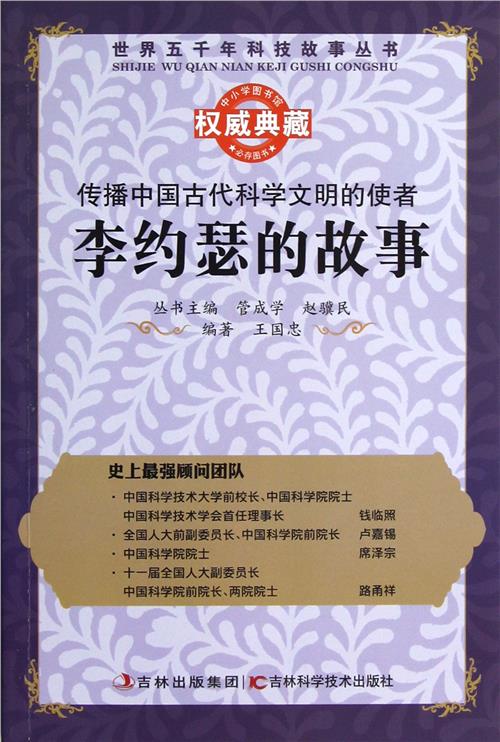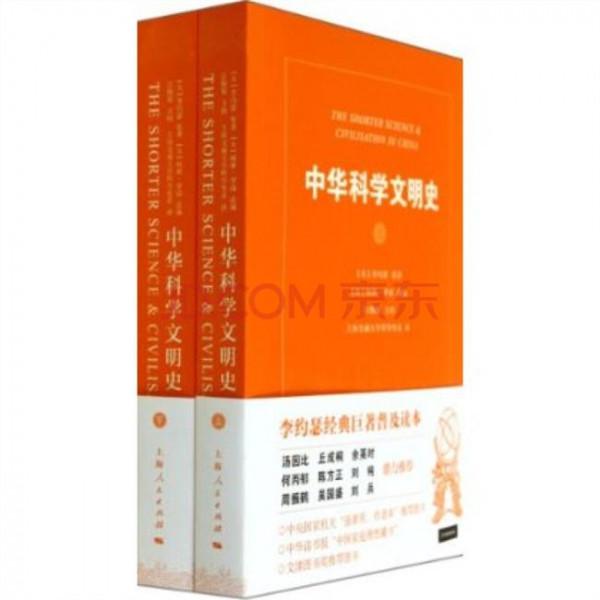竺可桢的拼音 老书的故事丨第一集 :李约瑟与竺可桢
编者按:一本老书,一段历史。在浙江大学121周年校庆之际,推出了一场名“老书的故事”的展陈, 30本老书,每一本都来历不凡,而它们的作者,正是百年来“求是园”中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字。每本老书都是一个学科承前启后的证物,以各自的方式共同记载了一所大学的沧桑与辉煌。

我们寻访到了30位跟“老书”关系最密切的“浙大人”,请他们带领我们重温每一本老书,在他们温厚的讲述中,你可眺望到浙大学术与思想传承的流脉,或筚路蓝缕,或奔流不息。
老书的故事丨第一集 :李约瑟与竺可桢

老书 李约瑟发文之《自然》杂志
讲述者 浙江大学教授、前哲学系系主任、科学史研究者何亚平
记者 石天星
录音整理 沈陈盼 汪小和 段昱
“浙大的科学研究当时在国内地位、国际影响,这确确实实是李约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浙大是东方剑桥,可能是过誉了,因为我们现在和剑桥的差距还很大,但是从比喻的角度讲,从客人的角度恭维浙大的角度讲,完全可以理解。”

记者:何老师,这次请您带领我们走近的是30本浙大的“老书”中的第一本,李约瑟在《自然》上的发文。这些年,您做了很多浙大校史的研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浙大校史发生这么大的兴趣的?
何亚平:考究历史,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参加过校庆的很多纪念活动,你看我们95周年、100周年校庆的纪念文集,最让我感动的是解放前在浙大读书的老校友,特别是海外校友。他们写的很多回忆录文章,纪念文章,充满了浓浓的亲情,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在竺可桢带领下所形成的校风特别是校训——“求是”所带来的浙大的精神状态。

这是他们到了垂暮之年都念念不忘的。我们浙大从20世纪80年代重提求是校训,越来越隆重纪念,“求是”是浙大的精神核心。
现在年事已高的老校友很少了,可喜的是“西迁”二代活跃起来了。他们关心浙大的发展,自发地为学校做一些事,包括考证历史,记录校史故事,因为他们就是在西迁路上跟着父母一块成长。
蔡恒胜就是西迁二代的著名人物,是蔡邦华先生的公子。他们自己记忆中的老浙大,虽然不像老一辈那样更完整,但他们是有真切感受的,不像我们完全是从文字上,从其他二手的东西上来感受。这就是浙大的求是的魅力。
记者:您能介绍下您研究校史的收获吗?
何亚平:我这些年来,特别是2007、2008年之后,比较专注做校史研究了。以前我主要是研究科技史,科技哲学,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带研究生,没有多少精力做校史研究。开始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带了几个研究生做一些浙大校史上的课题。
比如,吴英杰的硕士论文就是讲抗日战争时期浙大的科学研究。这篇论文在浙大还是有一点影响。过去我们讲浙大就是民主堡垒,学生运动,或者是中共地下党史,但是对于浙大教学或者科研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所以我让他做了浙大抗日战争时期的科学研究的论文,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连路甬祥都关注了这个事,把我叫去问。
那是他当副校长的时候,他分管我们系。有一次开完会,他说亚平你留一下,你给我讲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一篇文章说,抗日战争时期浙大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国际、国内影响,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对“至今没有超越”这句话是打问号的。他就说,我们这么多年努力,我们有双水内冷发电机、有原子弹爆炸的高速摄像机。
我说,那是技术上的成就。别的不讲,在竺可桢掌校时期我们浙大的名教授在国内都是身居前列,所以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樊洪业先生也是竺可桢全集的执行主编,主编组的负责人。他跟我讲过,搞清楚30、40年代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就等于搞清楚中国科技史30、40年代的一半的内容。
记者:这么重要的地位?
何亚平:这句话对我印象太深了,所以我为什么让学生去做这个,是受到樊洪业的启发。因为他是专门搞中国现代科技史,特别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史,中国科学院的院史。他还是《竺可桢全集》的主编,你看,《竺可桢全集》每一册前言、卷头介绍都是他写的。
我们浙大当时数学上,有苏步青、陈建功,一个是搞几何的,一个是搞复变函数的,都是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而且40年代他们带领学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人家称我们浙大为“陈苏学派”,甚至叫做“浙大学派”。
我看到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文章有一个观点说到,40年代的国际数学界,叫做三足鼎立,一个是意大利的罗马学派,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浙大陈苏学派。
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所以我说,路校长咱们现在一个都拿不出吧,他笑了。在物理上,王淦昌、卢鹤绂、束星北都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物理学家。还有生物学,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被称为中国生物界的三巨头,40年代都在浙大。
那更不要说,张其昀在历史地理方面,那是当时国内翘楚。像丰子恺、马一浮都到浙大来过,这是人文方面,也还是人才济济。化学方面,有机化学的王葆仁,无机化学的王琎。王葆仁是国内最顶尖,王琎主要还是化学教育家,就是王启东的老父亲。
我说,除了数理化生,历史地理气象,浙大也是名列前茅的。竺可桢更被尊为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所以,浙大的科学研究当时在国内的地位、国际影响,这确确实实是李约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浙大是东方剑桥,可能是过誉了,因为我们现在和剑桥的差距还很大,但是从比喻的角度讲,从客人的角度恭维浙大的角度讲,完全可以理解。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李约瑟对浙江大学“东方剑桥”的比喻?
何亚平:我最早看到的是张其昀在台湾发表的一篇东西,讲到当年李约瑟称赞西南联大为“东方牛津”,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这次蔡恒胜先生所作的认真考证我都发给你了。认真考证了以后,其实很关键一个,张其昀也是间接听到别人说的。
当时接待李约瑟的时候,他身在美国。浙大现在引用这句话比较深信不疑的原因,是苏步青先生生前多次讲过,他是亲耳听到李约瑟称赞浙大是东方剑桥的。我印象中苏步青先生在100岁以前,来浙大的次数太多了,甚至复旦的学生都有点妒忌,说苏步青在复旦作报告也是言必称浙大。
记得苏老在浙大有一次参加一个规模不是太大的纪念会,也是在校庆期间。他就说,我就在现场,是听到李约瑟说,浙江大学可以和剑桥大学相媲美,可以称为东方剑桥,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很确定地说,我是亲耳听到的。
记者:那么现在的考证,李约瑟是不是说过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这样的比喻呢?
何亚平:我们没有找到当时的文字记录,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有录音。也就是说,如果是从考证的角度,是既不可求真也不可证伪。考证的目的是把最核心的问题弄清楚。
现在陆陆续续看到的各种表述,我的看法是:第一,当时李约瑟到浙大来是客人,他出于尊重或者感谢,恭维地说这样子两句话,是完全可能的或者可以理解的。第二,他确实是来的时候发现,浙江大学一大批教授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研成果,他本来准备打算呆两天,后来呆了一个礼拜。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倒是倾向于竺可桢日记的里面记载,竺老说,据一位教授告诉他,《贵阳日报》上报道了李约瑟在英国的演讲,称“联大、浙大可以和哈佛、剑桥相媲美云云”。我很关注这“云云”二字,这随口所云,竺老把这个事情没有当作什么回事,他只是日记里仅仅带了一句。
记者 :那么对于这个溢美之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何亚平:对于当年这个问题,最近蔡恒胜先生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东西,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也让我们有个头脑的清醒剂。他说西南联大是东方牛津也有过誉之嫌,也是恭维和客气的套话。但是,我觉得这看作是给我们的鞭策也是好的。
我印象很深的、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苏步青先生在表述李约瑟的评价之后说的话,他说,我希望经过你们一代一代浙大人的努力,在你们的手上,能够让我们到英国听到,英国人说我们剑桥是西方浙大。当时,大家以热烈鼓掌来回应了苏步青先生。我们浙大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提“东方剑桥”就是违背了求是精神、求是校训
记者:在研究校史的过程中,您对李约瑟是不是也有了更多了解?
何亚平:当时李约瑟是四十二岁,年轻人,他的学术职称是个副教授,而且他是学生物化学的,中国科技史是他来中国以后才有所成就的,而且中国的学者们给了他很大帮助。我觉得,李约瑟和竺可桢的相互交往,是促成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动力!
竺可桢的大力支持是从李约瑟两次到浙大访问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你看蔡恒胜有一个竺可桢嘱咐学校寄过去的几百本书的目录,那是他真正系统接触中国科技史的原始的资料。你注意一下,到竺可桢日记里面去找,竺可桢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时候,也给李约瑟不止一次地寄过新发现的有关中国科技史的材料的副本。
在这点上,应该说,竺可桢和国内很多的人,包括钱宝琮、包括我们中国研究科技史的很多人,因为后来1956年,竺老带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参加了国际科技史的学术讨论会,在那个讨论会上,李约瑟是活跃人物,还是大会副主席,就更加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是在竺老关怀下,席泽宗、钱宝琮、李俨这批国内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汇聚北京成立起来的,也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
所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特别是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没有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对他的支持、帮助、指点,他是不可能写出中国文明史这部巨著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中英合作,中国和国际学者合作的典范,当然李约瑟是功不可没的,在全世界他首先发现,在15、16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西方望尘莫及的高度。
他是依靠着大量中国史籍、典籍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的。最近还新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和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合作支持的李约瑟研究所之友联谊会,定会深化关于李约瑟的研究。我这么多年,更多的兴趣是在对竺可桢的研究。对竺可桢学的研究,怎么讲呢,也是历史的机缘。我是从读竺可桢日记开始校史研究的,也是后知后觉。
“我是从90年代就开始觉得竺老在我们浙大、中国的科学界,甚至在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他是一个高峰。但是,我们现在对他的研究,还是回忆多、纪念多,深入地去挖掘他的伟大人格和学术成就的意义是相当欠缺。”
记者:您能讲讲您是怎样对竺可桢学研究产生兴趣的吗?
何亚平:我今年78岁了。我是在浙大1978年读研,读自然辩证法。读研之后,就留校,教自然辩证法,后来教科技史、科学社会学,带研究生。主要还是教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涉及一点,但是主要精力不在科学哲学。这些年来,我逐步地步入竺可桢研究,樊洪业是我的领路人,我们是同一届毕业的研究生。
他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史研究室,我们就是因为对竺可桢的研究上共同有兴趣,特别是后来他主编了《竺可桢全集》以后,交往更多,互相交流的确感觉到竺可桢这个人,学识渊博,学术上贡献巨大,特别是在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上,他在管理岗位上发挥了独一无二的重大作用。
你看路甬祥在《竺可桢全集》的序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在科学院建设初期竺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记者: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何亚平:我们最感动的恰恰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我昨天为什么给你发那封信,你注意那份信最后的两句话,说你寄来的那个东西是手抄的,不是复印件,那就很珍贵,所以我退还给你。你看这些细节问题上,做人做到他这个份上,就是可以称为圣人。
我和樊洪业聊天的时候,樊洪业曾说过,竺老的道德文章可以成学,如果单纯说他的人品,可以成圣。所以有一大批人对竺老确实是达到了崇拜的地步。所以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大学的严德一先生和刘操南先生,主要是严德一首先提出来,竺可桢先生一生他的道德文章可以成学,这是见诸文字的“竺可桢学”的由来。
而且在90年代的竺可桢研究会的杭州会议上,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严德一先生的原始文章,但是刘操南先生在1990年竺可桢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文集里,有两篇文章专门阐述竺可桢学,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竺学”蠡测》,这篇文章是至今为止论述最细,也是最有影响的。
我们收在了竺可桢学学术研讨会的文集里。
记者:竺老当校长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他主要是研究地理气象学,但是能够得到那么广泛的爱戴,主要是哪些原因?
何亚平:竺老,我最感动的是,一个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确确实实是尽心尽力。抗战期间他担任浙大校长,每到一地,非常关注有一件必做的事,就是找当地的方志,县志、地方志,里面有关地理气象的东西,尤其关注。物候学方面的东西特别关注。
所以他有一本书,叫《物候学》,在竺可桢全集里也有。你去看的话,坦率的讲,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没有渊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写不出这么一本书的。他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的考察(文章名应为《二十八宿起源之时间与地点》),这个文章前后写了四五年。
他是先是形成自己的基本想法,考察了国际上对于二十八宿的研究。那时候没有网络,只能靠自己日积月累,形成的丰厚的贮备。他能在抗日战争期间想到这个课题。
因为国际上当时还在争论,有说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日本还说起源于日本,当然也有起源于中国一说。竺老更倾向于起源于中国,但是要驳倒起源于印度、日本,那么需要论证,严密地论证。所以,他只要有空闲时间,经常利用晚上,自己查阅资料,自己写这个东西。
所以,在竺可桢日记里,你去看,有时候“今天又再弄二十八宿起源”。一个是自己努力,第二个是他虚心听取其他的专家的意见,特别是与钱宝琮讨论。钱宝琮是浙大数学系教授,当时主要是教微积分。
但是他自己热爱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那么钱先生就和竺老共同讨论二十八宿,两个人还意见不一致,还争论,一个说服不了一个,但互相都能够包容。所以你看竺老,后来在中国科学院里面,包括郭沫若都尊称他是老夫子。
因为当时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陈伯达、陶孟和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最初只有竺可桢一个,后来才陆陆续续李四光回来了,又加上了吴有训。但是,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竺可桢,因为他知识面很广,他天文、地理、生物、气象、数、理、化,他都有涉及,所以他在整个科学院早期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科学院最初也就是刚解放的时候,是两派,可以说两大阵营一样,北京有个北平研究院,南京有个中央研究院,都自成体系,都有数学所、化学所、物理所,有些是有差异。
所以合并的时候,留哪个,撤哪个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竺老在主持这个工作期间,他高风亮节。中国的气象研究所是1927年他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筹建的,中央研究院成立的时候,1928年正式成立。
他是第一任所长,他作为所长一直担任到1947年。所以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时候,他为了顾全大局,是他提出了撤销气象研究所,把它并到地理研究所。这件事情在科学院当时来讲,真是一个“地震”。
人们没有想到,竺老做了这么个决定。他的弟子们不服气,说凭什么我们这么兵强马壮,我们设备齐全,条件很好,我们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撤销可惜得很。竺老想的是顾全大局,因为他在主持这个工作,要兼并哪个研究所,要撤销哪个研究所,哪些人留下来,哪些人要他们离开,这是个非常得罪人的事情。
所以他自己做了这样一个表态,坦率讲,很多疑难问题都解决了,别人都没办法再争了。说到要撤离,要并,或者说是名字要改一改,工作顺利多了。这就是路甬祥说的,在科学院初创时期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自己体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只是其中之一。
记者:那从学术上来说,是不是撤销是比较可惜的?
何亚平:两种观点都有。但是他的人员都保留了,在地理研究所有气象研究组,人员、设备、工作都没有停下来,就是名义上、名气上受点影响。但如果你说,保留有更独特的发展,说不定攀登了。后来,出了个叶笃正,叶笃正是竺老的研究生,硕士,得了国家最高科学奖,著名浙大校友,很有骨气,是我们非常尊敬的老人。
叶笃正的故事更多了,你看《叶笃正传》了解一下。那么叶笃正是青藏高原气象学和国际上可持续发展这门学问的开创者,所以他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因此能够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他就讲,他深受竺老的影响,就是竺老对待气象、对待地理学研究有广阔的思维,不是钻牛角尖的研究方式。竺老的所有研究,很重要的就是他既有一定的宽度,又有一定的深度。这在科学上是很难把握这个度的。当然竺老,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为浙大作出的牺牲是最大的。
记者:竺老为浙大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何亚平:他到浙大之前,所有的传记都有讲,他其实是不愿意来的。但最后是夫人的两句话,“你不是一直抱怨中国的教育吗?现在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何不去施展你自己的抱负”。“再说浙大现在整体需要你,那么多人来请你”。
他这才下决心,但是他来的时候,一直没有放弃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他1936年4月25日来浙大上任,就职完之后,马上返回南京气象研究所工作。那时候,南京到杭州有火车了。他这样来回奔波,那就是他1936年4月到1937年11月,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面的常态。的确是为气象科学和浙江大学的发展,他自己就是玩命一样的工作。
记者:他之前跟浙大有什么渊源吗?
何亚平:之前没有更多的渊源,他没有在浙大的前身读过书,他1910年出国时20岁,因为他读书比较晚,再一个因为他先是读私塾,后来又读洋学堂,在上海的澄衷学堂读了几年,最后到了唐山的那个学校,他学的是土木,出国以后学的是气象,开始是学农,所以他为什么对生物也比较熟悉呢,他读过农科,读了三年的农学院,然后毕业以后呢,才读了哈佛研究生,是在哈佛读气象,那时候气象学科才刚刚从地理学里面独立出来,是一个新兴的、20世纪初的发展中的学科,所以他参与了早期的气象科学的发展,他的老师们同学们都是后来国际上知名的一代气象学家,他这个学术经历,再加上后来他到了浙大以后,他确确实实非常地谦卑,当时在浙大,凡是重要的事都由校务委员会决定,学术上的事还有个学术委员会。
记者: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不是一回事儿?
何亚平:校务委员会,是教授为主,没有专门的教授委员会。抗战期间还有特种委员会,就专门要应急的、逃难的、打前站的、扫尾的等等这些都是。所以后来他在浙大的这段经历,我们客观的讲,利弊得失都存在,对他后来主持科学院的研究所的建立、人员的调整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因为他对中国大学里面的各个学科的人才分布、学术状况了解,他心里实际上都有一笔账。
我看竺可桢日记有几个地方我是流眼泪的,一个就是1947年竺老抗战胜利了,浙大也迁回来了,正好有段空隙,联合国成立教科文组织,他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到法国访问了,再到英国去访问,然后到美国去考察。
前后待了大概8个多月。他到了美国以后,他在日记里面记述,他读当时最新的气象学杂志,他说他竟然有些文章都看不懂了,他在日记里讲“我已经是一个二流的气象学家了”。
你想想一个20年代在国际上著名的气象学家,他关于台风的研究,很多年被别人引经据典,作为经典的文章来拜读的,而且在国际,你去看到30年代国际气象学学会开会时候,竺老都是作为著名的气象学家参加的,他当时是在整个国际气象研究的前沿的,但是到1947年,他说他是二流的气象学家,这就是因为他担任了浙大的校长,他离开了气象学术研究的最前沿的领域,他只能做一些历史的研究,像二十八宿起源的天文学的问题了,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1949年, 4月29号的出走,真是叫做无可奈何啊,他把学校的工作委托给严仁赓和苏步青,躲到上海中国科学社的仪器公司的楼上,在上海等到了解放。
解放了以后,家属还在杭州,浙江省政府,包括浙大的师生相当一部分想请他回来,但是你也知道也有反对的写大字报,用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政治词汇他也了解这些情况,他在日记里写的是“我对担任大学校长一职已厌恶至极。
”,你想想“厌恶至极”,他担任了13年的浙大校长,这个痛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所以他确实是为浙大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更不要说1938年跟他相濡以沫二十多年的夫人,因为一个急性痢疾结果丧生,他最喜欢的二儿子竺衡比他母亲还要早死一个礼拜,读他的那两首悼亡诗写的特别感人,他是步陆游悼念唐婉的沈园的那两首诗的那个韵写的。
你可以想见他当时所经历的痛苦,所做的牺牲。
你看我写的文章里面我讲1939年浙大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这是浙大西迁中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竺老最痛苦的时候,刚刚丧妻失子,但是浙大又面临着如果不努力工作就有分崩瓦解的危险,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精神的东西。在那么困难的一个年代里,什么精神的东西,就是“求是”校训,来作为一个凝聚人心的精神鼓舞。
记者:浙大80年代重提“求是”校训,其实也包含了对竺可桢校长带领浙大走过的那段历史的一种再认识吧?
何亚平:竺老的的确确是我们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至今我说没有人超越。不仅是时间上, 1936年4月25号到任,1949年4月29号离开,十三年零四天。更重要的他熏陶了一代的浙大学子,那时候浙大学生不多的,六百多学生,后来到了抗战胜利光复的时候也只有两千多学生,但是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影响了老的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竺可桢学”的意义就在于未来。
浙大有今天,从精神上讲,特别是我觉得路甬祥功不可没的就是重提“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浙大内在的精神的东西挖掘出来了,提出了“求是创新”的新校训,我觉得这是路甬祥对浙大很大的一个贡献。
“我希望竺可桢学,真正体现他的精神实质,作为竺可桢一代,我是把他作为浙大的精神领袖的,或者说是浙大的魂魄的,能够让任何一个到浙大来读书的人,读了四年或者是八年,你能把竺可桢学学了,这一辈子我觉得就不枉了,能够像竺可桢那样做事做人,的确就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记者:怎样深化“竺可桢学”的研究?
何亚平:竺可桢学是严德一先生提出来的,你再看看刘操南主编的《一代宗师竺可桢》。竺可桢学研究为什么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个事情是2016年,另一个老朋友王作跃,他是加州理工莫迪那分校的一个历史学教授,我们也是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后来我们邀请他回来到浙大来参加活动。
他来之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个记者访谈。他就说道“竺可桢全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竺可桢的最丰富、最全面、最权威的研究资料”,这句话一下子启发了我。
我说竺可桢学研究什么,实际上就是专门研究活生生的24卷的竺可桢全集,研究竺可桢全集形成的学问就叫竺可桢学,这是我现在的新认识。所以前年,他来我们一块开会讨论,我说你这次来让我最高兴的是我产生了这么一个新的理念,得益于你的启发。
他也对竺可桢学非常感兴趣,我们已经讲好了到2020年,就是竺老诞生130周年的时候,在浙大开一次竺可桢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国外现在在组织人员在组稿,那么我的弟子们呢,就在国内组稿,就为了2020年5月份,浙大校庆期间开这个会。
记者:各种契机之下,您觉得竺学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时机了?
何亚平: 我就觉得研究竺可桢学现在是时间条件都比较好。对我们浙大来讲,就要做扎扎实实的研究竺可桢的工作,什么时间都不会过时。我们浙大的传统,新任的校长、书记都要重走西迁路,去年吴朝晖校长率队重走西迁路,我有幸参加了,我深有感受。
吴校长提出了“漫漫西迁路,我们浙大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落脚点和进发点”的新认知,这也将是竺可桢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所以我说浙大现在做好这样一个工作,条件很好了,只要是有心研究什么东西,应该说是问题都不大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竺可桢学,真正体现他的精神实质,作为竺可桢一代,我是把他作为浙大的精神领袖的,或者说是浙大的魂魄的,能够让任何一个到浙大来读书的人,读了四年或者是八年,你能把竺可桢学学了,这一辈子我觉得就不枉了,能够像竺可桢那样做事做人,的确就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说起这个想起一件事,想起一件事是关于常书鸿的,我父母的这幅画就是常书鸿画的。
记者:常书鸿和竺可桢也有渊源吗?
何亚平:常书鸿和竺可桢交往不是很多的,60年代竺可桢到敦煌莫高窟,去看完、参观完了以后,常书鸿送给他一套画册,他一直记着这个事。所以1966年元月常书鸿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代会,因为常书鸿是杭州人,到了外省呢,是浙江人就是老乡了,他登门拜访了竺可桢,竺可桢当时很高兴,接待了他,将尼泊尔古建筑的一张图片送给常书鸿,作为纪念吧,常书鸿走了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 “常走后,继思我到敦煌,常送我敦煌的图画册,吾是以薄报厚,遂决定以格拉西莫夫所赠苏联列宾画册转赠。
”第二天他就把他到前苏联访问的时候,苏联科学院送给他的列宾画册,一本很精美的画册拿上,去找常书鸿,结果还记错了地方,跑了两个地方最后找到常书鸿,把这本画册给了常书鸿,这样他才心里了了这桩事,做人就应该这么做,礼尚往来嘛。
你想论地位,他比常书鸿高多了,他是科学院副院长啊,全国多少头衔,几十个头衔啊,但是他能够在这么点小事情上,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太伟大了。包括我昨天给你发的那封信,就那么个小小的细节他都很关注,很尊重人,这也是一种自重吧,我觉得这就是为人楷模的,为人师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