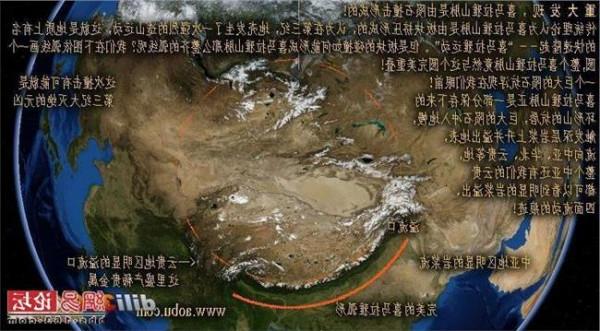王弼圣人观新探 余树苹:王弼的圣人观
王弼与裴徽有一段与圣人有关的对话,兹引如下:
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王弼“圣人体无”的答语在当时曾经语惊四座,冠绝群伦,成为正始时期儒道关系的新阐释。王弼融合儒道两家的异同,提出圣人“体无”的观点,因此而使孔圣与玄性相联。
王弼对“无”的阐述,主要见于他的《老子》注中。王弼所论之“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以无为本”与“以无为用”。“以无为本”的“本”类似于我们所谓的“本体”和“本源”,是万物形成与存在的来源和根据: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第四十章》王弼注)
无形无名,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作为万物存在依据的“无”,是“无形无名”,不可捉摸的,然也正是圣人所体之万物的终极。这里的“体”,是体会的意思。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意会”,其蕴含的意思即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是圣人“体无”而不说“无”的原因。这是由“无”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玄性的重要表现。也因此,一般人决不可能“体无”,唯有圣人才能做到。

依于“无”之为无,当它作为用时,则是自然、无为:
“道常无为”:顺自然也(《老子·第三十七章》王弼注)
“人之我教,我亦教之”:我之教人,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夫自然。(《老子·第三十七章》王弼注)
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论语释疑》)

王弼在讲到圣人之道德与政治实践时,多以“自然”为用。“自然”、“无为”是与“无”相应、由“无”而产生的,“以无为用”,即是因任自然,无为而治。这是王弼在注释《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自己形成的关于“无”的论说。
正是在“体无”的意义上,孔子高于老子而居于圣人的地位,《论语》中素朴的师长成了“玄圣”。然而,儒家与道家在“无”与“无为”上的对立,众所皆知,为什么王弼以儒家的孔子为圣人,却偏偏引入道家的“无”来说明圣人与众人不同之体悟呢?
王弼以道释儒,源于其所处社会深刻的思想背景与主要矛盾。经过汉代扶植,儒学及其经典已成为官方学说,不仅如此,它也渗入到社会各层,成为社会价值理想的主要承载者,成为一种文化形态,是生活、教育、施政的主要依据。
对于这一点,学者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如余敦康先生指出:“至于经学,则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它的命运不受王朝更替的影响,而和封建社会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1](P51)因此之故,无论王弼对《老子》的思想如何认同,如何向往,他仍与魏晋其它士人一样,以儒学为正宗,以孔子为圣人。
然而,他内心真正向往的,却是道家的自然无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道家的自然无为融入儒家的圣人的品行之中,使之二合为一,既符合受儒学熏陶的心理定势,又适应了受道家影响的价值追求。
由此可以看到,王弼对圣人玄性的阐发,其意图在于为当时名教与自然、儒家与道家之间的矛盾寻求恰当的解决方案。如此解决,既保住了儒家的地位,也不妨碍其追求道家之自然无为,可谓一举两得,而孔子也因此而成为玄化了的圣人。
[ii]然而,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的,“王弼的贵无论实质上是一种探求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专门研究抽象的有无关系的思辨哲学”,[1](P390)也就是说,王弼玄思之发挥,最终还是要落到现实中来,然而,圣人在“体无”的同时,如何体现他对“末”的统摄作用?无为如何达到无不为的效果?因循自然如何“畅万物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在于王弼圣人观的另一个方面“圣人有情”,与他在《论语释疑》中的思想相联接而产生。
二、圣人的人间性
“人间性”,指圣人在具有超乎常人的性质之外,与常人相似或相同的地方。以往论圣人的人间性,主要从德性方面立说,但德性已经不是纯粹的人间性,而是圣人之人间性与超人间性相结合所产生的品质,已经是在彰显其超出常人之处。王弼则不同,他关注的是圣人在德性之外的人格。王弼提出“圣人有情”,则恰恰是圣人与常人全同的地方。全同,是从自然发生与不能杜绝的角度上说,发生之后的节制与对“情”的运用,则圣人仍是不同于常人。
王弼关于“圣人有情”有经典论述: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邵《王弼传》)[iii]
如何理解王弼的“情”,如何理解情与性的关系?又如何理解王弼圣人体无与圣人有情的关系?下文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汤用彤先生认为,“五情者喜怒哀乐怨”,[2](P66)也就是说,“情”即类似我们现在所讲的情感。学者们认为,王弼的圣人有情说是针对圣人无情说的,而提倡圣人无情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以情为恶。圣人纯善,不可能有恶之情,圣人无情论因此而来。那么,王弼主张圣人有情说,是不是以情为善呢?这是一个过程,可以由其对“性其情”说得到解答: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能使之热者何?气也、热也。能使之正者何?仪也、静也。又知其有浓薄者。[iv]
这是王弼对《论语释疑》中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一段注文,也是他关于性情说的一段经典文字。[v]后代学者对此段的分析,多以“性”为主导,认为王弼主要表达了性之无善无恶与性对情的制约作用。笔者认为,王弼的这段文字虽出于对孔子“性相近也”的解说,但其着重点却在于“情”,表达了他对“情”的观点:一,情有“正”与“不正”(或说,情可善可恶),引起情之正不正的原因是“欲”,在于是否逐欲而迁;二,情可正可不正,引导情归于正的是“性”;三,必须使情近性,以使情归于“正”。
这就是王弼“性其情”说的三个层次,其重点在于如何使情近性。
在研究这段注文时,很多学者引入“理”来说明情与性的关系。如汤用彤先生认为:“性其情者谓性全能制情,性情合一而不相碍。故凡动即不违理乃利而正也”。[2](P67)贺昌群先生也认为,“王弼所谓‘性其情’者,即以情从理,以理化情,而后知天理即存于人欲之中,天理人欲之不可分,亦犹性情之不可分……”[3](P80)余敦康先生持同样的观点:“所谓性其情,即以情从理,以理制情,不以求离其本,不以欲渝其真,把情感置于理性的支配之下,使二者和谐统一,达到中和的境界。
”[1](P371)虽然他们在分析中并没明确提出“性即理”、何为“理”,但是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性就是理、天理,贺昌群甚至提出天理与人欲之相对,可见,学者们在此多少受宋明理学关于性、理观念的影响。
然而,王弼在这里并没有用“理”释“性”,“性”也并没有主动制约“情”的意味,而是“情近性”,即使“情”向“性”靠拢、看齐,形象的说法,可以说让“情”向“性”学习。而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其实只是“自然”:
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臆之内,然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何邵《王弼传》)
这段话是为孔子因颜回而产生的哀乐之情作辩护,这可以体现两个观点,一,圣人有情,二,情乃自然之天性。也就是说,圣人虽有超出常人之“明”,但也有与常人相同的“自然之性”。性是自然,情也是自然,但情会应物,会因欲、因物而动,[2](P66)而离自然。因此,如果使情近性,使情保持于自然的轨道上,则能得“正”。可见,情不在于是否以理节之,而在于顺应自然。
也正是在“自然”这一点上,王弼圣人观之玄性与人间性得到了统一。正如上文讲到,“无”、“无为”,说到底是因循自然。情,也是一个自然,产生时是因为自然之性,使情归正也只要使情合乎自然,因此,圣人之体无与圣人之有情,无非就是圣人对自然的因循。进一步说,因情是自然,圣人以其过人之神明,能使“情”处于自然之正。因此,圣人对自然的因循,也可以是对“情”的因循。
上文讲到,王弼之“圣人有情论”是针对“无情论”而发。大体是如此,但细究起来,圣人之情却有更具体之处:“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这里王弼所反对的,是以为圣人无累于物,就不再“应物”的观点。
也就是说,“无累”固然是圣人过人之处,但是圣人之情的“应物”,即对物的感应、反应,却一样重要,不可忽视。可以这么说,圣人有情,就“有”这一点来讲,与人无异。圣人之“情”异于人之处,在于经由“情”与“物”相联结,能够“应物”,最后得“物”之“情”,并统摄“物之情”。这一点,对解决王弼圣人观中的理论难题有莫大的关系。
因此,“情”于圣人,对于王弼来说,并不是纯粹的人类情感,而是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圣人以己情达物情,从而起到“统物”作用的重要途径。
首先,王弼将孔子的重要概念赋予“情”义。如对“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一句,王弼的注为:“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自然亲爱,即所谓的情。又如,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
王弼注为:“情发于言,志浅则言疏,思深则言讱也。” 再如,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其为之难。”(《论语·宪问》)
王注为:“情动于中而外形于言,情正实,而后言之不怍。”这两句有共同的特点,即在讲“言”时,王弼必引入“情”。言是情之所发,为情之表达方式。然而,此处以“情”释言,本非必然。考察其它注家的注释,如皇侃对第一句的注解:“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一云,仁道既深,不得轻说,故言于人仁事必为难也。
”[4](P826)并朱子对第二句的注解:“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4](P999)可见以情释言,是王弼独有之解,也是王弼有意引入“情”释圣人之言的例证。
其次,引入“情”是为了统“物”。
对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一句,王弼的解释为:
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唯恕也。
王弼同样以“情”释“忠”,情尽到极致就是忠,可见,王弼是从广义上来定义“情”的,它所包括的是人类的所有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情感类型。而圣人一以贯之的“恕”,其实是从自身的自然情感出发,以之为基础来了解、体会、掌握万物的“情”,从而达到“尽理”与“统物”的效果。
上文还引到“推爱及物为仁”,在王弼的理解中,“仁”与“恕”这两个重要概念,不仅与“情”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情”推广出去,达到统众之目的。这与上文所引“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中,对“应物”的强调是一致的。
“恕”之所本是情,圣人一以贯之的“恕”,朱子认为是“以一心应万事”,[4](P257)王弼的理解,则可以说是“以一情应(统)万物”。王弼在《老子注》中已申明以“无”为体,正如上文所言,关于“无”是什么、如何起作用,王弼并没有作清楚的理论说明,仍然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质疑的地方。
“情”虽非的“用”,却在实质上起到与体联结“无”与“万物”的作用,使王弼之体用一如在此得以实现。当然,我们不能离开王弼的整个圣人观来理解圣人之“情”。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因为圣人有茂于人之“神明”,能够体无,因此,圣人能因循自然而得情之正,才能够由己及物,得物之情,统物之性,得理之极。所以,“情”虽是圣人与人同之处,但却因为圣人的其它品质而显得更加不同。
三、圣人观的人格化
上文以“无”与“情”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展现了王弼所理解的孔子形象。王弼所强调的,是圣人的玄性与人间性,具体来讲,就是圣人体无与圣人有情。在王弼的整个圣人观中,无处不体现道家思想的影响:“圣人体无”这一命题,本来就是针对老子之言“无”而孔子之不言“无”而来。
王弼讲孔子能“体无”,虽然是将孔子放在高于老子的位置,但是,将孔子与他原本并不注重的范畴“无”结成如此紧密的联系,已经可算是对孔子思想的反叛。王弼在“圣人有情”这一命题中,其对“情”与“性”、“自然”等关系的界说,受庄子很大的影响。
庄子认为“情”与“性”相连,是人所固有,自然而然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而庄子所讲的“无情”,指的是不为情伤、常因自然:“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庄子·德充符》)王弼对情的讨论,其实是接着《庄子》而来的,是在“情”作为自然之性的意义上讲“圣人有情”,他对无为、自然的向往,与庄子根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王弼在描绘孔子形象时,注重的是人格,而不是身份;王弼注重的是孔子作为圣人的内在品质,即圣人人格。对圣人人格的讨论,在魏晋时期有很深的根源。汉时由于选拨人才的需要,非常注重人物品评,这种人物品评发展到魏晋,由现实政治的需要演变而为名士们闲暇时的谈资。
汤用彤先生对此转化有过解释:“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5](P12)刘劭的《人物志》即是这种抽象玄理化的代表作品。
王弼作为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其日常谈论自然不离当时的主要论题,他的圣人观的主要表达,正是在与别人的论辩中产生的。论题相同,不同的只是王弼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因而起到不同凡响的效果。“体无”与“有情”都是王弼对圣人人格的创见,“无”之玄性主要体现在王弼的《老子注》中,“情”之自然性与应用性,则体现在《论语释疑》中。
在了解王弼“体无”与“有情”的圣人观之后,我们不能忽视一点,与前人(包括孔子之后的儒家弟子与其它尊奉孔子的作者)更注重将孔子这一圣人形象作为标准与尺度运用于现实政治、理论实践不同,王弼更注重的,是圣人人格背后所体现的“智”。
王弼指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所谓的“神明”,实际上就是一种超乎一般人的“智”。顾颉刚认为,“圣”在最初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意味。[6](P132)而后人在将孔子奉为“圣人”时,其“圣”的涵义其实已经道德化了。
如孟子说的“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王充所说的“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本性篇》)都是将“圣”德性化的产物。而王弼这里所说的“神明”,恰恰不是在德性的意义上讲,而是在顾颉刚所指出的“圣”的最初涵义上讲,即智、聪明的意思。
对“德”的重视,是对社会伦理的重视,也是对“外王”的追求;而对“智”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对个体特性的关注,即后来儒者所谓的“内圣”。
王弼指出,圣人之所以能够体无、能够应物而不累于物,关键就在于圣人有茂于人的神明。可见,就王弼而言,“圣”的公共性,即对“圣”的社会意义、伦理意义,已经转化为“圣”的个体性。“圣”的公共性,必然要表现在仁、礼等人为方面,而深受老庄影响的王弼,更关心的是个体性,在彰显个体性的同时,必然向往自然而然的无为之境。
所以,即使王弼也一样关心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但他的体现形式与解决方案,是不同于以往儒者的。
这一特征,是夹杂于孔子形象的讨论之中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也是王弼本人思想的个性特征,而这也是玄学之所以谓之“玄”的原因。至此,魏晋时期孔子以“玄圣”的形象出现,是人性中夹杂玄性、既寻常又超脱的圣人。
[参考文献]
[1] 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1991年7月
[2] 《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四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3]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
[4]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10月
[5] 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全集》第四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6] 顾颉刚《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
景海峰老师指出,“体”在中国古代含义很多,最初指“具象之物”,另衍出三支:一是其延伸义,引申出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的关系;二是其比拟意,具有了哲学本体范畴的意义,既包含了具体与抽象的关系,也有隐与显的区别;三是做为动词的“体”,是人所具有的特殊的感知能力和心灵活动。
而作为动词的“体”又可细分成三类,一是以主体感知客体,二是主体之间相互沟通,三是用主体来表达客体。参照景老师的分类,本文此处的“体”,即是作为“以主体感知客体”、动词性的“体”。参阅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
[ii]对于王弼所理解的儒道关系,学者多认为王弼外儒内道,即实际上以尊崇道家为主,儒家则只是其披上的外衣。贺昌群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从道家的“无”与儒家的“中”皆含否定意义,认为儒道原本“同归”,而王弼恰恰发现了儒道相交之点,也就是说,在王弼思想中,儒道原来相同,并不像后人所说的王弼持“内道外儒”的双重性。(见氏着《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页74-77)
[iii]本文关于王弼的资料与注释文字,皆引自《王弼集较释》,楼宇烈较释,中华书局,1999年12月。下文不再说明。
[iv]王葆玹认为,只有“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这两句才是王弼的释文,其余的不是。(见氏著《玄学通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4月,页502)笔者限于资料与学力,不能作出辨析,只在此提出参考,行文时仍以一般看法为依据。
[v]王弼“性其情”之说,对伊川先生程颐深有影响。程颐在其《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谈到情与性的问题:“……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见《二程集》,王孝鱼点较,中华书局2004年2月,页5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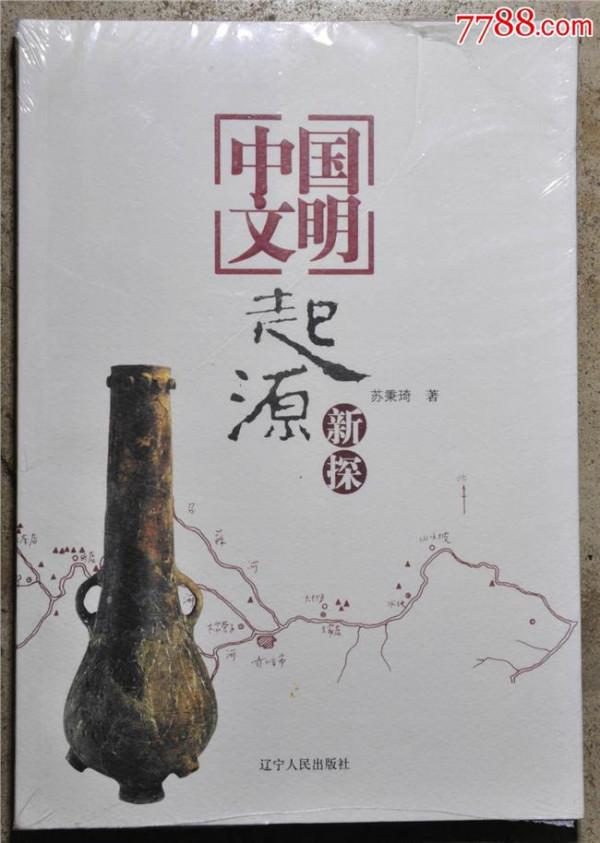
![>苏秉琦中国梦 [原创]读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两个打破”有感](https://pic.bilezu.com/upload/a/05/a0582b1e406b43314a8690e4922824b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