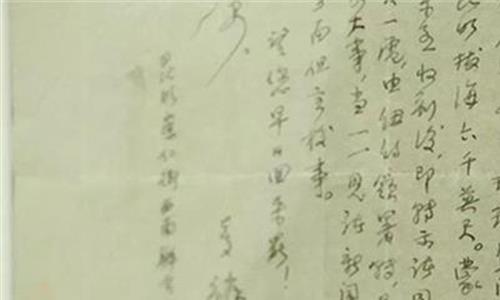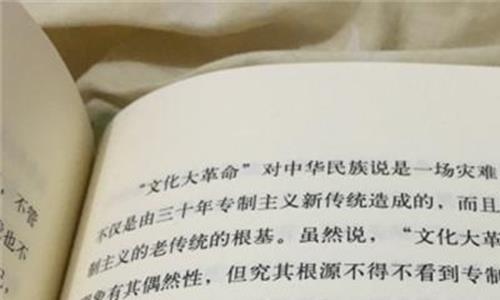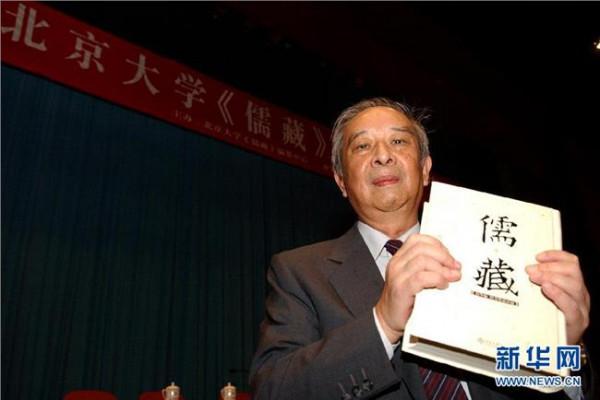汤用彤挽联 我认识的汤用彤先生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

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

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

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

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呵。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
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
《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
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我们中国文学教研室解放后新留的10个青年教师,8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就翻腾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房长孙——我的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
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
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四清”,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像也有福气!1962年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
毛主席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
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
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
毛主席也跟我们和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
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
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本文摘自《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活(1948-1998)》,乐黛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