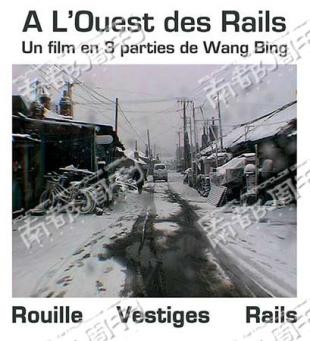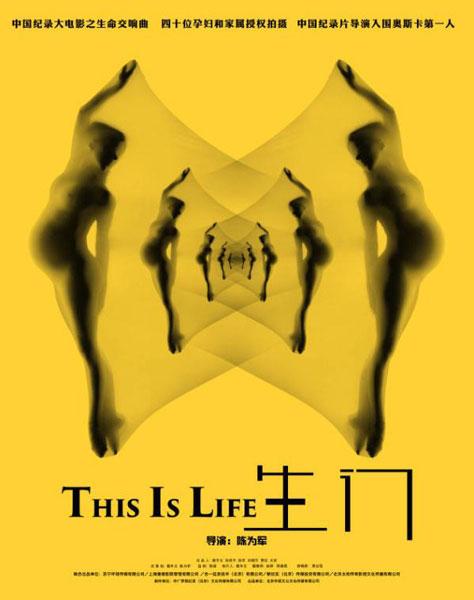陈晓卿美食纪录片 不拍美食纪录片的陈晓卿是什么样子?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纪录片此时恰恰应该是沟通的使者。”
陈晓卿在广院学的是摄影,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功课不错,老师喜欢,他说自己那时“很不开化”,由于脸比较黑,可能也不太容易引起女同学的好感。

大学期间,他就对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等早期纪录片很感兴趣,后来又接触了许多60年代风行于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纪录片流派—“直接电影”的作品。这种纪录片主张对镜前事件不摆布、不干预、不控制,只是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把捕捉到的一个个生活瞬间在作品中串起来,从而给人以超越生活原生形态的思想启示。

年轻时的陈晓卿
四年大学念完,陈晓卿被推免念研究生,专业是摄影美学,而后也顺风顺水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
1986年,正读大四的陈晓卿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实习,他经常被安排出差。有时候,即使拍了七天,有许多素材,回来后也只是编了一条新闻。他心疼自己拍摄的东西,就偷偷在机房里编着玩,结果鼓捣出一个15分钟的片子,带他的老师刘效礼偶然看到,觉得不错,起名叫《战士从这里起步》。

1987年,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到北京广播学院讲课,陈晓卿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听课,他的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伊文思看了。伊文思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陈晓卿:“你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
伊文思导演
“为什么不能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交给观众呢?”伊文思还说了说了这样的狠话:“你们都叫我老师,可我在这儿没有一个学生。”这话让陈晓卿大受刺激。
从那时起伊文思的几句话真正地影响了他对纪录片的认识,也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纪录片不只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寻找什么,还要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本身。
后来,陈晓卿拍了很多纪录片,当他被问及最满意的是哪部时,他谦虚地摇头,“没有特别满意的。觉得还过得去的应该是早期拍的东西,那是真正花心思去拍的东西,比如《远在北京的家》和《龙脊》。”
《远在北京的家》拍的是几个到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一个安身之所,独自面对颠簸不宁的生活。
灵感来源于还在读大学时的陈晓卿回家时与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一趟车,从她们故意卷舌说北京话中看到了一种变化。那时想拍就立马行动了,摄制组是临时组建的“草台班子”,把设备科的人灌醉了偷摄像机出去拍。一门心思拍片,拍摄都在业余时间完成,经费不多,还常常自己贴钱。
陈晓卿把粗编带给自己的导师看过,朱老师感动得哭了,又给周传基老师看过,周老师看完兴奋地骂了一句“他妈的”。片子拍出来好评如潮,1993年《远在北京的家》送去参加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得纪录片大奖。
一部片子拍完,其实他也未想过获奖、名声的事。陈晓卿说,“我对自己的过往,从来都不在意。家里没放过一个奖杯,也没有出过纪录片作品集。我也不愿意别人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作品,这只是我的工作。”
对工作还是对人,陈晓卿都是赤诚相待的。纪录片里的安徽小保姆到北京闯荡,她们都把陈晓卿当作可以倾诉烦恼和咨询的知心大哥,甚至一位小保姆在北京迷路,民警问她在北京有亲人吗,她说电视台里有位大哥,最后还是陈晓卿帮她找到了远在北京的家。
后来,陈晓卿去拍《龙脊》。拍摄地点定在广西山区,那种苦、累至今还让他忘不掉:“第二天早晨开始爬山,到了下午两点才走到一个寨子。我累极了,躺在板凳上,头耷拉在地上就睡着了……”
在这个忽隐忽现在白云深处的小寨村里,陈晓卿扛着摄像机拍了一个多星期,见谁拍谁,见什么拍什么。小寨村的村民一开始在摄像机前既惊奇又紧张,慢慢地,也就习惯了。陈晓卿的纪实创作才真正开始。
和潘高能一家这一主要纪实对象,陈晓卿与他们相处更像一家人,所以在摄影机面前,他们呈现了真实的生活常态。
“发现平凡生活里的乐趣,那种快乐,多少钱也换不来。拍《龙脊》时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课,小主人公上台解题,完了老师带领同学们表扬他:‘潘能高,最能干,潘能高,最能干。’这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由爷爷带着。爷爷原是桂北游击队队员,整个人都系在这孩子身上。
摄制组进村时,村长说,去潘家聊吧,他汉话说得好。聊着聊着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课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里去……’爷爷马上拖着个板凳凑过去看孙子念书,就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也不理我们了。后来我们拍爷爷教孙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爷爷站起身说:‘潘能高,真能干。’唉,我们拍到这些的时候,真是摄像机都不想要了,扔田里算了。
——陈晓卿
所以我们会在这部纪录片中看到生活本身,镜头下有被纪实者的生存状态,也是被陈晓卿的心折射的现实,其中有各样人生体味和审美情感。而这“心”说到底是一种个性化的“人文关怀”。
拍片是个苦差事,但在陈晓卿眼里,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乐事,不只是享受拍摄的过程,不只是为了获奖荣耀,还有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动。当年《龙脊》几个月的拍摄,陈晓卿对寨子感情很深,几乎变成了寨子里的人,拍摄完成,摄制组走的时候,全村1000多人都出来送他们,一直送到山口,村里人哭了,有泪不轻弹的陈晓卿也哭了。
“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还算个年轻人吧,对社会,对生命的理解今天看来都是那么浅薄和幼稚。我在深山里前后呆了半年,每天把镜头对准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他们没钱上学这一件事儿,我天真地认为通过我的片子唤起人们的爱心。”
拍摄《龙脊》时,陈晓卿给一个叫潘纪恩的孩子提供每年的学费,直至供他念完大学。潘纪恩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娶妻生子,他的父母每次到北京看儿子,总是下了火车第一个跑到中央电视台看看陈晓卿,之后才能安心地回儿子家。几十年陈晓卿一直和潘家保持来往,就像亲戚。
“无论拍土豆还是拍上帝,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我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片子。”
2007年,陈晓卿去拍了国内第一部生态纪录片《森林之歌》。当《森林之歌》走上荧屏后,国内一片哗然,每个镜头、画面,甚至解说,都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出自BBC之手。
《森林之歌》是由陈晓卿导演的一部大型生态纪录片,从编剧到拍摄整整花了4年。每个编剧至少被打回去了四五次。陈晓卿有他苛刻的道理,“一定要把它做得吸引人,否则可能观众已经谢幕,热情而激动的纪录片还久久不愿离去。”
“长时间不刷牙、不洗澡,一身动物的味道。”对摄影过程的艰苦,陈晓卿轻描淡写地说一句。2007年春天,摄制组的人回到办公室时,因个个蓬头垢面、形如乞丐,险些被门卫拒之门外。
到了后期,整个摄制组除了陈晓卿外,全部被圈养在办公室附近一个四室两厅的单元房里,吃喝拉撒以及工作全在一百多平米之内完成,他们管这里叫“森林集中营”。
成片十分美丽,如陈晓卿所说,“镜头像眼睛一样,清澈的眼睛有时会让我有挺心疼的感觉。”当飞机在画弧线的节骨眼上,云缝中投下一束阳光,恰巧照亮老银杉所在的山脊……那画面,由不得你不肃然起敬。有网友就说:《森林之歌》那些镜头,“绝对是深深被自然感动的人拍出来的。”
陈晓卿说,见证过的消逝,正是为了让自己平静地看待死,愉悦地享受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我正在记录的森林:
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要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在热带雨林里,每年每公顷土地上有15万棵幼苗生根发芽,其中仅仅有不到1%的幼苗能长成大树。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拍纪录片正是这样一种幸福,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很沉静地关注着一段故事,与你拍摄的人物共同走完一段历程。那是真的自己。
“出去拍片比坐办公室好太多太多了!”陈晓卿时常感叹,他想做的事儿很简单:“能一直拍下去。”多年来,他一直铭记导师的谆谆教诲:“不做官、不发财,专心做专业的事。
正如威廉·曼切斯特在他的《光荣与梦想》一书的最后所说的:"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中国队长纪录片 中国队长[纪录片]](https://pic.bilezu.com/upload/c/fc/cfc5e3ea187fe548f887b14173b76ad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