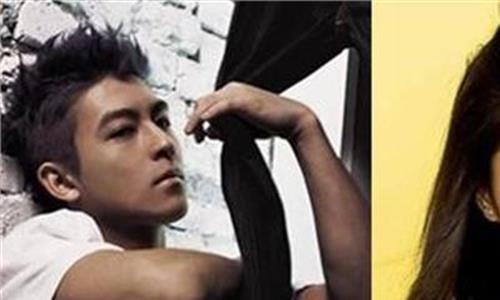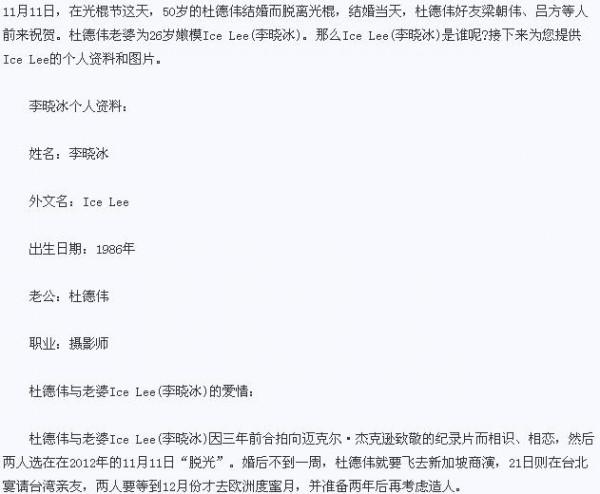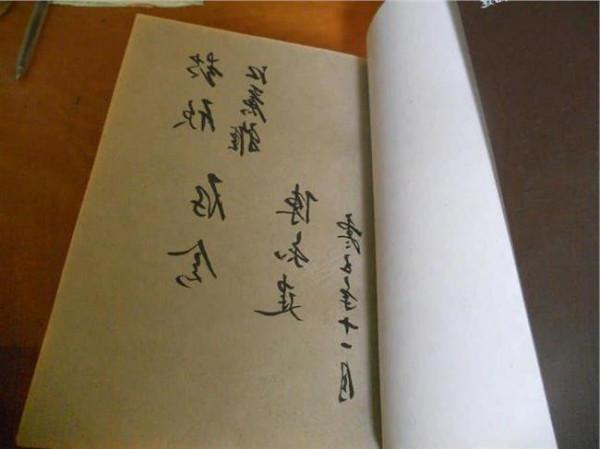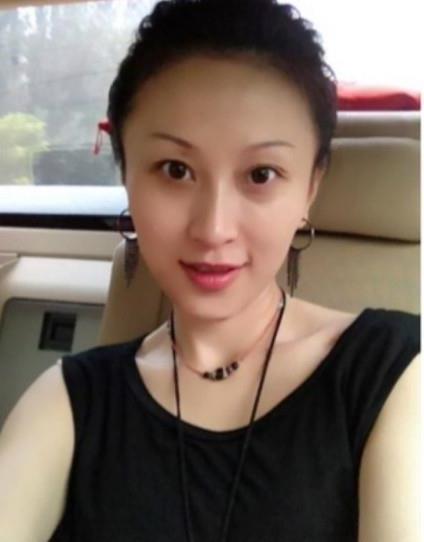陈晓卿第二任老婆 陈晓卿:摆事实 不讲道理
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
话说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灵璧县城,14岁的男孩小清子猫在粮站门口,探视他可能的未来。

他很淘气,初中毕业会考分数够不上录取线,因为父亲在这所中学任教,被“照顾”进了高一。母亲说,考不上大学,进粮站开票是没问题的。
现在,小清子正望着那个开票的瘦男人:眉毛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像当年的动脑筋爷爷——他困顿地望向天花板,长久保持这个姿势,每当运粮女工从身后过,他会飞快地转过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飞快地转回来,继续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开票男呲出黄牙,奋力从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犹豫地,按在桌面上。

小清子一路狂奔到家,迅速拿起数学课本。1982年,他考上了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因为个子高,不近视,从第一志愿新闻编采专业落进招不满的摄影专业。这一段,被陈晓卿(小清子的学名)概括为“一坨鼻屎改变的人生”。
2007年盛夏,北京西客站附近一个部队干休所,央视《见证》、《探索?发现》、《人物》栏目都在这里。《见证》机房里,有用到极难看的微波炉、几张行军床。据说,陈晓卿最亲近的办公伙伴是一方小毛毯,抖开一搭就是一夜。办公室里往来全是汗衫板拖,大嗓门儿不少。二楼走道一块牌子上有行小字:真实就是力量。
平头、面皮黝黑、眼睛炯炯放亮的陈晓卿坐在里间啃一份汉堡——昨夜又通宵,干到凌晨5点,这会儿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在徒弟眼里,他是各地纪录片人的北京办事处,是眼里闪烁着纪录片光辉的沙龙男主人,是磁场强劲的男“交际花”,是一个真小资;他对自己的评估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他以给周围人带来快乐为己任,他的手机里存着京城几百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
“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
80年代的北广云集了童宁、崔永元、时间、白岩松、黄海波,以及一大批日后撑起中国电视的年轻人。当时,自封“婚纱摄影专业”的陈晓卿很长时间不适应画面思维,似乎也没热爱,只是海量地看外国片,故事片、纪录片、毛片,什么都看。
“那时候的业务气氛真是浓,下了班儿,22楼的灯彻夜长明,都在看片儿。”
师从朱羽君教授读摄影美学硕士,学到最多的是怎样做人。“不要当官。”朱教授说。陈晓卿说他生来怕长官,当年进出老师家,与朱教授的爱人(当时央视副台长)没说过超出“您好”、“谢谢”、“再见”之类的话,直到副台长快退休了,他才意识到“有很多话可以讲了”。他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这是后来拍纪录片很重要的素质”。
1986年,拍过《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斯到北广讲课,陈晓卿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老头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他哭了多久?”“10来分钟。”“你拍了多久?”“十几秒。”“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老师说过,特写镜头不应该超过5秒。”“为什么不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交给观众呢?”陈晓卿心里一震。
“那时我们的纪录片观念太落后了,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剪辑出来,从没想过让画面里的人自己走出来说些什么。”这样的作品看得伊文斯很着急,老头说过这样的狠话:“你们都叫我老师,可我在这儿没有一个学生。”这话让陈晓卿大受刺激。
有段时间,陈晓卿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旁听司徒兆敦和周传基的课,跟两位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司徒老师家床底下全是录像带,有时老师不在,他跟师母打个招呼,在床底下淘啊淘,揣上几盒走人。
侯咏、吕乐摄影,法国人导演的《怒江,一条迷失的山谷》,改变了他即将开拍的《龙脊》的许多想法;迈克?摩尔的《罗杰和我》,多年之后他拿着给传媒大学的学生讲了好几堂课;还有艾伦?米勒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1991年,他第一部纪录片、讲述安徽洪灾的《孤岛纪事》在央视播出后,台里前辈李绍武说:“这片子怎么像外国人拍的。”陈晓卿特意找到李老师请教:“您觉得这片子拍得不好?”“这是最好的表扬。”李老师说。
这片子是怎样拍出来的呢?陈晓卿找了淮南电视台一个朋友帮忙,一台车,一部3/4格式的录像机。没钱,住制播合一的办公室,下班必须锁门,他得提前买好吃的,夜里只有小便的地方,大的不行。他在一个被洪水困住的小岛上生活了23天,拍救灾,更多的是拍受灾百姓的生活。带子金贵,同去的人总是提醒他:够了吧。他还是拍啊拍。尽管片子备受好评,但他心里清楚:洪水是什么,电视上播出的画面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拍到这些,摄像机都不想要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那种空讲道理特别逆反,我就想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纪录片恰恰能实现这个。”
“但是你选取这段事实,不选那段,这里面肯定有你的价值判断。”
“肯定有。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不一样,时间拍的《周恩来》是这样的,邓在军拍的《周恩来》是那样的;刘敬坤看到的流亡学生和钱钟书看到的完全不同;何兆武眼中的青春跟杨沫眼中的也不一样。这是允许的,非常自然,不是说一个东西它从根上就是红的或就是黑的,你看到听到,经过大脑过滤,最后说出的,是你内心想表达的。”
《远在北京的家》就是他人的故事在他内心的投射。那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整10年,住集体宿舍,跟江和平(现央视体育频道总监)一个屋。“每次他老婆来了,我就上外边玩儿去,我老婆来了,他上外边玩儿去。看着晚上的北京,心想,操,这他妈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有几次坐火车回家,陈晓卿听着到北京做保姆的同乡女孩卷着舌头说话,就动了拍她们的心思。他和安徽台的同仁摸到安徽无为县妇联,找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车,坐火车,一直跟到她们进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顿下来,历时一年半。城市的冷漠、伪善,外来者不停地委屈自己迁就它、适应它。片子粗剪出来,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过头看,陈晓卿觉得它在技术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动了情。他的学生认为这是陈老师最好的作品。而另一头,10多年过去,那些姑娘有事还会跑到央视找陈晓卿。
1993年,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央视的《生活空间》等,破天荒让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荧屏。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隐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单一和苍白。步入21世纪,这类片子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让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他讨厌这样的节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个词:纪录片的贞操。他说,就算今天已经很开放了,“贞操”还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绅介那样拍到死。无论拍土豆还是拍上帝,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他自信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片子。
“发现平凡生活里的乐趣,那种快乐,多少钱也换不来。拍《龙脊》时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课,小主人公上台解题,完了老师带领同学们表扬他:‘潘能高,最能干,潘能高,最能干。’这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由爷爷带着。爷爷原是桂北游击队队员,解放后在兴安火车站当巡道员,后来回到山里成亲、当农民,整个人都系在这孩子身上。
他是村里惟一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泽东。摄制组进村时,村长说,去潘家聊吧,他汉话说得好。聊着聊着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课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里去……’爷爷马上拖着个板凳凑过去看孙子念书,就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也不理我们了。
后来我们拍爷爷教孙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爷爷站起身说:‘潘能高,真能干。’唉,我们拍到这些的时候,真是摄像机都不想要了,扔田里算了。”
“让普通人不畏惧你的镜头,难吗?”
“一点儿都不难。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一个农民,一个打工仔,他可能有说假话的企图,但可能性很小,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在瑶族村寨拍《龙脊》,前一个月拍的素材几乎没用上,后来渐渐不同。
“拍一个孩子割猪草回家。他从山上下来,我们提前跑两步,拍他开门,扔下猪草,跨过摄像机,当我们是他们家的狗一样,哈哈。”
从《刘少奇》到《森林之歌》
拍完文献纪录片《刘少奇》,陈晓卿见到了刘的家人,经过关键人说服,王光美同意接受采访。1998年2月的16天里,摄制组每接到通知就扛着设备,赶到木樨地王光美的家中,从头说起,包括在西柏坡的婚礼。老人的修养、党性、坚忍,让他落了泪。
因为某种原因,最终成片的12集纪录片里,王光美的访谈不到5分钟。去年老人去世那天,陈晓卿接到朋友短信时正在同学聚会的热闹里,他挣出来清静了几分钟,稍后写了这样几句话:“那些磁带静静地躺在中央电视台的素材库里,恒温恒湿。希望我将来的同行们能够发现它们,善待它们。”
从徒弟金铁木花3年时间拍完的《圆明园》,一路谈到任学安总编导的《大国崛起》,陈晓卿有保留地赞扬,这些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他一歪脑袋:“实现了初衷的50%?”他断定,一个为国家电视台工作的有思想的编导,必须放弃一部分个人理想。
1998年,陈晓卿深入阅读党史和传记,所以今天他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有出入。那些难得的采访经历已转化为对伟人、对历史的再认识,种在心里。拍完《宋庆龄》,他渐渐淡出文献片,回到普通人中间,用他的话说:接地气。
《见证?影像志》诞生于2000年11月27日,前身叫《纪录片》,从早先的历史文化领域转向社会史、民生史,定位于记录中国当代变迁,子夜播出。
这批常被深夜剪辑机的荧光映得面孔发绿、随时可以和衣而卧或者整装出发的纪录片人,瞄准的是《国家地理》、D iscovery和BBC纪录片。他们记得陈晓卿在机房反复说的那句话:摆事实,别讲道理。他们也记得栏目的《圣经》是年鉴学派著作,目标是成为中国影像历史的一部分,入图书馆、档案馆。
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他说。
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糅起来、串起来,《见证》试图尽可能传达多种声音和信息,就像药剂里的复方,这是陈晓卿目前的“真实历史观”。
被打捞的记忆、大量的细节,随画面上步鑫生、张蔷、穆铁柱、汪国真、毛阿敏、少年大学生宁铂,或者砖头录音机、牛仔裤、霹雳舞、模特儿、朦胧诗、托福、深圳速度、涉嫌裸体的机场泼水节壁画一一展现。他对细节的敏感,也许是由童年故乡西关澡堂子里木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一路淌过来的,所以在巫山拍片时,旅店女主人提把暖壶过来续水,他能一眼望见上面4个字“移民光荣”。
2003年,有了笔钱,领导说,做个自然类的节目吧,于是请老外来做培训,接着全栏目人马分组奔向森林。人数最多的一组也就3个人,在大兴安岭、长白山、秦岭、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方热带雨林一次蹲上20多天至75天不等,精打细算着航拍……
3年过去,长焦、红外以及微距镜头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大熊猫、金丝猴,会飞的鼯鼠、美丽的碧凤蝶、芭蕾舞演员般的黄猄蚁、万分之一克重的胡杨种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审片时,领导问:“这都是你们拍的啊?”组里的人答:“都是。”
拍片期间,各摄制组都欢迎陈晓卿上他们那儿去,因他号称“活体蚊香”,“关键是气味,人的气味可以吸引10公里之外的蚊子。”3年下来,连他儿子的自然知识都大长,“可惜中国没有博物学家,搞科普的同志都在吵架。等我们真正明白该怎么拍,摄制已经快结束了。”
这边在遗憾没能把对生命、轮回、报应的理解完全表达出来,那边拍秦岭的编导已经收到国际灵长类动物研讨会的邀请函。“照说,这么大的央视,也该有个野生动物部。”他说。
11月19日,耗资1000万元、描述中国森林版图的11集纪录片《森林之歌》开始在央视播出。跟3500万欧元的《迁徙的鸟》和BBC耗资1700万英镑的《地球脉动》有一拼吗?他嘿嘿一笑,“到时候看。”
小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的电话是那种捆着干电池带摇把儿的,打电话的人总是对着那玩艺儿吼,说给我接哪哪哪。听说电信要恢复这种电话,他很想对着它说,请给我接地气!
他怀念那些日子,比方在杭州朋友家吃掉朋友母亲做的一整只酱鸭,把老太太看傻了。 “现在好像最好的朋友都不到家里去了,见不到父母了。”他怅然地说。现在更多的是饭局上笑呵呵摇了半天手,暗里使劲回忆:“这孙子是谁啊?”
每年春节前夕,透过办公室的窗户,他能闻到西客站传来的回乡的气味。他就想,我得回去了。可是,父母在北京,房子车子孩子都在北京,回哪儿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