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元马志明 马志明:马派相声回眸
在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黄族民,这黄族民呢是中央制药二厂的工人,当过几天干部,他爱这个行业,在业余里玩过几天。开始我不想用他,因为基本上传统东西他都不会,我在他身上我得下工夫。可是呢,也有好的一面儿呢,像这种“生坯子”如果教出来,比那个好多有毛病那个现扳毛病要容易点儿。
黄族民这个人呢,很正直,从87年跟我搭伙一直到现在,十三年了,十三年呢团里边就不给调进来,每一届“津门曲荟”都跟着演,什么叫慰问部队了,什么公益活动了,团里的所有活动,黄族民都是义务的,单位请假扣工资在这儿帮忙。
但是不知怎么个原因吧,领导总在说在调,说请示局长给调过来,局里不同意,始终就没给调。没给调到去年的,前年——98年——我身体不好我提出来我退休吧,我找到局长,我一问呢,我说我退休,看看年龄也够了,我们团比我小的都退了。
“你干得不挺好吗?”局长说,我说:“就连个伙伴儿跟着我十好几年了都调不进来。”我跟局长一提呢,局长从事业出发:“给他办!”一个星期,98年就把他调进来了。一分钱没花,反正就进来了。
黄族民呢,这个事业心相当强,就说一般的如果说跟一个专业的人员搭伙,目的是为了进曲艺团,为了从事专业,把我那个工厂的活撂了,我跟你干这个,起码轻省吧。如果说,三年五年调不成,那就放弃了,一般规律是这样儿,没有可能就算了我也不给你捧了,我该找别的路子就找别的路子了。
而他不然,调也好不调也好,他是(星期)一、三、五准到我家来,他岁数比我小,身体也比我好,一、三、五准到这儿来。你给我念什么活我就听着,我就学。
可以说是我从干这行以来,搭这么多伙,跟我合作的伙伴儿里头,两个人掌握段子最多的就是这个黄族民。黄族民这个人呢,也是在这行里头不可多得的人,他出身于干部家庭,他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候受伤的,炸掉一条腿,那是老干部了,离休以后后来过世了,他母亲也同样。在他身上有很高的人的素质,决不轻诺寡信,这人是一个守信义的君子。
他跟我搭伙这么多年,一般的伙伴都因为钱上产生矛盾,以至于最后散了,黄族民不然。因为从我这角度,我本着一个……没有藏着掖着,都是公开的,我要不我不用你,你这人不行,我不用你,我找别人。我既用你,我就相信你,我绝不在任何小节上给人不愉快。
比如说演出吧,演出的单位就说:“马老师,我们拿车接你去。”我说:“我们自己去也行。”“不用不用,我们有车。您在哪住?”我说我在什么三德里胡同,怎么进去,“那黄老师他在哪住?”我说他在兰州道里边,有个派出所,旁边……一说,反正挺费事的,人家不熟悉:“要不这样行不行?让黄老师到您那集合去,到点我们拿车把您俩一块从您家接过来。
”这种情况很多,作为我这方面,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我说:“这样吧,你先接我,接完我,我领着这车去接他。
您不是不好找吗……”“还是应当先接捧哏的,然后再接您这逗哏的。”我说:“咱们没这些事。你先接我,我跟着车绕。”绕,把他接上,对他给与应有的尊重。
或者说上火车,给我一个软卧,人家不说你这艺术也好,以这级别也好,人家说你岁数大了,你身体不好,你来软卧,他来硬卧。这样呢我力争给他要个软卧,如果要不来,我也换硬卧。我老跟他一样。或者到哪吃饭,人家往外调:“刘?英刘老师,严建国严老师,马老师,您几位出来一下。
”“干嘛?”“您到这屋来。”到这屋一看呢,有人家领导陪着,甚至于菜的质量也不太一样。“哎,我说,黄族民呢?”“他在那屋吃。”我说:“别介,要不我也跟那屋吃,要不就把他叫过来,你选择。
”往往呢就把他也叫过来了。就说不应当在伙伴中间造一种让他我低于你(的感觉),这样呢,从大局上说,对事业有好处,对我们这场活绝对是有好处,他也就有了责任心了,不然的话,“咳,我这个,我这……我跟人家比吗?”他一产生这个,就没好处了,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有的人呢,他就是无事生非,他自己不研究自己业务啊,他琢磨别人,想法给人拆对,黄族民从来不受调。在北京演出,吃早点。
北京有一位艺术家吧,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不知道怎么想起来了:“小黄,走,咱们这边吃去。”吃早点不分回民汉民,都是花生米啊,酱豆腐啊,茶鸡蛋啊,牛奶啊。(把黄族民)叫一边去了:“你知道你们这场多少钱吗?”按他的想法呢,这场多少钱我不跟黄族民说实话,他要在这里边挑拨一下,“你们演一场,志明给你多少钱?”黄族民回答的呢,一句就把他噎回去了:“这场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也不知道。
反正每次领钱都是我去领,你不要调了,我经手。
至于给我多少,他都给我,他愿意,我都给他,我也高兴。我们俩不分彼此。”这一句,这位先生就灰溜溜了。有时候有些人呢他就利用这个,有点成就的,或者两个人搭伙,老话“搭伙三年,不火自赚”嘛,如果搭了三年伙,这对就磨合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个劲敌了,很容易台上就打不过他了,用这种方法,把他们调散,但黄族民不受调。
相声比赛最近这些年不怎么搞了,也可能是相声演员新的一fa的,年轻一fa的少一点儿,年轻的都演小品,都搞别的去了,专门为这个相声下功夫的人不多了。老一fa的,成名成的那些笑星们呢,人家已经都功成名就了,再有比赛也不愿意参加了,再参加万一没得奖呢?就功亏一篑了,前功尽弃了,没好处。
我一共参加过两次比赛,第一次是86年,1986年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专业相声演员大赛,那次我拿的节目是《五味俱全》,这《五味俱全》呢是我们团编导组的朱学颖,他出的点子,师世昌执笔写出来的,后来经过我的加工,里边很多重点的包袱儿,都是按照我们马氏相声的手法(加工的)。
我觉得这个段子不错,虽然是连练本子,带改本子,一共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在复赛的时候效果相当好,现在电台有时候也总爱播吧,你也可以去听一听。
那时候是谢天顺给我捧的。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了,不管什么原因吧,没进等次,一二三等都没我的份儿。我在复赛以后,有一位老专家握着我的手:“不要骄傲,你这个一等奖拿不了也得拿二等奖。
”当时那种气氛是那样的,我们老爷子听完了以后呢——他是顾问——在台底下听完以后呢,亲自摘下一个戒指来,这个戒指不值钱,但是这个戒指年头很多了。
这是在刚好起来,解放前刚业务有点儿好转,我们家就可以吃“金裹银”的面饼的时候了,里边一层棒子面外边一层白面,能吃上白面的时候了,买了这么一个小戒指,上边刻着“马三立印”四个字,这是个纪念物。
(老爷子)就把这个摘下来:“这个给你吧!”谢天顺在旁边看着嘛。我当时就说呢:“我要这个可有愧,这样吧,您家也没有电视,”1986年老爷子家没有电视,我说:“等我这一等奖拿下来,”因为当时我心里想,我这一等奖十拿九稳,“一等奖拿下来,这彩电给您,拿那个换这个戒指。
”谢天顺也挺高兴:“没问题,准拿啊!”后来在赛完,结果呢一公布,我就算优秀奖,优秀奖就算等外了,有“荧屏奖”,有“优秀奖”,再上来是三等奖,再上头是二等奖,再上头最高一等奖。没拿等,我又把这戒指还给老爷子了。
我经常爱到派出所串门儿。我们这剧场叫中华剧场,在和平路南市口,斜对过儿,有一个治安派出所,我爱在那串门儿,跟这些干警们也都很熟。目的呢,一是解解闷儿,另一个呢,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了解社会,观察动态,收集资料,有助于塑造相声的人物,搞创作。
有一天,我正在那坐着呢,就看见两个人揪着就进来了,抓着胸脯附近的衣服,不依不饶,骂骂咧咧,进来打官司,找警察评理。什么事呢?这个人啐痰,随地吐痰本身就不对……崩一个点儿,崩那个人袖子上了。那个不饶,“赔衣服!
”到了派出所一看呢,那个点儿都找不着了,都干了。民警一问这情况,也摇头:“这怎么办?……你们俩先上那屋呆着去,现在没功夫问……”就把旁边小屋的门打开了。就是我创作《纠纷》里说那小屋。里边有两条长凳子,两个人坐下了。
他们俩进去以后,我就问这民警,叫陈健,我说“小陈,像这种问题你们怎么解决?”“这个没法解决,这俩人素质太低,这叫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只能是冷处理,降降温,让他们自己消化了。你看我的,一会儿,他们俩自己就解决了……”果不其然,不到一个钟头,两人就出来了。
“同志,我们跟您说说……”“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他故意地不说。“我跟您说说……”两个人直求,“我跟您说说,我们俩就算完了,都解决了,给您添麻烦了……”两个人都走了。
我发现,哎,这个好,而且街上很多纠纷、矛盾,究其原因,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蹬鞋、踩袜子了……无非是这种事……一句话,不爱听了……应该互相谦让,得有这种精神呀,把精力都放在四化建设上,这多好。当时,正提倡安定团结,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
“就要这‘稳定’!”当时,我就萌发了创作的想法。晚上……用了差不多一宿……天快亮了,我实在困了,才睡。就把这段子的轮廓、梁子写出来了。我没说啐痰,我就说拿自行车轧那个人脚了,改了这么一点儿。
其中,这三个人物,民警;这两个人,一个丁文元,一个王德成互相的那些话,都是我编的。是我观察街上的人爱吵架呀,爱拌嘴呀,这个档次的人的语言,跟民警的语言把它揉和在一块儿。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吧,搞了这么一个段子。
为什么这个段子用了半年的时间呢?要说写本子,跑这梁子,是一宿,然后逐渐地改,随改随着观察、修理。就说这几个人物吧,这名字,这名字我当时循着咱们相声界的老道儿,一般上舞台上提名子都提本行业的人。“说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叫什么名字呢?叫王富贵。
”王富贵就是我们团弹弦的。说这《三字经》,我们同学,同学有谁啊?有白全福,有郝树旺(?),有沈君,有曹永才,都是我们团的,这样也避免某些个人多想,“哎,是不是说我了?”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你随便编一个名字,你在全国里准能找出几个人来,所以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叫丁文元,丁文元是杨少奎老先生的大弟子,他的四个徒弟叫“元、亨、利、贞”嘛,丁文元,刘文亨……元、亨、利、贞,按这个排的。
丁文元现在在张家口曲艺团,退休了,还在张家口住着呢。另一个呢叫王文进,丁文元,王文进。王文进也是杨少奎的徒弟,他后四个徒弟叫“学、习、进、步”。这个人呢,王文进。后来我一斟酌呢,这两个人打架,都带“文”字的,也不太好,明显的是“文”字辈说相声的俩打起来了,又经过改呢改了王德成。
王德成呢是我一个好朋友,是天津有一个大画家,油画家,王麦杆,他儿子,叫王德成。我们两家下放在农村,都是邻居。
他跟我也挺好,我用他名字,他也挺高兴。确定下来,一个是丁文元,一个是王德成。民警没有名字,就“民警”就行了,代表一个公安机关正面人物,这三个人。我这段子一开始是单口相声,我也想尝试一下,因为每次曲艺团的相声专场、津门曲荟啊,都是俩人一对,俩人一对,俩人一对,最后演七个、六个散了,这里头应当呢当间有一个差乎差乎,有一单口,这也符合过去的规律,换换口。
我呢,虽然能说几个笑话吧,但是像这种专门的一个单口相声还没有,我自己给自己写这么一个。
我一人在台上说,又是丁文元,又是王德成,又是民警,又是我这个旁叙,我这个叙述者,就是我本人。那么四个人,四个人的段子,一个人说,那就说呢:王德成说什么什么,丁文元又说了什么什么,民警同志又说了什么什么,我认为怎么样,丁文元又说……这玩艺儿倒腾,闹得慌不闹得慌。怎么办呢?我考虑就用这声调来区别。
这四个人,从发音上、从语言上,让他有差别,有了差别以后呢,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丁文远说,那是王德成说,用不着了,一变脸,一变声,让观众(马上明白),这是丁文元,这是民警,这是王德成,这样呢,既简练,又真实。
那么这四个声音,我的声音就不用动了,民警呢,也比较好塑造,干部的声音就行,关键是这俩人。这俩人都是玩儿闹,都是这种素质比较低(的人),我就考虑了,这王德成呢,把他刻画成一个30多岁的,也就是说成家了,有老婆孩子的,这丁文元呢,20出头,20出头还没结婚,比较幼稚,不知天高地厚,不懂法,就一个小法盲,但是不是多坏,说这俩人都是犯法分子?都不是,都是缺乏教育。
一个年轻点呢,嗓音让他稍微窄一点,那个上岁数的呢,就是天津有这么一类,就类似我们团里头有几位,就是他这个声音,“少……少跟我来这一套!
”,就这味儿的,宽,而且似乎是有点结语又不是结语,说话慢,他那节奏不均匀,这类的话,就给王德成。丁文元这声音呢,就费事了。
有一天呢,我到北京电视台录像去,回来呢在火车上,火车上有这么几位在王府井做买卖的,每天早上去摆摊,下午六七点钟回天津,在那给人打工的,这车上有这么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小子认识我,就跑我这儿来了。
“你是那说相声的马志明吗?”我一听这声音怪,我说:“你在哪住?”“我东方里……”我们那儿怎么来,怎么去,跟我聊起来了,对相声还挺懂,跟我聊了一道。他聊的东西我没记住,但是他那声音我可记住了。
哎,我一听这味儿好啊,就像一个女的声音,有人乍一听以为我这刻画一个女的呢,其实不是,他是天津单有这么一路人,小细嗓,太监嗓,这声音跟王德成那粗嗓子差开了,这样呢,人物就比较鲜明了。我把他这么设计好了以后呢,这段子我就在天津市政协礼堂,有一天民主党派的一个联欢会,民进,在那会上,我试一试,因为我心里也没底,究竟效果怎么样?我要把它见见观众。
那时候民进的主委,天津市人大副主任,杨坚白(???),杨老,他在那听,哈哈大笑。我一试呢,出乎我意料,呦,这么好!
《纠纷》这个段子出来以后呢,我的处境是越来越不好。第一呢,我这叫……我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吧,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二届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在大连有个“星海杯”。我忘了是谁找我呀还是怎么回事,就让我拿这个《纠纷》去比赛去。
可那个时候呢我又没捧哏的,我不知道团里是领导布置啦?还是……我求谁谁都不去,谁都不给我捧。在那种情况下呢,因为本身我这是单口相声,捧哏的最好一句话别说,别搅和我最好,我就用了一个唱山东快书的一个不怎么上台的演员,基本上我没怎么看他演出过,叫李凤祥。
我说:“你跟我去。”他说:“我哪行,我没说过相声。”我说:“你试试。”“行!”他那儿也挺高兴,就到大连比赛去了。大连比赛呢,我以为呢这个作品,最起码从作品说吧也会获得一个好名次的。
经过复赛、决赛,最后勉强给了我一个三等奖。后来报纸上我也见过几篇儿,有不少人写“冤了”,给得低了。在评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咱也不知道内幕的东西了,但是我想呢不管他怎么给我低了,我认为两次相声比赛我都是一等奖。
实践证明,我这两个段子,电台播放,现在还有人邀请,点我这个段子的,很多。不少人还是拿着我这《纠纷》去模仿,去改成了MTV,甚至于很多小年轻的,小学生都学我这段子,我就是一等奖。当时的一等奖那个段子我不记得是谁了啊,我相信没有这么大影响。
我这个《五味俱全》,别人说(好的)不少,最难得的就是我父亲。我父亲呢,手里头很少有相声的音带、像带。从一般来说呢,他不怎么爱听相声,他自己琢磨他不爱听别人的。他在中青年以前他听,他老年以后,听个一句半句。
他特意找到我“你把那个《五味俱全》给我录一盘儿,我听。”我说:“您听这个干嘛?”“好!这个从表演到作品,我认为都够水平。”他没事就拿录音机放这段,反复地听,甚至于他都背下来了,老爷子对我的评价,有些段子最多也就说“你这还行”,甚至于有的“这可不行”,“这个一般”,我没听过说好,说好的就是《五味俱全》,现在您有功夫去问问老爷子,绝对认为我这段儿(好)。
不然的话他不会把他的戒指摘下来给我。《纠纷》那就更别说了,《纠纷》的社会影响要比《五味俱全》更大,尽管我拿了个三等奖,我认为去得还是有必要。
这个《纠纷》从播放以后,在社会上影响相当大,我亲自看到的,经常听别人说的大街上两个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起来了,以致影响了交通,这时候往往要出来一位两位:“得得得,你都吃饱了撑的。你就是丁文元,你就是王德成,这不没事找事么,赶紧散了完了!
”就解决一些问题。我周围一些观众呢,见着我也都赞不绝口,而且呢对我提出要求,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来个二本儿,二本儿,三本儿。有些个公安机关啊,派出所啊,给我也来信提供很多的材料,希望我能够再写。
在下一届“津门曲荟”,就是说在《纠纷》的下一届,两年以后,由于这个……一般领导不支持那是他的事啊,我最崇拜的我最孝敬的是我们的观众,观众说的话我认为是最高的,我听观众的话,我要按照观众的要求去搞创作,我又写了一个《听曲艺》。
因为这时候呢,从大势上应当弘扬民族艺术,曲艺呢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但是有些个观众呢不太爱听曲艺,好像曲艺跟相声是两码事。我为了弘扬曲艺,也让人说明一下曲艺其中包括相声,我也希望那些爱听相声的人也能够逐步地爱听曲艺。
有的人爱听我的相声,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了,从全国说,就天津的一些观众,我们老乡亲爱听我的相声,不一定爱听京韵大鼓、单弦、时调、梅花(大鼓),不一定爱听。
我想引导他们呢,也听一听曲艺,我编《听曲艺》这个段子其中有这层意思。另一层意思呢,就是在丁文元受欢迎的基础上,人们喜欢这个人物,再把他放在《听曲艺》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包袱,这么一个主线,而且这个段子呢还能够把我所学到的一些个曲艺知识展示一下,也打破了我们马家从来不唱的旧观念。
我这就属于“不肖之子”了,从老爷子那说“马家不唱”,一直坚持不让我唱,但是我总觉得既然能学两句儿,为什么不让我过过这瘾呢?我就设计了这一个段子里头有单弦,谢派,谢芮芝谢派单弦;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也有阎秋霞的,白派,也算白派,但是阎秋霞味的京韵大鼓;好像是一些个老段子,《杂条》、《杂学唱》的意思,用丁文元贯穿这个段子,收到相当好的效果,电台也有录音,有时候也放,也出乎了一些同行业的意料。
同时呢这个段子呢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专利,你别人在台上再说丁文元,人家说了“这是跟马志明学的。”再有呢,我这里头虽然是水平不高吧,学了几句京韵、单弦的,比一般演员,比现有我们团里的演员要高一块,因为我没什有么爱好,我这人哪,除了爱听北京人艺的话剧,就是听京剧,其次就研究我这点相声、曲艺。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坐得住。比如说吧,这有支出去一句话。在农村,我父亲跟我母亲到市里来了,到市里看病。我弟弟上河工,挖河去。就我一个人在村子的最南头,我住上一个礼拜没见过一个人,晚上连电都没有,我不寂寞。
我自己拿一本字典,能在屋里呆一个星期,这是我的性格使然,天性。这也是多年处境不好磨炼出来的。反过来呢,要是太乱呢,上歌舞厅,我还受不了,我心跳,跟人打麻将牌,我急躁。跳舞、打麻将甚至于玩儿,我都不太爱。
甭管是庐山,是西双版纳,是名胜古迹……如果都去呢,我就去。让我自己想,去一趟……我没这想法。逛书店,我倒愿意去。我的爱好比较窄。所以在听节目上呢……在曲艺团我又不得志,总让我干活。人家都歇着,让我捡场。
捡场呀,就是每一场节目完了,我去服务,把桌子搬下来,摆几把椅子,后台打点水……我经常干这种活。给大伙熨衣服……所以,我这耳朵始终在台上。有很多段子,文革以后,有些老艺人,捯(读二声)不起来了,比如说梅花调的唱十个字,《十字西厢》:“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莺莺红娘,三请张生来赴会,四顾无人跳花墙……”这个词,捯来捯去插(读二声)住了,找谁呀,“找志明……”我又不是唱梅花调的!
她准知道我会!拿过来,我就告诉她怎么来,怎么去。
我是这种性格,下意识地,搜罗、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唱单弦、唱京韵,我能够上弦。大部分演员,即使他是“柳”为主的演员,在台上唱,如果把三弦、四胡、鼓放那,让他正式唱……我相信他唱不完就乱了。
因为一上弦,“板槽”一定要准,只要没“板”,乐队没法给你弹,没法给你拉。我的“板”就准,因为我学东西比较认真,比较刻苦。我把掌握一段京韵大鼓词做为一种享受。我能把京韵的一些段子改成快板,这是题外话了。
我把这些优势,再把“丁文元”在观众当中的“声望”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段《听曲艺》在那一届的“津门曲荟”上露了把脸……
刚才我说我们老爷子,不主张唱,“咱马家不唱……”因为他没有天赋条件,我们马家恐怕辈辈都是这发闷的嗓子,不太亮堂。唱呢,不是咱的优势,咱的优势是说,是刻画人物,刻画小市民的内心世界,惟妙惟肖,那是有口皆碑的吧。
但是,不等于老爷子不唱,不等于他不会唱,如果说比唱,从他内心说,他认为比谁都不逊色。就因为咱没嗓子,这不是咱的优势,他就躲着这个了,他不唱了。比如说他唱《改行》当中这一段,学李多奎,李多奎卖菜,一般的使《改行》的都是那几句:“香菜、芹菜、辣芹椒,茄子、黄瓜、嫩蒜苗……”都是那个。
老爷子这个呢,他会的这个很有技巧,他用《四郎探母》“见母”那段快板,套着那个,出来这个卖菜的词。先唱一遍《四郎探母》,再唱一遍“卖菜”,然后一句“四郎探母”,一句“卖菜”……对仗着唱,很吃功夫。有的人学呀,唱不下来就乱了。偶尔有老观众、老朋友邀请之下……他在电台也录过这个。在某个一次演出时,电台录下来了。
我觉得,马家的嗓子是不好。但是,马家也有优势,我们马家的“五音”全,凡是低音,有韵味的,不单不次于嗓子好的,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他。比如说,让我唱刘宝全,我绝对不行,我小时候学也许行,只要是上台,我够不上,不够那调门。我如果学阎秋霞,学白云鹏,学荣剑尘,学谢芮芝,还是比别人有好的一面。有些曲艺演出邀请我专门唱大鼓、单弦,这就是证明。
那年“津门曲荟”搞《学曲艺》这个段子,达到了我原来预期的效果。有些相声爱好者找到我,烦我给他录点曲艺段子,我在推动曲艺的发展工作上,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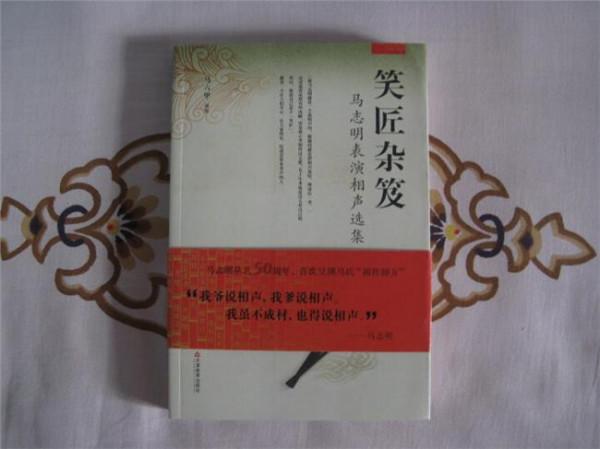





















![>李文华拜师马三立:儿子马志明代父收徒 李文华儿子是谁[第2页]](https://pic.bilezu.com/upload/d/b5/db52dd9f1f9fcd9bf7a8b8027734a1d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