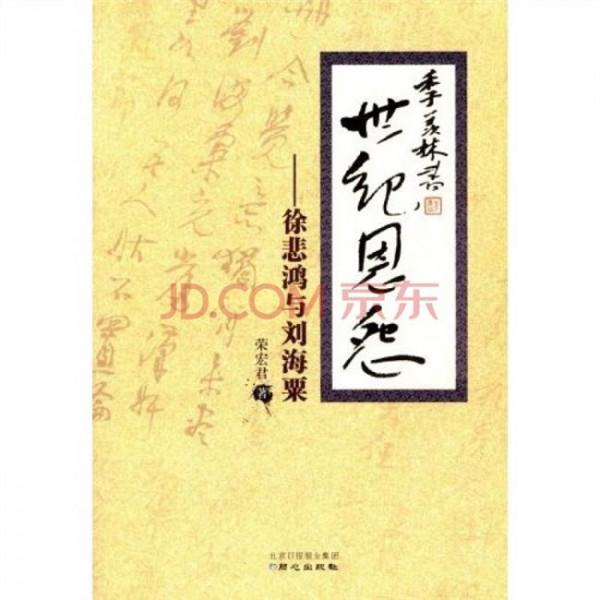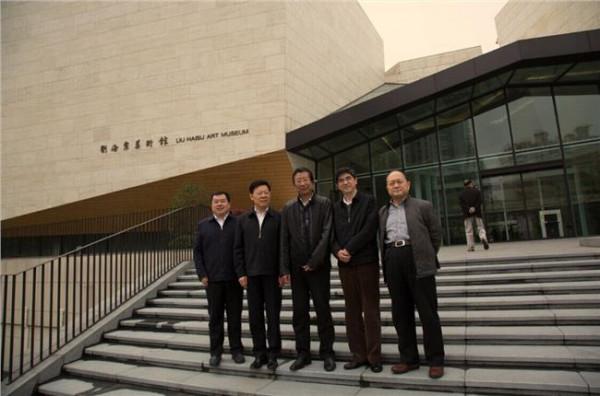刘海粟什么 我们从刘海粟那里学到什么
刘海粟先生在民国时候被骂为“艺术叛徒”,他之所以获得这个称号,因为他把女人体艺术送进了学堂,这在白话文刚兴起、小脚缠布刚解开之时,还是大胆的。不过这个叛徒不是最早使用女人裸体模特的那位,倒是李叔同先用了。在这样一个整体思想闭塞的混沌时代、一群英雄争战的历史环境里,敢于抛出女人体艺术,说明刘海粟确实够有底气的。

刘海粟雕塑头像
我们今天再看回刘海粟先生的画,评价俩字:狂野。这位活过90岁的“沧海一粟”、大耋巨匠,创作量确实惊人。从油画风景、人物,国画山水、花鸟、人物,还有那“康有为体”的书法字,林林总总、会然大观,让人止不住一叹。但无论他画什么、怎么画,总脱不开一个特色:野兽派。
鲁迅全集里对刘海粟很不屑 : “‘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 知道是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 ’,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次也许要‘载誉归来’。”
也许鲁迅先生对当时的国画抱有偏见,认为一定是“贫乏的”,不足以评价刘海粟的真实面目,那我最近在中国美术馆看过“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品过他的画,我认为:他的画,尤其是国画,有种“过犹不及”之感。
刘海粟《满庭芳(泼墨黄山)》,68cm×137cm,国画,1980年,中国美术馆藏
仔细看过刘海粟的油画作品,发现他掺杂了大量西方现代画派:如印象派、野兽派的风格,用笔粗疏狠重,可能是书法沿习“康体”的路子,颜色生涩,基本不调色(直接用色管里的颜料作画)。当然,这种欧洲现代派油画的痕迹,在二十世纪初很多海归艺术家的作品上都有明显的标识,刘海粟也不例外。
只是看来看去,一直到晚年的作品,始终惟有野兽派,再加点印象派的光影。每一幅画作,初看很跳脱、也浑厚,再细品,就深入不下去了,缺乏回味的细节。
1982年创作的油画《曙光顶看始信峰》,就是用一种率性的不拘一格,去肆意画一种物态的不规则,来追求“不讲形似”的理念。这比起1954年创作的简色般的《黄山云海》,成熟多了,似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但也就是圆润多于狠辣,少了锋芒毕露罢了。
刘海粟《黄山云海》,62cm×75cm,油画,1954年,中国美术馆藏
刘海粟曾在《拭目待天葩》一文中说:“既要有历史眼光,纵览上下二千年的画论画迹,又要有囊括中外的世界眼光,凡属健康向上可以吸收的东西,都要拿过来,经过冶炼升华,作我们民族艺术的血肉,对古人和外国人都要不亢不卑,冷静客观,要厚积薄发,游刃有馀,随心所欲不逾矩,达到自由和必然统一的境界。”表明他对中西艺术的兼容思想。
再看他的国画、书法,感觉书法比国画好,书法确实苍劲刚健,一种“屋漏痕、锥画沙”的拙朴风浮现出来,还是很正气的。那国画作品,跟油画创作一样,都只是大形俱在,却逸笔草草,独缺雅趣。1954年的《万山积雪图》,那层层墨染的山头和红叶绿树勾勒感觉还算细致,染中带写,算是学习传统山水中比较成功的一例,大效果不错,尚欠动人处。
有人说他的山水画为“有笔法而无皴法,传统法则均为时代的气韵所替代”(陈履生(微博)语),此言甚是。只是这“时代的气韵”,我觉得,这纯属刘海粟个人的气韵。
刘海粟《毕竟西郊八月中》,书法,100cm×50cm,1979年,中国美术馆藏
看他晚年的泼彩山水画,有种“大刷漆”的感觉,不了解他这是泼出来的,还是刷子刷成的,总之跟画面的主景融合不到一起,生硬感、违和感很强,产生一种视觉上的不适感。开始以为大师是用早期的油彩作画习惯来创作。再看张大千的泼彩,就舒服很多,其泼彩形成的云雾气都能整体和主景交融相合,色彩生发出氤氲淋漓的变化感,既有拨开云雾的大气,又有层层递进的舒畅。
刘海粟说过“张大千是泼我是浇,浇得惊风雨泣鬼神”,我感觉,真的是“惊风雨泣鬼神”,还十分“惊人”。有一幅1988年创作的《奇峰白云》感觉还算到位,“大刷漆”不突兀、不刺眼,渲染效果细腻,远近景的层次分明,画山用焦墨皴擦,整体干净、利索。
刘海粟《奇峰白云》,93.5cm×172cm,国画,1988年,香港私人藏
把刘海粟的画跟关良作比较,两者都有野兽派的痕迹,跳脱、不求形似。但关良在画坛的名声不响,如同一滴水投进大海般无声无息,与刘海粟的“大师”地位没得比;其次关良主攻人物,画幅尺寸小,鲜有那些高头大卷、磅礴巨幅;油画基本用平涂,不怎么探索西画的立体、光影和空间。
当然,关良埋首于民间美术,把民间绘画的特色融入到他的油画和中国画创作中,这是他一大艺术成就。我们看关良的画,它很拙稚、真诚,没有刘海粟画中的“火气”(浮躁气),更重要的是,他潜心研究绘画艺术,综合了多方面的艺术元素:譬如音乐、戏剧等等,开启了一条中国现代水墨之路。
刘海粟《黄山光明顶》,105cm×137cm,国画,1982年,香港私人藏
反观刘海粟,过去和现在对他的赞誉抬的太高,他的艺术创造性在哪里:泼彩?或许刘海粟也走“中西融合”的路子,尊崇西方的梵高、塞尚和中国的八大、石涛,尝试结合中国传统的野逸画风和西方新进艺术思潮打造他自己的“民族气派”;然而,无论怎么用何种手段去挥舞,都脱离不开他早年书法用笔的套路,所涉猎的“中西融合”路,是在“野狐禅”的基础上加入一些西画的光影、原色的表现力,和中国画的渲染皴擦,同时也暴露出他致命的先天不足:缺乏科班的基础训练。
他的中国画“泼彩”,更像用油画里的厚涂法,把原色往上砌,也体现出厚重与色彩的丰富,也有物态的质感,可惜是求量不求质,对艺术探索肤浅,不断在重复他早年的学画路向。他有天分,性情也真我,可惜把艺术当成他自我标榜的工具。
刘海粟油画《外滩风景》,97cm×163cm,1964年,油画,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藏
刘海粟自己这么说的:“艺术是表现,不是涂脂抹粉,这点是我个人始终不能改变的主张。 ‘表现 ’两个字,是自我的,不是纯客观的……所以表现必得经过灵魂的酝酿,智力的综合,表现出来,成功一种新境界,这才是表现。”(《艺术的革命观》)至于怎么理解这段话,那就见仁见智了。也许,他一生的艺术表现,根脚都落在他的“自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