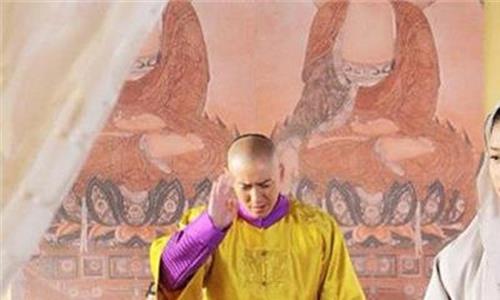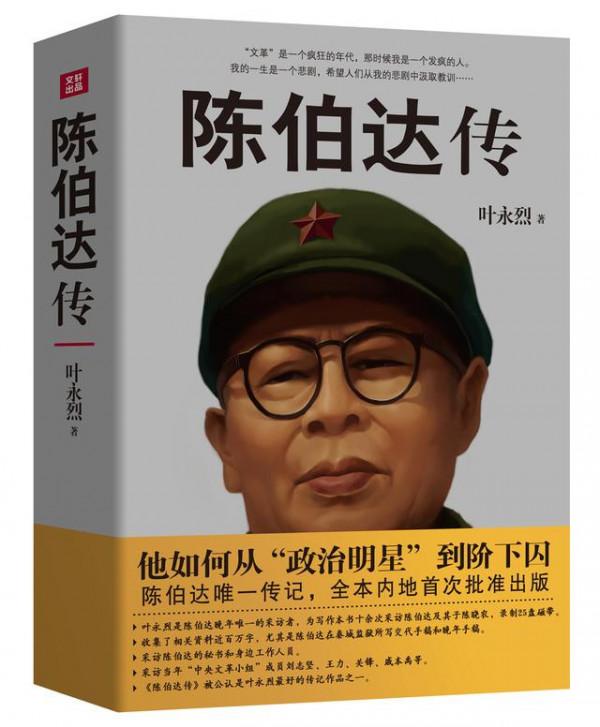陈三立的诗 陈三立的除夕诗
晚清人做的除夕诗,多是“例行公事”,大同小异,其实很少能翻出新意的,因为节日诗,无非也就是那点意思,难以出奇制胜。这是可以预料的。不过陈三立在1917年除夕做的几首诗,倒是可以一谈的。
自上至下依次为周大烈楷书仍珠先生近诗、陈三立1928年作行书及陈三立所书对联。

客:今天是除夕,可否谈谈晚清人的除夕诗?我知道除夕诗起源很早,最早的一首,是南朝梁徐君蒨的《共内人夜坐守岁》。历代的除夕诗多极了,谈的人也不少,不如谈谈晚清遗老的除夕诗。
主:你的建议很有意思,不过晚清人做的除夕诗,也多是“例行公事”,大同小异,其实很少能翻出新意的,因为节日诗,无非也就是那点意思,难以出奇制胜。这是可以预料的。

客:这倒也是,因为横竖不过这个节,大家都在纷纷做诗,人同此心,意思被做尽,也不是奇怪的事。我读南宋蒲积中编的《古今岁时杂咏》,其中共收节日诗两千多首,除夕诗有一百多首,读来读去,也就那些意思。不过,你有没有好玩的与除夕诗有关的事说说,这个也是可以的。

主:这么说,我倒想起陈三立在民六那一年(1917)除夕做的几首诗,那几首诗,我读了很被它打动,在别的场合也与人讲过,这倒是可以一谈的。
客:那太好了,我很想听听这个,散原的诗,我当然是感兴趣的。《围城》里的那个董斜川,不是说过“近代诗人以陈散原为第一,这五六百年里数他最高”的话么?你且说说他的除夕诗是怎么写的?

主:散原的这个诗,题目叫做《除夕得周印昆由张家口税关寄诗和酬四绝》,总共是四首,诗为:
荒城角起烛初烧,斗柄斜檐对一瓢。忽仰帛书传塞雁,声声听入可怜宵。
一身万里别三年,想得呵毫雪满天。细字作行杂呜咽,惜花故事出灯前。
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招隐恐无干净土,得钱烦买画中山。
边徼沙黄车驮移,指挥云物照刀锥。遥怜旧俗人扶醉,念乱伤离独捻髭。
第二首的结句,有一个自注:“君居湘,逢戊戌政变,有《惜花词》。”
客:这个周印昆是什么人?
主:周印昆就是周大烈,字印昆,是湖南湘潭县辰山桂花堂(今黄荆坪乡辰山村)人。他生于同治元年(1862)十月廿三日,生肖属犬,比散原晚生九岁,散原生于咸丰三年(1853),属牛;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二日因肺炎病逝,早于散原三年下世。
著有《夕红楼诗集》《桂堂清故宫诗》,编有《民法总则》等。他是散原长子陈师曾(衡恪)小时的老师,也是陈寅恪先生的老师。这是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提过的。他在陈家教书的时间,是在1895年。1905年,他四十四岁时,尚设法去日本留学,肄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期间,去谒见过孙中山,共商国是。辛亥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晚年住在北京。
客:说起周大烈,我是知道的,记得他是许地山的岳父,据说他生了七八个女儿,没有儿子。老先生为此很不高兴,订了一条规矩,说谁娶他的女儿,生的第一个儿子,必须随他姓周,否则就不同意婚事。这人实在是很好玩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主:正是他。他生了七个女儿,长女名懋先,嫁了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湖南湘乡人左光策;四女名盖季,毕业于湘潭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嫁了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山西人何厚伟;五女兆元,毕业于上海艺术专门学校,嫁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学士、上海宝山人朱有骞;七女铭洗,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特立萨大学的文学士。
次女仲恒、三女叔鲍,均早亡。嫁给许地山的是六女俟松,生于1901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士;晚年住在南京。据说俟松与许地山恋爱时,周大烈见了许地山,认为:“从相貌上看,许君属短命之人。”所以很反对这门婚事。
客:哦,原来是这样的。今天知道许地山的人很多,知道周老先生的人却寥寥无几了。
主:其实,不仅他的女婿是大名人,他的另外一位亲戚,说起来,更是声名震耀一世,那就是他的祖姑父左宗棠。他的祖姑名周诒端,是他的曾祖母王慈云的长女,能诗,有《饰性斋遗稿》。一次,他的祖父周诒昱带左宗棠来家,被王慈云看见了,特别欣赏,就把女儿许配他了。王慈云也能诗,有《慈云阁诗钞》,是左宗棠编刻的。
客:这么说来,周大烈也是大有来历的人了。那么,他寄散原的诗,又是怎样写的呢?
主:周大烈的诗,是一首绝句,题目很长,为《陈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屡徵不起,近惟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因以一绝奉寄》,诗云:“承平门族多残破,并数陶谭记二三。老病迦陵诗见骨,一身枯瘦卧江南。”次句后自注:“清末伯严与陶葆廉、谭嗣同同称三公子。”就是这四句诗,引得散原一口气做了十六句,大大地来劲了。
客:这首诗有什么特别处,让散原这样激动?
主:可说的可以有两点。首先,是周与散原很交好,比较投合。散原有篇文章,数过他在湖南时的挚友,共四位,里面就有周。友朋之间,如果关系好的,说话也就易于投机,做起诗来,也就易于起劲。陈衍有一个说法,深为人所首肯,他认为:友朋之间,为有些人作的诗便佳,为另一些人则不尽佳。
如郑孝胥为顾云作的诗,就特别佳;陈宝琛为谢章铤、张佩纶作的,也每佳于他作。这就好比《南史》中谢灵运说的“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周大烈是卓荦之士,怀抱很高,与散原的为人、气味比较接近。所以他寄的诗,自然易起散原的“共鸣”。
客:是、是。那么,第二点又怎么说?
主:其次,是周的这首诗,文字固然不多,但却字字搔着了散原的痒处。唐人杜牧不是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如倩麻姑痒处搔”。搔着了痒处,读了才能过瘾,才会来劲,否则不痛不痒,是没什么意思的。散原的和诗,有句说“声声听入可怜宵”,换成我们的大白话,便是“你老周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说进了我心坎”。
当然,作诗与说话不同,作诗必须蕴藉、必须典雅,言在此而意在彼,兴发感动,不能过于直白,那样也太浅、太不好看了。所以,收到了周大烈的诗,这里就写作了“忽仰帛书传塞雁”;周的话说进心坎,就写作了“声声听入可怜宵”。这才是合乎诗艺的。
客:你这两点说得太浮泛了,能否说具体些,如究竟是哪些地方,“拨动了散老的心弦”?因为周大烈的诗,在我看来,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总之我读了并不激动。
主:你不激动,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通心粉”:“通心”了,一两句就够了;不“通心”,说几箩筐也没用。从周诗来看,首先它的题目,就足以把散老的魂魄勾起来了。我们知道,散原的一生,是截然以戊戌政变为分水岭的,在戊戌之前,他的父亲任湖南巡抚,与黄遵宪、江标等先觉之士,共办新政,他从旁多所赞画;政变作,他们父子俱被革职,“永不叙用”。
1900年冬,他父亲乃被慈禧赐死,并取其喉骨,命人奏报。散原作了一篇很长的《先府君行状》,而于父亲之死,却只能说是“忽以微疾卒”。
毫无疑问,“戊戌政变”之于散原,是其一生的伤痛所在,可谓“刻骨铭心”。在除夕的晚上,在“急景凋年”的光景里,你单提“戊戌政变”四个字,也就够刺激他的了,更何况,还要提及“屡徵不起,杜门作诗”,“中年皮肉脱落几尽”?什么叫做“皮肉脱落几尽”?这自然不是谑散老的瘦,——你看过散老的照片,确乎是枯瘦的——而是用了一个典故,来称赞散老的精神,这就是山谷《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八云:“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
”不过在这里,为了与后边“一身枯瘦”呼应,周诗把山谷的“皮毛”,易作了“皮肉”,这在散原,也是一见即知的。
同光体诗人的诗,从精神上说,大抵都受了山谷的影响,散原也不例外。就此二句而言,山谷是本于药山答马祖语:“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又《涅槃经》云:“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惟真实在。
”这是任渊注指出过的。是的,人生所最可贵的,在于自性的真实,一切身外是非得失,不过皮毛而已。山谷另有名句云:“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人间世的是非,究其实而言,皆为外在的、虚妄的,于我们一己的精神,并无足重轻,如是则皮毛脱落、返于“真实”,就是诗人所当追求的境界了。散原的为人,是真足当得起这两句的。
1898年即戊戌政变后,直至1917年,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是散原始终未再出,他的怀抱和志节如何,是用不着多说的。有人称散原:“先生知事不可为,自是纵情山水,殚心著述,绝口不言时事。
”(陶在东《关于散原老人》)可见散原的为人行事,是当世所共知的。而在政变之时,有人竟为联嘲笑散原父子,以与徐氏父子(徐致靖、徐仁铸)为对仗:“徐徐云尔,陈陈相因”;“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徐一士《一士类稿》)。
所谓的“北看成南”,在散原来说,正是身所经历的事。不过,在散原的心中,其伤痛必是永不能忘的。所以周大烈的诗里一提,他也就大受刺戟力了,他的诗不是说:“细字作行杂呜咽,惜花故事出灯前。”其实,“杂呜咽”的不是周大烈,是他老先生本人;他自注里说的《惜花词》,周诗也没有提,而是他的脑海里翻腾起的往事的影像!
周大烈的诗,有六个字最好,我认为写出了散原,那就是“诗见骨”、“卧江南”。“诗见骨”,是呼应“皮肉脱落尽”的,散原的为人,是可谓“真实在”的,其为诗,则也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真而“见骨”了;而“卧江南”,更把散原的姿态,描摹得立于纸上。
散原不造显贵之门,友朋之间,也多为君子之交,通问较疏,不那么殷勤往来。近人《睇向斋逞肊谈》中说他:“岁逾八十,高卧匡庐,虽尺笺之微,罕与人通殷勤,澹旷殊似魏晋间人。
”有一次,友人易顺鼎六十寿,特请他为作寿诗,他答易书札云:“仆于海内故旧,例不通问,若一破格,则于我疏懒之性习,不能成就。”“疏懒之性习”,“似魏晋间人”,与“卧江南”,是完全搭调的。至于“老病迦陵”的“迦陵”,是陈维崧的号,他与散原同姓,又同是名父之子,所以用之指代散原。这是那时人的惯常写法,不必多说。
客: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原来散老被周大烈捧得好,看来捧人也不能乱捧,要捧必须知心。《象山语录》里说:“文王不可乱赞,须是识得文王,方可称赞。”其道理是一样的。周大烈对于散原的诗,是不是也是极推重的?
主:是的,周大烈对于散原的诗,作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精准的评价。其语见于散原长子衡恪为其岳父范当世之子范罕、也就是其妻兄的诗集《蜗牛舍诗》做的序中,其语云:“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亦旧诗之殿。
”这两句话,没有大眼光是说不出的,在今天看来,这一评论的正确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其实,就是在1917年,散原写这四首绝句的几个月前,还发生了一次关于评价散原诗的笔仗,那是南社柳亚子与闻宥、朱鸳雏等人干的,不过,如柳亚子等此种蚍蜉撼树的小丑式攻击,散老是并不以介怀的。
附带一提,后来有一个号黄山樵子的人,与冒效鲁论诗,也诋散原为“豁鼻老牛”,冒为之气不平,写了几首诗,来为散原辩护。前面说过,散原生肖属牛,此诋固属诞妄,而就属相说事,却也有几分幽默,一笑了之可矣,实不必与之辩的。
客:你说散原的诗,是受了山谷影响,我记得他本人不承认,近人的笔记中,也记了他对门人胡翔冬说的:“我四十岁前,于山谷、后山诗,未尝有一日之雅;以我为西江派诗,岂不冤哉?”陈衍则以为其诗出薛浪语,又遭到钱锺书的驳斥,这些人都是诗学的大行家,而意见如此分歧,莫衷一是,我也摸不着头脑,也不想再为此纠结了。我现在只问你,这几首除夕诗里,有没有山谷的迹象?
主:你所说的,是追溯源出于谁的问题,事实上,从钟嵘的《诗品》起,此事就争论不休了。这事说来太麻烦,我们姑且不谈它。就说散原的这几首诗,其实也是用了山谷的,如第二首的“想得呵毫雪满天”,“想得”的意思,是“想见”,是山谷诗所喜用的一个词,如“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想得争棋飞鸟上,行人不见只听闻”,等等。
又第三首的“我长落拓四立壁,公亦蹉跎反抱关”,“反抱关”是用《汉书》的典,山谷也用过的,却不能就说他本于山谷,但“四立壁”三个字,则确乎是从山谷来的,“四立壁”的话,本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即所谓“家徒四壁立”,但将之变做“四立壁”,则是山谷《寄黄几复》的“持家但有四立壁”。
这也是前人称道的,是山谷“善于变动生新的手腕”(潘伯鹰说)。
客:“反抱关”,你说是用了《汉书》的典,我记得《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那个侯嬴,就是“夷门抱关者”,为什么不是用《史记》的?
主:“抱关”二字,《史记》前就已有,见于《孟子》;“反抱关”三字,见于《汉书·萧望之传》。这些都是前人说的“无一字无来历”,我们也不去追究它了。周大烈此时是在张家口监督税务,所以散原用“抱关”这个词,这是很雅化的写法,包括第四首的“指挥云物照刀锥”,也是如此。
“云物”指云气、景物,“刀锥”语出《左传》,指微末之利,所谓“商贾竞刀锥”(陈子昂诗);税务监督要与商人打交道,这于诗人而言,总不免是件俗事。
客:周大烈是何时去张家口的?另外,他的诗题里说的“伯严自戊戌政变后,久客金陵”,是否有些问题?我记得辛亥革命后,散原也是住过上海的。
主:是在1917年。周大烈先是在1916年迁居天津的,他的女儿有三人都就读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因天津涨大水,又挈家迁往北京。也是在这一年,值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派他去张家口任税务署监督。
赴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7月。他的《夕红楼诗集》中,有一首《赴张家口车上作》云:“今来七月京张路,才过沙城草又黄。”可以为证。不过他的家人,必定是留在北京的,他是只身赴任的,并且大概也常回家、在北京张家口之间老是跑的。
他去张家口,是从德胜门出,经过居庸关、榆林驿、怀来、宣化,中间不过四百里左右的路,坐车的时间并不长。他另有一首诗,题目叫“由京回张家口留别姚重光”,是可以印证我的推测的。而散原诗说的“一身万里别三年”,其实不是写实的,而是一种烘染的写法。
张家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在当时的张北县南,属口北道,是蒙古同内地买卖、货物进出口的总关门。每天进口的骡子,算来也有几千匹。这里也与俄商交易,出口货以生牛羊皮毛及南方的茶叶为大宗。所以散原诗里说“边徼沙黄车驮移”。
至于散原的“久居金陵”,是从1900年4月始的,直至1911年9月,又因为避乱,而携家人移居上海,住在老靶子路,就是今天的武进路;1915年夏,才又从上海还居金陵青溪之旁的散原精舍。周大烈的话稍欠精确,但也不算大错,他与散原之间,通问未必很多,但肯定是关注他的。
客:好的,我想散原的除夕诗,写了什么,已经是很清楚了。我另想请教的,尚有一事,就是你也每年除夕作诗,自觉哪首是得意之作?也顺便说说吧。
主:我那都是乱写的,是标准的“半瓶醋”,比我乱谈还要坏,不过你既提起,我也不能藏拙。我在癸巳岁除,作了首七律寄友人贺岁,其中后四句,比较的有些气象:“未妨冬雾蛇鳞没,却喜春风马耳吹。明日腾骧先发轫,与君同看踏云姿。”这里不妨摘出,为春节的吉祥语,同时,也算是效颦山谷,来个“打猛诨出”收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