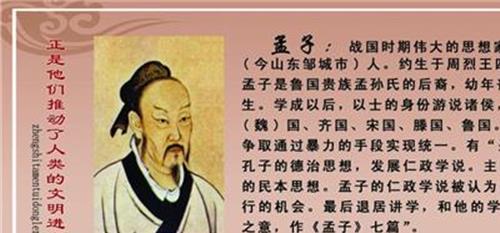刘邦是汉元帝什么关系 汉元帝毁宗庙 背后有什么政治考量和角力?
汉元帝实行宗庙毁庙礼制,依据其所毁庙场所的不同,主要分为毁弃郡国皇家宗庙,和依据儒家经典有关记载,实行皇家宗庙“毁庙”礼制。
西汉郡国庙,是指刘邦称帝后,在西汉帝国中央直辖郡及封建的王国中,为刘氏皇家修建的用于祭祀刘氏祖先的礼制性建筑——宗庙。

郡国皇家宗庙的修建始于汉高帝十年八月,令诸侯王在各国都城为刘邦已经去世的父亲太上皇修建宗庙。其后,高帝刘邦高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除立于京师外,先后皆立于郡、国。对于高帝、孝文庙立于郡、国事,《史记》、《汉书》的记载却互有歧异。对诸文献记载歧异的详细考证,可参看拙著《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第83-95页)

西汉初期为何实行郡国庙之制?据元帝永光四年罢黜郡国庙而颁布的诏书,联系西汉初期纷繁复杂之局势,当时在郡、国为高、文二帝立庙,或许主要与维护皇帝权威,巩固刘姓皇朝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紧密相关。郡、国庙的设置无疑成为强化刘氏宗族血缘关系、笼络异姓诸侯王感情,从而有效协调郡、国并行行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遏止离心割据思想滋蔓,以达到强化中央皇帝集权体制目的重要手段。

随着几乎清一色的刘氏同姓宗王布满畿甸格局的形成,汉“祖”、“宗”郡、国庙的设置就被赋予更为浓郁的宗法伦理意义,从而对诸侯王构成具体、强有力的精神威慑、约束作用。
或许为摆脱这种精神力量的约束,吴、楚“七国之乱”时,胶西王刘卬等竟焚烧了设置于胶西等地的汉“祖”、“宗”庙,其约束力于此可见一斑。

汉元帝时,王国对中央的威胁已经微乎其微。宣帝为武帝设立郡国庙,其范围仅限于武帝生前游历过的郡国。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出于纪念意义和制度的习惯性延续,而不具有汉初那种明显的政治目的。
元帝时期推行宗庙礼制改革,与其时政治、经济、思想学术与社会和汉元帝本人皆有密切的关系。汉高帝至昭、宣、元帝时期,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基本确立是改制得以实施的必要前提。西汉初、中期,儒生对礼学文献的整理、诠释,为改制的推行提供了充实的理论、文献依据。
昭、宣、元三朝政治矛盾与社会危机的激化是推行改制的直接动因。西汉祖先神灵祭祀的财政支出可谓巨额耗费。以郡、国庙数167所,京庙、陵庙9所计算,合计一年祭祀次数就应为4400次(167×25 9×25)。
尽管目前缺乏足够数据,难以比较准确估算上述祭祀所需费用,但其数目必然相当浩大。在国家财富贫弱至捉襟见肘时,要继续维持这样的排场、规模,可能确实已难以为继。大力拓展财源,紧缩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为统治阶层不得不采取的根本对策。减撤耗费弥繁的郡、国庙开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紧缩财政支出逐步推行的基本措施之一。
由于西汉初期制定、实行的皇帝宗庙制度与儒家典籍有关记载极不相符,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中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固守儒家学说的儒者往往以不符古礼为辞,对其大加讥斥。盲目崇信儒学的汉元帝,或许禁不住某些儒生真心信仰并时刻鼓噪的只要恢复周礼,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的说辞诱惑,在客观现实的逼迫下,凭借极大勇气、魄力,断然变更祖宗旧制。
他起用出身儒学世家的韦玄成为丞相,在其佐助下,依据儒家权威典籍有关记载,发动皇帝宗庙礼制化改革。
此次宗庙礼制化改革共包括两方面内容:废除西汉高帝时起,惠、景、宣三朝在郡、国陆续为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等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皇帝设置的宗庙;依据古礼,确立宗庙毁庙制度。
元帝时,国库空虚,维持如此庞大的郡国庙祭祀已经成为汉王朝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况且,依据儒家典籍记载,宗族庶子无权祭祀宗子。上述三帝郡、国庙长期由诸侯王或者地方官吏主持祭祀,有悖于宗法制度。故儒学士大夫阶层对废除高、文、武三帝郡、国庙,并无异议,毁弃郡国皇家宗庙的改革得以在永光四年顺利推行。
次年,元帝诏令议皇帝宗庙迭毁礼制。与罢弃郡国庙顺利推行相比,皇帝宗庙迭毁制度的确立、实行却因受参与政策讨论、制定者援引经典的不同,以及现实政治因素影响而充满了坎坷、波折。
按照元帝本意,天子宗庙应该是立亲庙四,有“祖”、“宗”庙号的先帝宗庙万世不毁,由于当时有“祖”、“宗”庙号的仅有高帝高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如果按照元帝设想立庙,则恰与礼书中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之制相符。
但此意招致以韦玄成为首的部分儒学士大夫的反对。韦玄成等人虽然与当时大多数儒生一样,遵循周代天子七庙由在位天子始祖庙、文、武庙以及其高祖父以下四亲庙组成。但他们或许依据先秦时期逐渐严密的宗法丧服制度,以及血缘关系限制于高祖父以下观念,坚持四亲庙说,主张实行天子五庙制度。
但这一建议遭到了部分臣僚的反对。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孝文皇帝生前功德卓著,其宗庙宜为太宗庙。不应毁。廷尉忠以为孝武皇帝庙宜为世宗庙,也不应毁。
由于韦玄成等人主张将未曾即皇帝位的皇考庙(刘据之子,宣帝生父刘进。宣帝即位后,追谥刘进曰皇考)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中,导致武帝末年爆发的“巫蛊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昭帝、宣帝两朝诸多敏感的政治禁忌,再度跃入人们视野之中,重新被某些政治感觉灵敏者捕捉。
将皇考庙列入皇帝宗庙系统,确实不是名正言顺的举措。即便在事隔将近五十年之久后,意图变更先帝定谳,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阻力。这或许是韦玄成等人主张致命缺陷之所在。不出意料,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果然据此进行反驳。
韦玄成等人按照宗法制度,以武帝、昭帝、皇考、宣帝四庙作为元帝“四亲庙”,与高庙合而为“五庙”。从某种意义上推测,韦玄成等人内心或许认为此事历年已久,试图借此实现宣帝无法言传的未竟遗愿。由此不难理解,韦玄成奏议中景帝亲尽、皇考庙亲未尽之语真实意旨所在。
不过,尹更始等人的驳难也是冠冕堂皇,难以轻视。由于皇帝宗庙系统只能由曾经即位为帝的祖先宗庙组成,刘进没有做过皇帝,将其与昭帝庙并列于昭穆序列,又违背以父、子为昭穆的宗法制度。
屏弃文帝庙,确实又有违以往褒崇文帝的用意。但即便将皇考庙排除于皇帝庙制系统之外,“四亲庙”也只能至景帝庙而止。如果加上文帝庙,那么,宗庙庙数将突破“五庙”之制,这与韦玄成等人信奉的五庙说,又成凿枘之势。
由于各种论争涉及礼制、宗法以及当时政治诸多因素,已经无法由臣下议决,只能留待皇帝作出宸断。对于恪守传统礼制而又优柔寡断的元帝来说,此次宗庙礼议反映出来的“君统”与“宗统”的矛盾、情与礼的冲突,迫使他不得不万分谨慎,对各种方案进行反复权衡、思量。
以至从三种意见上呈至元帝对此问题加以裁断,其间间隔竟长达一年之久。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元帝下诏,阐述自己的态度。元帝力图在上述难以调解的激烈论争中扮演公正、中庸和事佬角色心态。
他既打算遵循韦玄成诸人主张的五庙之制,又试图折中韦玄成、许嘉、尹更始三派主张。元帝意图采纳尹更始等人的主张,以“亲尽”为由将祖父刘进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但这样为迎合现实政治之需要而蔑弃祖先的做法,既与宗法制度不符,也有违于人的基本性情。
元帝可能由于受五庙之制影响较深,在采纳许嘉等人的建议,将文帝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后,又不得不将依“君统”为其高祖的景帝庙列入“亲尽”范围,以使宗庙庙数合乎五庙之制。不难看出,元帝为消弭争议而折中诸说提出的新方案,更与人情、礼制不合。
为弥缝元帝诏书中存在的上述诸多纰漏,韦玄成既不放弃初衷,同时又适当折中许、尹之说,重新上奏。从策略角度而言,韦玄成此奏可谓是“偷梁换柱”,或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既坚持皇帝五庙之制,以及将皇考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的初衷。又适当灵活变通,将文帝太宗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与高庙一并作为世世不毁之庙。
由上述分析可知,此时皇帝宗庙有7所,即高、文、景、武、昭、皇考、宣诸庙。韦玄成此次实施策略高明而不着痕迹之处在于,他出人意料地主张保留景帝庙,这或许恰恰是理解上述七庙因分属“君统”、“宗统”两个不同统系,而实际为六庙之制的关键所在。
依据韦玄成第二次奏议确立实行的七庙之制,由于分属“君统”、“宗统”两个不同的系统,所谓“七庙”,实则“六庙”。“君统”系统“六庙”:高帝庙、文帝庙、景帝庙、武帝庙、昭帝庙、宣帝庙;“宗统”系统“六庙”:高帝庙、文帝庙、武帝庙、昭帝庙、皇考庙、宣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