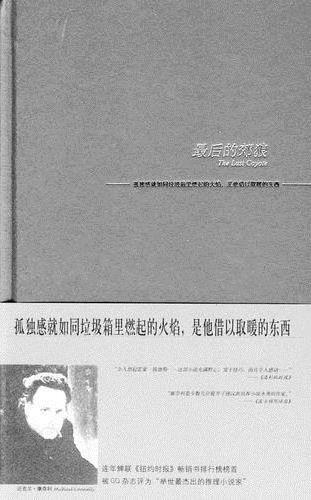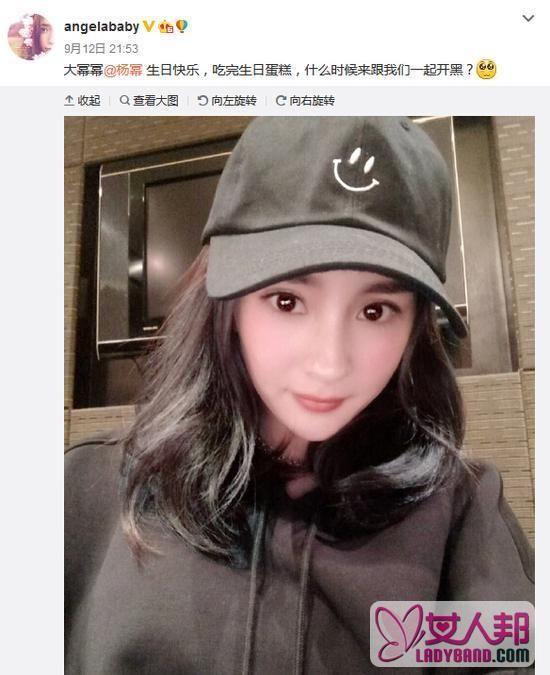科学网彭庆生、王水照、齐裕焜、胡友鸣笔下的吴小如先生
小如师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淹贯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文史并重,兼工行草楷书,笔意遒劲秀逸。先生治学,擅长由训诂而通辞章,重考据以明义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洵为乾嘉学派之鲁殿灵光,旷世难求之通才。
小如师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特立独行,从不俯仰取容,然极重情谊。对师长,感恩图报;对朋友,肝胆相照;对门生后进,眷顾奖掖,不遗馀力。凡此种种,有口皆碑。
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余忝为吴门弟子,受业五十馀年,虽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难窥夫子之墙;但先生的教诲和奖掖,恩深似海,没齿难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大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云萃,而且,几乎所有的名师都开基础课。1956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时,尚未满十八岁,实在不懂事,由着性子胡来,对系里给我们安排的课程,有兴趣的就认真听,使劲记;没兴趣的就逃,或坐在后排看自己想看的书。后来工作了,自己也教书了,才明白当初中文系安排的各种课程,没有一门是无用的。这才硬着头皮,自己补课,然而,毕竟已事倍功半了。
在大学本科的五年中,我学得最认真的只有三门课:一是游国恩、萧雷南、林庚、冯钟芸、二吴(组缃师与小如师)、季镇淮、王瑶、章廷谦等多位名师分段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含专题讲座),二是杨伯峻先生讲授的古代汉语,三是小如师新开的工具书使用法。这样算起来,小如师既给我们讲授了文学史中的元明清戏曲,又独自开了一门新课,还开过几次京剧讲座,应该是为我们授课最多的名师之一了。
在众多的名师中,小如师的职称最低,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时,他始终是个讲师。但那时北大的学生是有眼光的,不重头衔,只认学问。小如师从小就爱看戏,对京剧与昆曲极为娴熟,并与梨园名角过从甚密;最难能可贵的是:小如师还曾师从京剧名家,认真学戏,仅“真正从师问业一板一眼学到手的戏”,就多达六十多出,而其学戏的目的,“不为登台,不为出名,只是想通过实践来钻研戏理”(见《学戏与临帖》,后收入《心影萍踪》)。因此,先生讲起中国戏曲来,就绝不限于文字记载,而是富有自己看戏、唱戏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戏曲的历史与理论,均能穷源竟委,阐幽发微;又穿插一些先生耳闻目睹的梨园掌故,自然格外生动,深受学生欢迎。
1958年始,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大搞集体科研。在小如师的影响下,我们四班的同学集中兵力,撰写《中国戏曲史》。毕竟学殖浅薄,未能完成这个我们原本就力不胜任的大项目,但这件事却写进了学生档案。因此,大学毕业后,一些同学都因档案中有此记载,而被分配到有关戏曲的单位去工作了。如韩蔼丽分在北方昆曲院,后来还写过昆曲现代戏的剧本。张仁健分在山西文化局戏曲工作室,后来写过《近代晋剧旷世硕果——丁果仙艺术生涯评传》;张继顺分在四川文化局戏曲工作室,为著名清音表演艺术家刘时燕改编创作过不少清音脚本,二人因此而喜结连理。
我虽未从事戏曲工作,但在小如师的熏陶下,也成了半个戏迷。记得昆曲泰斗俞振飞先生在北大礼堂演出《太白醉写》时,我们班的同学早早地就去抢占了座位。后来,因韩蔼丽在北昆工作,我可以去看蹭戏,因而有幸欣赏过侯少奎先生的《单刀会》、李淑君的《昭君出塞》等名家名剧。侯先生的唱腔慷慨苍凉,念白铿锵顿挫,“(白)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这两句,迄今犹不时在我耳边萦绕。李淑的扮相美极了,使观众大饱眼富。可惜,有一次我在北昆食堂蹭饭时,韩蔼丽突然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悄声说道:“李淑君来了。”我抬头一看,大失所望。她并不十分漂亮。我一面后悔来蹭这顿饭,以致毁了我心目中美的偶像;一面又惊叹我国戏曲的化妆术,竟能将中人之姿妆扮成令人眩目的绝代佳人,委实神妙。
看京剧就不容易了,必须自己进城买票,却又没那么多时间,只好去等退票。我的运气好极了,竟接连五次都等到了退票:三次在长安戏院门外,买到退票,欣赏了马连良先生的《淮河营》,高盛麟的《挑滑车》,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赵燕侠联袂主演的《四进士》;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外等到退票,欣赏了谭富英的《大保国》;一次在护国寺人民剧院外等到退票,看了杨秋玲主演的《雏凤凌空》。至于杨秋玲主演、后拍成电影的《穆桂英挂帅》,我至少看了六遍。最难忘的是:1961年夏,袁良俊打听到梅兰芳先生即将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演出《穆桂英挂帅》,但很难买到票。他找我商量,一拍即合,决定两人接力,通宵排队。
我是夜猫子,不怕熬夜,就由我值夜班,从头天夜里排到天亮;良俊排早班,从早六点排到购票。我下午六点半就赶到了剧场,排了个第六号,心里便踏实了。那年头,社会风气好,没人加塞儿,更没有票贩子。而且,按惯例,先到的三个人中,总会有一位积极分子,事先在家里裁好了若干张小纸片,写上号码,排队时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发号。领到了号,就吃了定心丸,但不能远离剧场。因为,每隔一小时,那几个积极分子就点一次名,凡叫到号而人缺席者,那个号就作废,后头的就都递升一名。这样,大家都在剧场附近找地方休息,每隔一小时去应一次卯。凌晨六点,袁良俊依约而至,我便回校吃饭睡觉了。其时,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已登峰造极。我们虽然付出了一个通宵再加大半个上午的辛劳,但能看到梅先生精彩绝伦的表演,深感荣幸。那年八月八日,梅先生就驾鹤西归了。因此,五道口的那次表演,很可能就是梅先生的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了。人生一世,能看到一位空前绝后的京剧艺术大师的告别演出,幸如之何?
我絮絮叨叨地写了这么些琐事,无非是想说明:小如师授课半年,沾溉后生,其泽远矣!
1993年初,燕山出版社社长陈文良宴请一新师(姓陈,讳贻焮),由师兄陈铁民和我作陪。我们心里都清楚:宴无好宴,陈文良肯定“别有用心”。果然,开宴不久,他就请一新师出任《增订注释全唐诗》主编。一新师为人豪爽,两杯啤酒下肚,就站起身来,举杯说道:“如此,我就‘黄袍加身’了。”然后,又对铁民师兄和我说:“你们两位就当常务副主编吧!”铁民兄与我面面相觑,心中叫苦不迭。此前,陈文良已找过一新师,谈过这件事;一新师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早已说定:决不接受这个大项目。谁知一新师一激动,就欣然应允了。铁民兄和我深知这个大工程之艰巨,极不情愿;但老师既已应允,学生岂能拆台?只好勉为其难了。九六年此书交稿后,我便着手撰写《初唐诗歌系年考》,整整十年,创获甚微。到2007年,我已年近古稀,自知来日无多,决心以此生馀力,完成《陈子昂集校注》。要之,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沉浸在校勘、注释、考证之中,终日矻矻,却也乐在其中。在这些科研工作中,我受益最大的,是静希师传授的唐诗、伯峻师讲授的古代汉语和小如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正是我大学本科阶段学得最认真的三门课。
1986年始,《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陆续出版,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省却了许多獭祭之劳。然而,古籍浩如烟海,古人所用词语、典故及其涉及的名物、史实、职官、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等,实在是任何词典或字典都不可能囊括无遗的,这就必须查古书了。查书而不明门路,势必事倍功半,甚或徒劳无功。因此,我常常为自己能聆听过小如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而感到庆幸。随便举两个例证吧!
陈子昂《感遇》其十九云:“鬼神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又《大周受命颂》云:“臣闻大人升阶,神物绍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这里的两个“存”字都不大好解释。《汉语大字典》中“存”字有十三个义项,《汉语大词典》中“存”字有十四个义项,但都不适合。于是,我想起了小如师的教诲:训诂资料最丰富的,莫过于《经籍纂诂》。应该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该社1989年影印的《经籍纂诂》,既便宜(特价45元),又附有“四角号码索引”,一翻即得。果然,我从该书卷十三“十三元”查到:“存:至也。《荀子·议兵》‘所存者神’注。”再查原书,《荀子·议兵》云:“所存者神,所为者化。”杨倞注:“存,至也。言所至之处,畏之如神;凡所施为,民皆从化也。”释“存”为“至”,子昂诗文中的那几句便迎刃而解。《感遇》那两句的意思是:鬼神尚且干不了,人力又怎能办得到呢?《大周受命颂》那三句的意思是:臣闻圣人登基,祥瑞的神灵之物相继而来,绝非人力所能至也。
又如前几天我注到陈子昂的《赤雀章》,其中有一句:“在昔甲子,降祚于昌。”既是祥瑞,我便先查《宋书·符瑞志》,果然有“赤雀者,周文王时衔丹书来至”,周文王姓姬名昌,这算是对上了,然未言“甲子”。周代的甲子日,最著名的自是武王甲子日伐纣。一查《史记·周本纪》,果然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但这天没有“赤雀”,而在此前两年的盟津观兵时,“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我以为是陈子昂记混了,把三件不同的事捏在一起了。其时夜已深,人已倦,只好睡觉了。第二天上午起来一看,不对头呀!陈子昂再糊涂,也不会把父子二人混为一谈,何况,“赤乌”毕竟还不是“赤雀”。此时,我又想起了小如师传授的“秘方”:凡经书正史中查不到的典故,便查类书。我从《北堂书钞》查起,再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终于在《太平御览》卷八四查到:“《尚书帝命验》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酆,止昌户。拜稽首。’”并从《御览》得知:此典最早见于《墨子》。再查哈佛燕京学社编印的《墨子引得》,知其出自《墨子·非攻下》。引了《墨子》与纬书,这条注就比较可信了。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每当我解决一个校释考证中的难题时,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念叨:小如师,谢谢您!
1961年秋,我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当研究生,拜入静希师门下,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长达四年之久。后来工作了,但仍常回燕园62号,一则问候先生与师母,二则向先生请教。先生一如既往,继续给我上课。直到先生九十五岁高龄时,我才不敢再劳累先生,但请安是从不间断的。
拜入林门伊始,师生就形成了一个程式:我入门后先进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到客厅坐定,问候先生的饮食起居,接着便是我请教,先生授业。只是在1990年2月21日师母仙逝后,我进门后先向师母的遗像行鞠躬礼。四十多年,一仍旧贯,连拜年亦循此程式。然而,也有两次例外,这都是因小如师而起。
第一次例外在1979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先生和师母拜年。刚在客厅坐下,还不等我开口,先生就气呼呼地问道:“彭庆生(先生历来只呼名,惟独这次加上了姓)!为什么吴先生的职称至今还解决不了?早在文革前,我就和游先生(讳国恩)联名保荐他破格直升教授。去年游先生去世,我又和吴组缃先生联名保荐他直升教授。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解决?”我很犯难:一则我离开北大已久,不太了解情况;二则虽然也道听途说地知道一点内情,但又怕说出来使先生更加生气。但先生一直盯着我,不回答是不行的,便只好含含糊糊地嗫嚅道:“据说是由于人际关系。”先生似乎若有所悟,但仍然愤愤不平。幸亏我深知先生有个特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提起唐诗、新诗格律、楚辞、《西游记》和篮球这五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先生便会立即兴奋起来,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于是,我便请教:“您说过:唐诗最大的特点是新鲜,如旦晚间始脱笔砚;又说唐诗最高的成就是深入浅出的统一。到底是哪个重要呢?”先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深入浅出!正因为是深入之后的浅出,是深入浅出的统一,才能永远新鲜。”接着又详尽地讲解了“深入”和“浅出”的关系。我心中大喜,一来深受教益,再也不敢在先生面前提如此愚蠢的问题了;二来也得以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其实,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直为小如师的职称问题而耿耿于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小如师早就是教授了,而且,中文系的老先生亦作如是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本书影响深远,一直是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的重要参考书,多次重印,发行量以十万计。小如师注释了其中的先秦神话、《国语》、两汉辞赋的全部和《尚书》、《诗经》、《左传》、《楚辞》中的部分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全部定稿工作,都是由小如师承担的。书稿杀青时,小如师尚未满三十五岁,非家学渊源,功底深厚,焉能至此?游老素以渊博严谨享誉学林,而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定稿工作,全部交给了小如师,可见其器重之深,倚重之切,则其与静希师联名保荐,亦良有以矣!
静希师对我说过:“遇到史料、训诂、考证方面的问题,你就去问吴先生。”组缃师说得更妙:“吴先生对古书熟极了。他查书,从不翻目录,一扒拉就找着了。”我是湖南人,家乡话中没有“扒拉”这个词儿,因而觉得很新鲜,也很生动,记得很牢。在我的印象中,组缃师素来是比较严肃的,不苟言笑,但他老人家竟然也如此推重小如师,则其继游老之后,与静希师再次联名保荐,自亦顺理成章了。
不仅中文系的师生都很尊重小如师,而且,在我看来,系领导虽不给小如师提职称,却一直把他当教授使用。上述《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定稿工作,便是确证。须知当年极左思潮泛滥,反对“个人名利”,两书的署名,都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而参与选注的先生,有的已是副教授了,却由一位“讲师”来定稿,岂不发人深省?
1961年秋,北大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留了四个研究生:李文初的导师是游老,齐裕焜的导师是小如师,黄侯兴的导师是王瑶先生,我拜入静希门下。这四位导师中,游、林、王三位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家,惟独小如师还是讲师。但我们一点都不惊诧,都觉得小如师带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我和裕焜同班且同寝室,长达九年,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我深知:数十年来,裕焜始终执弟子礼甚恭,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充满敬仰与感激之情。他也很争气,很用功,深得小如师之真传。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荣获教育部社科著作二等奖,为师门争了光。
小如师不仅带出了出色的研究生,而且还创造了讲师指导讲师的奇迹。大概是六二年前后,河南某大学的一位讲师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系里指定的指导教师就是小如师。当年北大的研究生与进修教师,都住在二十九斋,因此,我和裕焜能不时见到这位进修教师。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说:“吴先生的学问真好!”
第二次例外在1980年春,小如师刚从中文系调到历史系不久。我去拜谒静希师,照例先去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来到客厅,还没坐稳,静希师就问道:“吴先生去历史系,怎么样了?”正好我前几天去拜望过小如师,便毫不迟疑地答道:“挺好的!”先生又问:“他开什么课呢?”我答:“吴先生讲《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历史文献选读》,准备先讲《陆宣公奏议》。”先生说:“好!这《陆宣公奏议》,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
静希师的话,我听清了,但没有听懂,回家就查书,才理解此中的深意。陆宣公名贽,唐德宗时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官至宰相,谥曰宣。他是唐代最卓越的政论家,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翰苑集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资治通鉴》采录陆贽的奏议,竟多达三十九篇,在这部长达600万字的史学巨著中,实属罕见。因此,静希师听说吴先生开了这门课,便赞道:“好!”
然而,陆宣公侍奉的唐德宗,却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饰非文过的昏君。为了使皇帝能听从规诫,接受谏诤,陆宣公不得不在奏议中大量援引经典,多用故实,如《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云:“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这107个字中,接连用了《左传·宣公二年》、《礼记·大学》、《周易·系辞》、《尚书·仲虺之诰》和《诗经·大雅·烝民》的名句,其意无非都是规劝唐德宗不吝改过。更难解的是:奏议中的许多语句,往往化用经史,几乎不露痕迹,如果不熟悉古籍,不明其出处,很容易望文生义或不得要领。因此,陆贽的文章固然富有典雅弘赡之美,却也有文辞艰深之弊,要讲授《陆宣公奏议》,殊非易事。静希师说“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其深意大概就在于此。
这两次例外,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静希师对小如师的关顾和推许。
我自幼顽劣,不怕鬼,还专拣闹鬼的地方去睡觉;不信神,故乡的土地公公,多次被我偷偷地埋在水田里,竟然也没遭报应。然而,年过古稀之后,我却开始信命了。我觉得:我能考上北大,拜入林门,受业于小如师,并受到众多名师的耳提面命,这都是我的福气;而我的两位太先生林宰老(讳志钧,字宰平)和玉如公、两位恩师静希师和小如师的深厚交谊,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
2006年春,小如师命我写一篇介绍静希师的学术成就的文章。虽然我力不胜任,但我知道:这是恩师对我的奖掖,不能推辞。文章写成后,即呈小如师审阅。在交谈中,我首次获悉:小如师是先结识宰老,后听静希师的课,从而成为两代林门的入室弟子。最有意思的是,小如师给我讲了一个掌故:1952年秋,小如师陪静希师到天津去参观工业生产展览会,由于林吴两家是世交,林宰老与玉如公有诗唱和,故静希师就住在吴家。小如师的妹妹见家里来了客人,十分高兴,便向兄长问起林先生的年龄。小如师告诉她:林先生属狗,生于1910年庚戌岁。这个妹妹很聪明,马上联想到:爸爸也属狗,比林先生大一轮(玉如公生于1898年戊戌岁);哥哥也属狗,比林先生小一轮(小如师生于1922年壬戌岁)。按当年书香门第的家规,小孩子是不能上桌陪客的,因此,吃饭时,妹妹就在一旁说:“你们是三狗同桌啊!”虽说是童言无忌,却正好点明了这非常难得的缘分。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小如师尚在弱冠之年,便已深得宰老垂青,授以书道。后来,小如师在《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中写道:“我曾从宰老学习写章草,屡承老人当面点拨指导,不但使我对习字的道理有所领悟,且因写字而涉及作人,宰老往往也以为人处世之道见诲。”
1947年秋,小如师从清华大学转入北大,在宰老寓中初识静希师。翌年,静希师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同时在北大兼课。小如师选修了静希师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此便成为静希师名副其实的学生”(《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语)。1951年秋,小如师应陆志韦、高名凯二位先生之邀,自天津重回燕大任教,一度当过静希师的助手。次年院系调整,静希师和小如师都留在北大中文系,直至2006年10月4日静希师仙逝,我这两位恩师的交谊,几及六十年,又小如师蒙林宰老青睐近二十年。这样的缘分,人间能有几许?
静希师与游老、组缃师一样器重并倚重小如师,只是由于宰老和玉如公的关系,更增添了一份关爱;而个性的某些相近,便使之相知相亲。因此,我一直认为:这两位恩师的交谊,本在师友之间。
小如师在《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中回顾了他与林门两代的交谊后写道:“两代深恩,没齿难忘。”惓惓之忱,溢于言表。但在弟子看来,这话似乎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便是小如师的涌泉相报。
太先生玉如公是书法大家,素有“南沈(尹默)北吴”之誉。小如师自幼从尊翁习字,家学渊源深厚;加之宰老亲授章草和书道,故小如师在书学上的造诣,举世罕见。静希师也工书,但对书学的研究,似稍逊于小如师。因此,1997年,当上海教育出版社决定影印宰老的遗著《帖考》和遗作《书画集》时,静希师就请小如师来整理。小如师不负重托,认真拜读,精心整理,并加以编次。凡有所献替,静希师都欣然采纳。此书出版前夕,静希师又请小如师作跋。这跋写得情深意切,我反复诵读,浮想联翩。余生也晚,未及亲聆太先生教诲,只匆匆见过一面。那是1959年冬,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与我们五六级四班同学合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与《陶渊明诗文汇评》。其时,静希师任教研室主任,我是学生中的编委。我去向静希师汇报工作,正好太先生经过客厅,静希师悄声说道:“我父亲回来了。”客厅的光线本来就不太好,又碰上个阴天,我没看得很清楚,只依稀觉得:老人似乎有些落寞。没想到,第二年三月,太先生就仙逝了。但那有些落寞的身影,却深深刻在我脑海中。这几天,重新拜读小如师的《影印〈林宰平先生帖考及书画集〉跋》,眼前又不断浮现出太先生与静希师的身影。
十年浩劫中,静希师与小如师都遭到抄家之厄,并被打入牛棚。1966年夏,我去北大看大字报,从19楼与20楼之间穿过,曾目睹静希师、游老、组缃师等几位老先生,手里都拿着扫帚或拖把,显然是在打扫厕所与楼道之后,稍事休息,这真可谓“斯文扫地”了。但静希师很达观,竟然还跟我打招呼。我心中十分悲苦,想去接过先生手中的扫帚,便向先生走去,先生看出了我的用意,连忙说道:“扫完了,扫完了!”我无言以对,只说了四个字:“先生保重!”便匆匆走了,那大字报,自然也没兴趣看了。
然而,文革结束后,却有人诋毁静希师。林门弟子多矣,大抵人微言轻,只是在同学与朋友中澄清事实,惟独小如师挺身而出,写了《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一文,例举事实,称颂静希师“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所表现的铮铮傲骨,充分体现出一位坚贞而执著的老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并说“静老这种坚贞而执著的表现真足以使某些人咋舌愧死”。作为林门弟子,我深深地感激小如师;作为吴门弟子,我为自己有人品如此高洁、敢于仗义执言的恩师而深感庆幸。
在中国士人的传统中,历来倡导“道德文章”,而“道德”是位在“文章”之上的。小如师的文章固可传世,而其道德更是门生后进学习的典范。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由于小如师和林门两代的深交,因而对我这个静希师的研究生,总是有些偏爱,更多眷顾,着力提携。
遥远的往事姑且不提,就说近几年罢。2004年冬,我去拜望小如师。蒙先生垂询,我汇报了《初唐诗歌系年考》的进展情况。先生命我将已完稿的《贞观诗歌系年考》送审。没想到,文章送呈后不久,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命我去家中面谈。原来,他老人家已向静希师汇报了审读的意见,得静希师俯允,并和《燕京学报》另一编委程毅中先生商定,决定向该刊推荐拙文。我不胜惶恐,《燕京学报》品位甚高,在该刊发表论文的多是学界耆宿,我辈岂能高攀?我深恐自己有损三位先生的清誉,便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先生勉励道:“庆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接着又说:“你们五六级和五七级,虽然运动太多,下乡下矿的时间也太长,但给你们上课的,大多是老先生。你们的底子还是不错的。”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2005年5月,《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果然刊登了拙作《贞观诗歌系年考》。2006年11月,该刊新二十一期,又刊登了拙作《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林庚先生学术业绩浅述》。2008年5月,该刊新二十四期又刊登了拙作《唐中宗朝诗歌系年考》。这三篇文章的发表,都体现了小如师和老学长毅中先生对门生后进的眷渥与激励。
2008年初,经袁行霈师推荐,北大出版社愿出版拙著《初唐诗歌系年考》。我获悉这一喜讯,便兴冲冲地跑到小如师家,求先生赐序。一进门,才察觉先生正在病中,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说明来意。先生自然为弟子能出书而高兴,但也流露出为难之意。我很失望,便小声说道:“太遗憾了!”没想到先生竟听清了,慨然道:“我不愿意让你遗憾!这序,我来写。”几天后,我又奉命去先生家,先生当面赐序。这序,写在一张八开的竖行稿纸上,蝇头行书,遒劲俊爽,清雅秀逸。我视若拱璧,爱不释手。序文尾署“公元二○○八年三月病中写讫”,这使我联想起陈曦钟、吴书荫、张明高三位学友校注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小如师亦为之作序,题为《新注本“三言”题记》,尾署“1993年8月,小如病中作于北京”。为了奖掖门生,先生两度扶病操觚,确实是不遗馀力了。
在《〈初唐诗歌系年考〉序》中,先生对我奖勉有加,同时也流露出老一辈学者对当今学界的不良风气的不满与忧虑:“今人治学,或浅尝辄止,或游谈无根。”我以为,这是切中时弊的。同时,先生期望:“北大学风,用兹不坠。”我想:继承北大学风,这是恩师对弟子们的鞭策,也是已仙逝的恩师们的在天之灵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