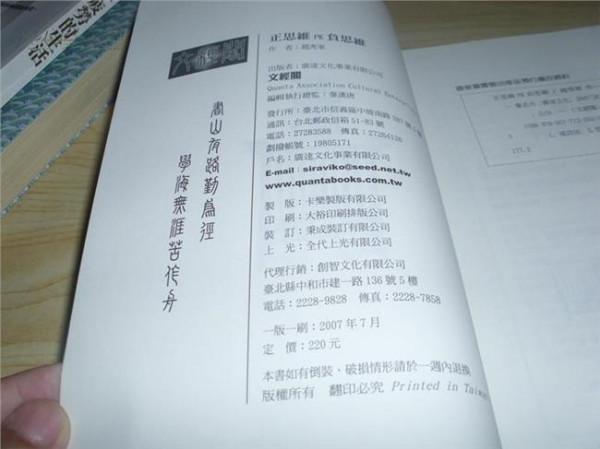陶东风撕裂 陶东风:社会撕裂中的“众声喧哗”
一个稳定可预期社会的建立,最起码的一点是每个个体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进而有普遍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理性的公共空间,宪法最高权威、透明可受约束的制度,以及良善的道德。
“由于没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认定和基本的价值共识,目前中国知识界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多元状态,而是整个社会的撕裂。很多所谓争论的本质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极权和反极权之争。”陶东风在采访中指出,“极权主义并不是跟某一特定群体为敌,从根本上说,它是跟与人类为敌的,是对整个人类尊严的侵犯。”
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陶东风的全文:
娱乐不一定就是非政治的
问:网络对于“公共性”产生了什么影响?
陶东风:像阿伦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的经典理论,是在没有网络的文化语境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他们一般把“公共领域”看成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往的领域。阿伦特讨论的主要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而哈贝马斯讨论的则是18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对于大众传媒对公共生活的影响,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评价都是比较消极的。大众传媒(主要是广播)被认为是一种单向的操控而不是真正的对话。
网络对超越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对公共空间的重建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网络交往、网络传播区别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重要特点,就是恢复了公共空间的互动性和对话性,网络有突出的草根性,其去精英化的作用非常大,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发送者。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形式,同其他传媒形式不一样,它的互动性很强,它重新建构了一种通过网络来运行的公共性。大众的声音很难介入到电视、报纸和广播之中,但是大众在网络中发出声音比较容易。尤其是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被高度控制的情况下,网络传达民意、影响舆论、建构公共领域的作用就更大。
问:公共性必然与政治相联系?
陶东风:这要看你如何理解政治。广义的政治就是公共生活。政治实践必须依托于公共空间。古希腊时代的公民走出家庭私人领域(生命必然性的领域),免于家庭经济活动才能参与城邦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就是政治实践。
问:娱乐与政治什么关系?
陶东风:娱乐不一定是非政治的。我曾经专门写文章分析改革开放初期邓丽君流行歌曲所代表的娱乐文化在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禁锢、建构公共领域和公民生活方面的巨大意义。我也曾经写文章阐明不能把波斯曼的《娱乐至死》简单、机械、直接地运用于中国。
我还分析过大话文学的政治抵抗意义。前段时间又出现了一种恶搞人大代表选举的现象,也属于大话文化。基层选举还存在许多不足的情况下,有些人采取了一种无厘头的方式进行恶搞,比如填苍井空。这是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政治表达方式。
问:还挺严肃的。
陶东风:当然,这里也带有一种无奈。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喜欢恶搞,喜欢这种方式的政治表达。绝对不是。这是在别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不通畅的时候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一种无奈的政治表达。让人笑不起来。即使笑,也不是完全开心的笑而是苦涩的笑。
真正的文学是不相信必然性的
问:您提到“真正的文学天然就是反极权主义的”,如何来理解这句话?
陶东风:我的这篇文章《故事,文学与极权主义》谈到了阿伦特、哈维尔、昆德拉等关于“故事”的观点。阿伦特讲到,故事是人的行动的记录,而行动就是多元的人在公共空间里面自由地展示自己,是一种冒险,它的特点是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偶然性,期间会出现大量意料不到的奇迹。因为行动没有被纳入必然性。只有在行动的意义上人才是自由的。如果纳入必然性,人的自由就没了。
哈维尔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极权社会没有故事”。换言之,被必然性控制的社会没有故事。故事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行动的讲述,所以极权社会没有故事。哈维尔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故事”的。极权社会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纳入到所谓的“必然规律”里,胡作非为被说成“替天行道。”真正的文学表达的是每一个个体不可重复、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故事。
问:这里的“故事”跟通常文学理论所讲的“故事”有何不同?
陶东风:和我们通常文学理论理解的“故事/情节”并不一样。我们的文学理论其实是以革命文学为典范的。因此,不妨从革命文学入手看看这问题。如果说人类学意义上的“故事”意味着行动的偶然、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那么中国革命文学就没有这个意义上的故事——尽管它的故事/情节似乎也很离奇。
革命文学都是按照意识形态话语构造的,而意识形态话语的根本特点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叙事,它把整个人类历史都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不可改变的全盘性方案。
革命文学作品的情节设置、人物命运,基本都纳入了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必然性”:不会有例外,不会有偶然,不会有奇迹,更重要的是,不会有自由。因此,革命文学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意识形态控制区,它的使命不过是要把革命必然胜利性的“故事”讲得“曲折”一些。
问:从这个角度说,经典革命文学中有“故事”么?
陶东风:从阿伦特和哈维尔理解的“故事”意义上讲,肯定没有。《金光大道》《艳阳天》和那些样板戏作品,好像也讲了一个人的经历,也有所谓情节发展的起因、高潮、结束等等,但这个经历、这个情节是按照作者安排好——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安排好——的逻辑去发展的,不是真正的故事,是历史决定论教条的演绎。
“金光大道”只有一条,这就是“高大全”——意识形态传声筒——走的那条。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哪来自由选择?没有自由,哪来的文学?再比如林道静(《青春之歌》之中的人物)的故事最后一定是加入什么组织,走上某条道路,经过各种运动变成一个XX主义者,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
甚至连最后与某人结婚都是纳入了必然性的(第一个丈夫必须离婚,第二个必须死掉——可怜的卢嘉川,因为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因此必须为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让路)。而真正的故事不会告诉你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
伤痕文学的很多作品深层次还是革命文学的逻辑
问: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是否超越了这种必然性?
陶东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并没有超越必然性的逻辑,只不过是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调换了一下,但是深层次里面还是受到必然性逻辑的支配,甚至是变相的革命文学。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故事的。它们也有一个预定的情节发展线索,最后的终点(结局)一定是:黑暗(或冬天)过去了,光明(或春天)开始了,恩怨忘却,“团结一致向前看”。
它同样分享了一套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假设。像《天云山传奇》《伤痕》看起来充满了奇遇,情节离奇,巧合多多,但是这些奇遇和巧合都是按照必然性逻辑安排的,它们不是削弱、消解,恰恰是进一步印证了必然性的逻辑。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就是不知道荒诞为何物。
1985年后出现了一些先锋实验文学对于革命的荒诞式书写,突破了革命文学的深层次逻辑,不仅故事是荒诞的,而且历史没有规律可言,历史并不是必然从一个起点走向一个终点。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之高度评价。但是先锋实验文学有另外的问题,这就是命定论或宿命论。
每个人都注定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灭顶之灾。你看余华、残雪等的小说(如《一九八六年》《黄泥街》),看了第一句就知道了一切都注定了:只能如此。这也是必然性,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必然性。一切都是宿命。革命文学和启蒙文学是乐观主义的必然性,先锋文学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必然性。
有意思的是:阿伦特说的行动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恰恰是乐观的,不可预测才意味着希望,意味着自由和开新的可能性。阿伦特说行动就是开端启新,因为它处在必然性之外。行动的意义就在这里。从本体论角度说,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意味着开端启新的可能,阿伦特把超越极权主义必然性、决定论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人类这种生生不息的新生命。先锋文学超越了历史决定论,但是却没有写出人类的这种希望所在。
阿伦特的这种乐观行动理论当然不同于革命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革命文学的乐观主义。差别在行动的主体是个体还是集体(阶级或者种族)。革命文学中的行动主体是阶级,阶级主体是意识形态的建构。阶级的道路只有一条,每个人都走在这条通向“必然性”的道路上。
















![唐慧是谁 [社论]让社会回归正常 唐慧事件只是起点](https://pic.bilezu.com/upload/f/47/f47362ad104908fad4a90e5fbe734ea9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