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灵魂之旅 邓晓芒: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
邓晓芒的妹妹邓小华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残雪
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一共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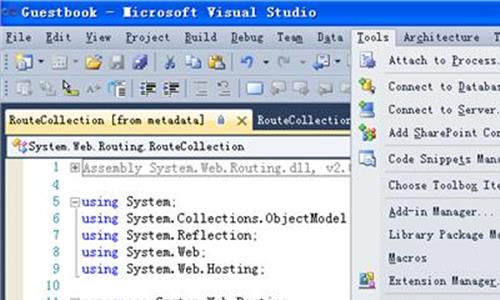
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排除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那些教育付出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的书,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工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中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的父母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过关。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教育经历。
“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我觉得很荒唐”
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旁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
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18000字的信,批评李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是案头书。
《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都必看《美的历程》。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
而对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是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的起点还没有完全脱开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改造。”
杨小凯数学、英语很棒,和邓同住在“筒子楼”
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邓晓芒觉得当年的经济非常贫乏,但大家心情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有一种使命感。
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
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
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易中天想和邓一起去厦大,最终邓没去易却去了
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
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
到了90年代,易中天的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后现代”让中国不思考的学者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哲学不是指导生活,我觉得哲学就是生活。哲学是活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学出来的那不是哲学,那只是哲学知识。哲学史上面的知识有很多,有很多哲学命题的知识,像逻辑学,要划为哲学的话,只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真正的哲学是活出来的,一定要拿命去活。像康德、黑格尔都是拿命去活的,他们都是几十年当家庭教师,受尽了人间冷暖的捉弄,所以哲学跟生活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
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思想访谈
点评当代中国知名文人
中西两大文化在这个地球上互为倒影
李怀宇:晚清民初,西方的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是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于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有。
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面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
到今天,西方的制度严谨,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李怀宇:中国的哲学里面有没有这种传统?
邓晓芒:中国哲学应该就是日常生活的传统。所以,中国的哲学是最好教给小孩子的,当然也适合于老人,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像儒家,我们说从娃娃抓起,《三字经》、《论语》、《孟子》要小孩去背,那些古文他们不懂,但是你如果跟他讲道理,他会觉得非常自然:人是要爱自己的父母啊,然后一步步讲:你爱父母就要爱国家啊,孝是忠的根本啊,这都很顺理成章的,小孩子都能懂。
老庄就适合于老人:你在世上拼搏了一辈子,老了的时候就要想,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还不如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就是回归儿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多好。所以,老庄、佛教、禅宗比较适合于老人读。它都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这些都是生活哲学。
西方的哲学因为重视语言、逻辑,要有推理,比较适合于青年人读,青春期是西方哲学叫做“启蒙”的时期。所以,西方的哲学都是在青春期开始,十五六岁时爆发出对哲学的向往,这也是生活的哲学,当然更强调青年和成人的特点,是开拓生活的哲学。
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多么激进、革命 骨子里都有软肋
李怀宇: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激进、革命、坚强、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非常有价值。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冷静地看出来这些革命者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人,像储安平。
李怀宇:鲁迅可能有切肤之痛,他跟左联那些人的关系并没有搞好。
邓晓芒:他体会出他们的那种霸道,那种唯我独“左”,那种意识形态的僵化,觉得那是很可怕的,没有人性、没有人情味。
李怀宇:后来像胡风、周扬、冯雪峰之间这些关系,暴风骤雨中就显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一面?
邓晓芒:对,胡风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尤其像舒芜这些人,当时都各人自保,也耍了不少阴谋,他们跟王实味可能还不一样,王实味是太傻,书呆子一个。胡风他们还是有政治头脑的,就是懂政治。但是没有周扬那样懂,还是太书生气。胡风想玩点政治,哪玩得过那些政客呢?
钱锺书才华横溢 自己大概也陶醉其中
李怀宇:钱锺书的英文很好,他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你是怎么理解他的这种看法?
邓晓芒:钱锺书当然学问了得,他什么都知道。他有些闪光的分析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些亮点他也说得很精彩,但总体框架是不对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等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都是地球上的人类,都有语言,都会使用工具,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怎么样来解释我们这么不同?要用一个普遍的原则来解释西方人、中国人为什么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才能说清楚。当然可以拉扯很多中国人的说法跟西方人的说法,德国人的说法、法国人的说法,放在一起一比,好像很相像,但是不能到此为止,要能在相像中间看出骨子里的不同。他这方面有些工夫做得好,但是很多是做得不够的。他才华横溢,自己大概也陶醉其中:我什么都知道。
王朔是沉痛的 我非常看好他
李怀宇:除了做研究以外,你还有公共的一面,为什么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深切的批评?
邓晓芒:我写了一本《灵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分析了十几个作家。我还是力图从一种文化转型的眼光来透视这些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他们写这些作品背后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
我总结出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回归,以前叫寻根文学。什么是寻根?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儿童,一个是文盲,没有文化的,人的最低生存境界。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寻根,回到远古,回到古朴、朴素,远离城市。
本世纪的文学又有一些变化,我接触不多,感觉已经不完全是寻根,本世纪的文学基本散了,有点像后现代,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凭感觉。90年代有理念,每个作家都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现在的作家没有要想表达什么东西,就凭一种才气。
特别是网络文学出现以后,基本上就是凭一种临时爆发出来的才情、敏感、调侃,没有一点正经,满不在乎。王朔也满不在乎,但王朔是沉痛的,我对王朔非常看好。人家说他是痞子文学,他表现出来确实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后面有东西。他也能写很纯情的文学。90年代以后,他已经写完了。但他偶尔发表出来对中国当代的看法,非常深刻,他是看透了。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搞怪 没什么意思
李怀宇:近十年来你还有没有看文学作品?
邓晓芒:基本上没看。一是没有时间,再一个是不想看。因为文学已经碎片化。像莫言,我那本书里写了他的《丰乳肥臀》,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给莫言寄了这本书。莫言回信说:你对我的评论非常击中要害,你猜中了我的玄机。
包括心理分析,他为什么要写那个东西?他就是那样想的。他说:我最近又有一本更好的,我寄给你。然后他把小说《酒国》寄过来。他自己觉得《酒国》比《丰乳肥臀》要好,我看了以后很失望。我觉得碎片化,没有一个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在一个空的理念之下,完全是魔幻加才气。当然作家都有一定的才气,完全凭着丰富的联想、搞怪、魔幻,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搞怪,讲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这就没意思了。
李怀宇:贾平凹呢?
邓晓芒:贾平凹后来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也是搞怪。他本来有本土的底子,商州那一带的民风、民气很熟悉,但是完全这样按原本讲,他又不甘心。他要在里面穿插一些魔幻,穿插一些传说、故事,有点像《白鹿原》的那种奇异的东西。
当然中国也有志怪传统,鲁迅当年也很欣赏的。他们现在就搞这些东西,但这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人都有好奇心: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起一种作用?我觉得没多大意思。
中国现在处在赤裸裸的、触目惊心的社会状态,你搞这个还不如老老实实反映现实好一点。或者你就另开一条路,总要有路,现在没路了,就是一点才气,才气完了就完了。我也评了贾平凹的《废都》,就是他的对风土民情的了解、体验,那是没话说的。但是他经常掺杂知识分子的那种梦幻,甚至是性幻想。《废都》完全是性幻想,有点看三级片、成人片的感觉。
中国作家不老实 用写作搏出位
李怀宇:对当下还比较活跃的作家,有没有对谁稍微留意过?
邓晓芒:没有,我后来就比较失望了。当下他们都没有一条路可走,都是各显神通,异军突起的是网络文学。我一般不看网络文学,但有一次看了一篇,觉得写得非常不错,还是现实主义的路。中国这么一个时代,不搞现实主义,搞什么呢?搞其他的都是装饰,没用。当然现实主义也有不同层次,有外在现实,也有心灵的现实。
李怀宇: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而且现在生活里面稀奇古怪的太多了。
邓晓芒:各种冲突,观念的冲突,内心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解体,能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人们都对这些瞧不起,觉得写这些东西太掉格,非要搞些高深莫测的。中国作家不老实,写作不是一种不吐不快的东西,而是为了搏出位的一种手段,这就搞不出东西来。






![邓晓芒文小芒 [邓晓芒]邓晓芒 dasein翻译](https://pic.bilezu.com/upload/2/1d/21d41a67c574fb350fbc0d6b9e4f0caa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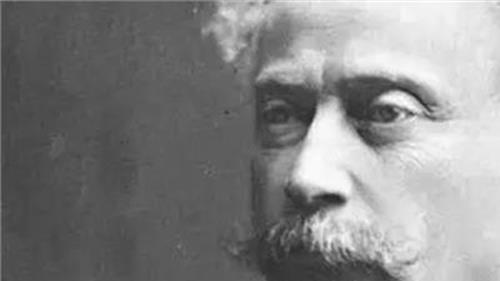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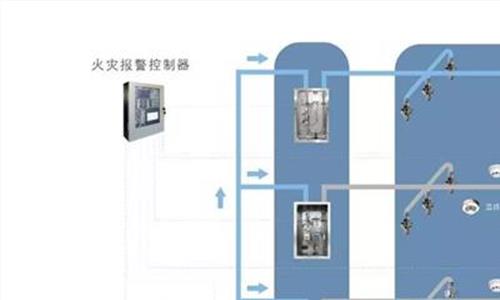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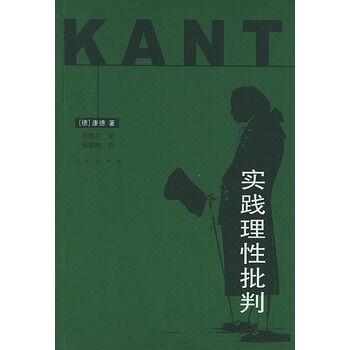


![>《邓晓芒教授著译作系列》文字版+影印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4/02/4023d87b5bd996bb048e57ea52104f3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