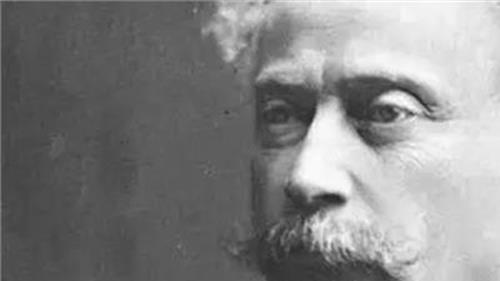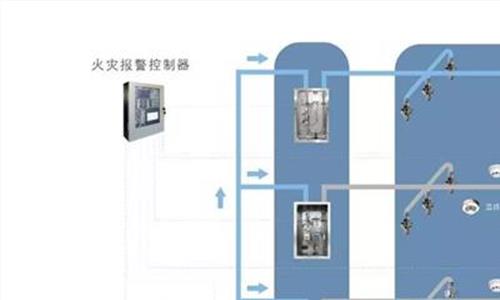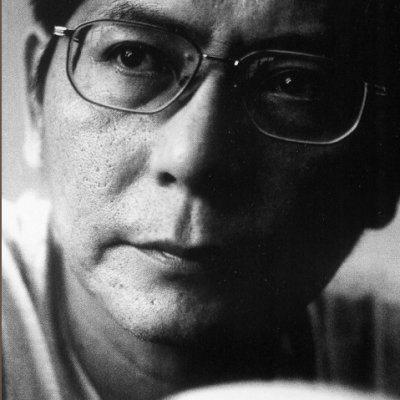邓晓芒什么是自由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下)
最后是自由的谱系。一般自由有三个层次,即自在的自由,自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自由。
1. 自在的自由首先看自在的自由,这是最起码的,就是自由自在,怡然自得,逍遥。这在人的儿童期表现得比较单纯,或者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如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游荡,虽然已经是自由的了,但当时没有觉得自由;只有在后来的怀旧中那种生活才成了自由的理想。

通常,这种自由自在只有在失去时才会被人明确意识到,而在拥有的当时则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自由。只有当产生了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失去了自由,才开始意识到自由了。文明时代初期,人们开始怀念这种失去了的自在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意识总是带有一种怀旧的伤感。

2. 自为的自由自为的自由是第二阶段,它已经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自觉的了。文明社会的建立使自由受到束缚,在国家里面不可能为所欲为。在自然状态里面,是弱肉强食。国家束缚了人的自由,但迫使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

(1)反抗的自由。对不自由的反抗最初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倒退,一种是前进。老庄是倒退、怀旧,想回到自由自在;有的人则说“不”,反抗不自由,还有的人甚至认为自由本质上就是反抗。老庄不是说“不”,而是说“无”;不是反抗,而是逃避。
禅宗则是完全退回到了内心。能够说出“不”是最直接的反抗,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已经有一种行动,而不是一味逃避。当然,真正反抗的行动就是起义、暴动,但这其实还是很初级的自由。起义的农民唯一想望的可能就是“翻身得解放”。
“翻身”是什么?“翻身”就是今天你奴役我,明天我要报仇,要奴役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反抗精神可嘉: 如果连这样一种反抗的自由都没有,那么人就完全成了拉磨的驴了。但是它的层次是不高的,它停留在幼儿的阶段,只会说“不”。它只是自由意识的萌芽,但也是一切自由意识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层次。自为的自由里面首先就是反抗的自由,这是第一个层次。
(2)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已经有了一个目的,这里面有一种理性的权衡,但最终是基于任意性,即任选一个。所以选择的自由就是在理性权衡之下的任意性。在反抗的自由里面没有理性,无可选择,只是要反抗、复仇,只凭一种情绪。
但是选择的自由已经有了理性的思考: 不是仅仅以当前的目的物为转移,而是在各种目的物之间有选择,凭借理性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害的最小化。但这种自由中有个问题,就是可供选择的目标是预先提供的,我们只能选现实已有的可能性。
所以选择是自由的,但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是自由决定的。因此这种自由虽然比反抗的自由高了一个等级,但仍然不是彻底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和儒家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孟子也讲熊掌和鱼、义和利,由你选择(参见《孟子·万章下》),但这种选择是规定好了的: 如果你选择了见利忘义,那你就是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所以你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你不敢沦为千夫所指的禽兽。而英国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如边沁、密尔这些人所设计的选择,它的对象虽然不是自由的,但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 有很多可选择的,你既可以选这也可以选那,这是你的权利。
什么是权利?权利就是你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甚至可以不选择;即使选择错了,人家顶多会说你不明智,但是不会说你是禽兽,那是你的自由。
(3)立法的自由。立法的自由其实在选择的自由里面已经有了,权利本身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法,所以又翻译成“法权”。权利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他人的自由。所谓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立法,这本身就已经是法治了,但是英国人还没有把这种立法当作自由本身的原理,而只是当作实现自由的一种工具。
法律被视为只是对自由的一种外部限制: 你要自由,但是你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否则自由的总量就会减少了。伯林讲“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重要,因为积极自由总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使人不能为所欲为或任意选择,成为不自由。立法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减少: 一个人不能把自由都占全了,你得分一点给别人。
这样,选择的任意性就提升到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志”,任意性和意志的不同就在这里。任意性当然也可以用理性来加以选择,但还是外在的,它本身并不是理性;而意志不但是有理性的,而且它本身就是理性的体现,是有一贯性的、有法则和规律的自由。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意志的意志”,因为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这种立法自由在西方古希腊就已经有它的萌芽了,但还是潜在的,直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立法的自由才得到彰显。卢梭的社会契约是在“公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还有“众意”,但法治社会中公意是最根本的。
什么叫“众意”?众意就是大部分人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就是众意,是大众的意见,但是还不是公共的意见。我们一讲民主,就想到大众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不完全对。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起点,起点是公意。那么,什么叫“公意”?公意就是所有的人都承认,都同意的。但是这样的公意存在吗?我们常常觉得,哪里有一个事情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但是的确有。
比如说,一个社会“要有法律”,这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至于要有什么样的法律,那当然是众意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最后是要诉之于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没有人认为可以不要法律;即使造反的人,也是向民众许诺要建立一个有公平法律的社会,而不是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所以公意才是立法的最终依据,也是立法的自由。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有可能陷入“多数的暴政”,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事先有公意的认可,比如说先由所有的人同意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添加了保护少数的修正,那么即使某些人在投票时处于少数,他也仍然是自由的,因为他事先认可了他处于少数的这种可能性。
而到了康德,就提出“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这就是道德命令,它相当于法律上的“公意”。康德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西方的自由意识上升到了“自律”而不再是“他律”。
自律是更高层次上的自由,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立法的意志,每个人都为自己立法,所以康德讲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也不是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意志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立法的自由既包含了反抗的自由,也包含了选择的自由,但是最终它是一种普遍的自律原则。
它是超功利的,但又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并不违反功利。在外在的层面上它容纳了所有的功利主义原则,但在内在层面上它为这些原则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反思的道德维度。
3. 自在自为的自由比自为的自由更高的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那就是所谓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理想。人类的理想就是自由王国。这个理想康德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目的国”,在这个目的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是目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目的国不同于设想中的“自然状态”: 那种自然状态中虽然每个人也许都是为所欲为的,但总体上看却是弱肉强食。
这种自由王国还可以借用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来说,但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个“矩”不是由先王和传统所传下来的了,而是由人的理性建立在自律的自由意志之上。孔子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他的“不逾矩”是回到本性,属于人的“自在”状态;而“自在自为的自由”则是以前面两种自由即自在的自由和自为的自由作为前提的,是前两者综合起来的合题,所以这个概念不是以人的本性的善、而是以“人性自由”为前提的。
而当这种目的国实现之日,孔子的另一句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话也就会成为现实: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终有一天,国家、法律都会消亡,由道德来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就够了。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只是一个逻辑推论,是否能够实现尚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个理想的终极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说人总要有点理想,不能只盯着眼前: 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清通达这个理想的道路,但是我们有了这个理想,就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看它的自由度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尺度是不可少的,不然我们就没有努力的方向了。
总而言之,做一个自由人,为此而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它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过程;它不但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人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正像胡适所讲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批奴才能够建立得起来的。(参见胡适)所以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有一种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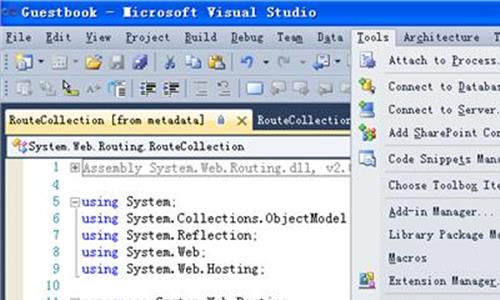

![邓晓芒文小芒 [邓晓芒]邓晓芒 dasein翻译](https://pic.bilezu.com/upload/2/1d/21d41a67c574fb350fbc0d6b9e4f0ca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