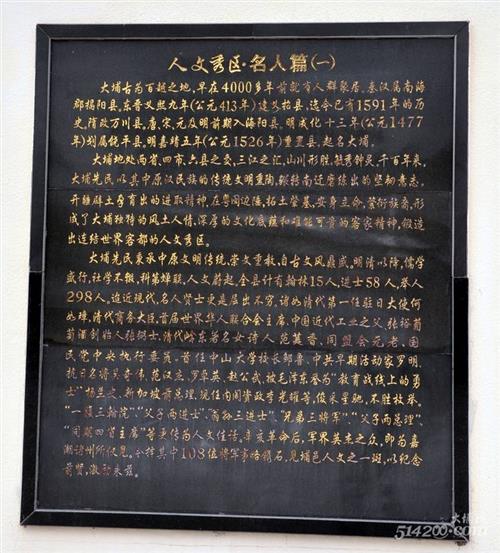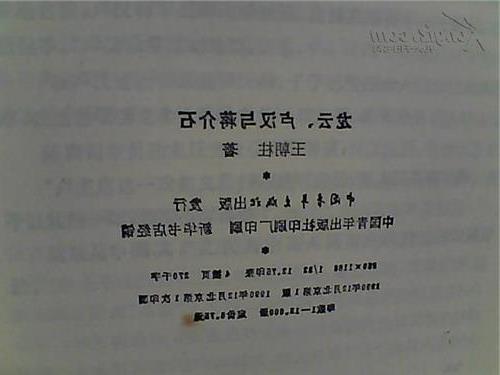方汉奇编年史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当月17日,人民大学举办了“方汉奇教授从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图书馆大厅内,方先生的学术之路图片实物展览也同时举办。
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皓首穷经的老前辈慢悠悠地说出如此语句,让人忍俊不禁。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新闻理念和业务规则都以西方为师,虽然在实践中受到中国社会历史影响,时常彰显中国文化印记,但在学科体系构建上仍有着深刻的西学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新闻史便成为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甚至如下之说也不为过:中国新闻史的学科建设是新闻学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基础,是新闻学在中国独立性体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民国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臬。当时,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最为著名。从所用教学材料和教育工作者的背景来看,来自西方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训练是比较成熟的(美国李金铨教授和张咏教授、中国的邓绍根和王海教授对密苏里新闻学院与中国民国新闻教育的联系均有过深刻论述)。
此时,中国新闻史的知识体系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方先生曾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前,总共出版过不下50多种新闻史研究专著,其中通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剩下的都是地方新闻史、新闻史人物、专门史或者文集之类的出版物,比如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
这里面“最见功力、影响最大”的就是戈氏著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部再版的旧中国新闻史专著。但《中国报学史》仅错误就有200余处,其他的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作为中国新闻学基础学科的中国新闻史,其学科建设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59页)。
从1949年到1978年,第一代中国新闻史的专家学者主要进行了无产阶级新闻史的挖掘,《新华日报》《向导》《新青年》等一批革命报刊获得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受时代限制,这些研究角度单薄、片面,特别是革命报刊以外的新闻史研究更显薄弱。
但是,这并不代表当时的研究没有价值,它借鉴了政治史和革命史,从一个侧面分清了中国报刊发展的阶段和特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借助意识形态和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可以获得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方先生的论文成果题目,都非常朴实,如《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一代报人成舍我》等,这些论文不卖弄艰涩难懂的概念,看似也没有明快点睛的问题意识,仿佛随手拈来,便成一文,但背后史料的广博深入,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
我曾撰文专门谈方先生的史料观,在印证一段关于《开元杂报》到底是不是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先生征引四种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证,读来宛若福尔摩斯断案一般,环环相扣,逻辑清晰。先生曾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言必有征,无征不信。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地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
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后来,有学者认为,“敦煌进奏院状”应该是新闻信,先生亦从善如流。
在东京访问期间,方先生借机去横滨寻访了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改良知识分子的办报遗迹。他边走边回忆,清末志士异域办报的细节,甚至哪篇重要文章出自哪个门牌号码的房屋,都如数家珍,历史镜头感极强。
方先生研究著名新闻工作者邵飘萍。他实地到邵飘萍的故乡调查,通过家人对其属相的回忆,确定了其出生年代,并四次走访罗章龙同志,确定了邵的中共党员身份。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由于新闻史是史学大家庭里的新生代,仅有百余年历史,史料零散少见,且深藏于各种历史文献隐秘之处。尤其是中国古代新闻史的梳理,难度很大。就如,推算《开元杂报》是否可能印刷,“邸报”到底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名称,还是世人对这一类官方新闻传播文本的通称,都需要各种材料互相印证才能推测出结果。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属于文化史的部分”(《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新闻纵横》1985.3)。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百废待兴。1981年,方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率先问世,这是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部通史类著作,内容则比前者整整多了一倍。
“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从戈公振到方汉奇——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座高峰之间》,史媛媛,《新闻爱好者》2001年第五期)。这篇文章赞誉方先生是戈公振之后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另一座高峰。
《中国近代报刊史》里大量的一手资料让人常看常新,新闻史大家、日本龙谷大学的卓南生教授誉其为“不朽经典著作”。此书一出,即成当时新闻史学界的重大事件,引来美誉无数。就在一片赞扬声中,先生公开自曝写作初衷和过程,指出作品前紧后松,越写越放开,但整体上还是个“放了半个脚”的作品。
后来,《中国近代报刊史》准备再版,但方先生表示,就不再进行修订了,因为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还是留给后人做研究吧。
方先生所引领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和路径,对学界后辈影响深远。多打深井、多用一手资料已经在中国新闻史学界成为一种共识。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环境的改善,方先生和宁树藩、陈业劭等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组织全国20多家新闻学术单位的50位学者开始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是中国新闻史学者第一次集合一起从事重大研究,这样的学术开拓可谓前所未有,意义深远。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历时13年,于1992年、1996年、1999年分别完成,全书共计268万余字,研究自先秦两汉以来2200多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
2013年12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由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天窗专业出版社)出版,并面向全球发售,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里程碑,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方先生又联合全国新闻史学工作者,在1998年完成《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的编写工作,全书共计217万字,编撰了自《开元杂报》以降到1997年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2015年,《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又进行修订,将编年史的下限延伸到2015年。
有了通史和编年史,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基础逐渐厚实,在整个新闻传播学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一切都与方先生高远超前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眼界密不可分。
新闻学曾长期是语言学、文学或法学的附属学科,发展没有独立性。新闻学要进行学科发展,必须要进行一级学科建设。
中国传媒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回忆说,那时,新闻学因为是二级学科,有什么重要问题,常常要到一级学科那里去请专家帮忙来进行投票,既不方便,也没有自主性。为此,方先生带领我们多方争取,将新闻学升为一级学科。如果没有方先生领导我们争取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就没有今天传播学成为二级学科的可能。正是以方先生为代表的一代新闻学专家的努力,才为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学科制度上的保证。
方先生高远的学科建设视野还在于创立了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
20世纪80年代,民政部放开民间团体的申报工作,方先生听闻,联合上海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等,一起到民政部注册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并创办《新闻春秋》,并请陆定一和邵华泽两位前辈题写刊名。
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联络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和纽带,是国内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团体。在历届会长的努力下,学会已有16家二级分会,涉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广告、新闻史、新闻理论、传播学、新闻业务、伦理法规等新闻传播学所有领域。在现任会长陈昌凤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的带领下,学会设立了每年评选一次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学会奖。
方先生在民间和官方两个领域对新闻学的建设都功不可没。
方先生的道德文章在新闻学界广受称颂。
我敬仰的大师级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新闻传播史》首席专家、华中科技大学的吴廷俊教授,以新记《大公报》研究和《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两度入主吴玉章学术奖,虽未能入“方门”攻读博士,但一直获得先生无私帮助和指教。他常孩童般地为是不是“方门子弟”而“争辩”,自诩为“方门弟子”,对先生执弟子礼。
民国新闻史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的倪延年教授,指导其博士生刘泱育进行方汉奇研究。刘泱育有幸被拉入“方门弟子”微信群。倪延年教授得知对刘泱育笑言,我想进这个群都难,没想到你倒进了!一席话,惹得在场专家笑语不断。
人大新闻学院马少华老师曾说过,他在课堂上推荐过方先生的一篇文章《跋〈开元杂报〉考》,其重点不是在新闻史方面的知识普及,而是让学生知道,作为一位学术大家,在面对青年一代学术质疑时的谦卑态度,先生的“君子之风”和“古人之风”尽显无疑。实际上,那位提出质疑的年轻学者,在方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从这篇文章出发,继续了新闻史的研究,终成著名的新闻史研究专家。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所有的求助,在方先生那里都会有下文。提携后人是他的一种习惯。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史论部主任、教授,中国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新闻春秋》主编。出版《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等多部新闻史专著,2012年获吴玉章青年学术成果奖。与方汉奇教授合作编撰各种“民国新闻史史料”四辑,共100余卷,主持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