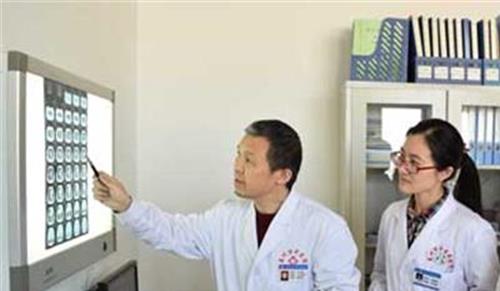颜德馨传人 深切缅怀国医大师:颜德馨
我的家乡江苏丹阳是一个中医之乡,毗邻的常州武进更是著名的孟河医派诞生地。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开业中医,同时他也为刚刚出生的我选定了从医的人生道路。从1920年到现在,长达九十多年的光阴里,我浸润在千年中医的书香和药香里,耳濡目染,孜孜问道,也结识了很多杰出的中医同道。我亲眼所见、亲手所为,中医中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减缓了许多病患的痛苦。

我想,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国医节——我们中医人的节日。1929年3月17日,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卫生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废止旧医(中医)案”,全国17个省市、47个社会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随后推举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位中医界人士组成请愿团,赴南京陈情请愿。

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中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节日。但是这个节日并没有赐予中医吉运。水深火热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医依然多次面临被取缔的境地,它前途未卜,生死难料。而我的父亲出于对中医的了解与热爱,仍然苦心竭力让我接受了成为一名中医必备的基础教育。

1936年我来到上海,考进由中医界有识之士王一仁、秦伯未、严苍山、章次公等人自办的中国医学院。1937年,“八·一三”的炮火,摧毁了我们的新校,在民族危亡、中医危亡的双重打击之下,却催生了更加强烈的自强济世之志。

毕业后在乱世的上海,我一个人打天下,靠做医生为生。那时候行医很艰难,求诊也很困难,我们全班四十余名毕业生,最后从医的只有三四个。为了提高医技,我经常熬夜,多看书,多揣摩,多请教师长。为了多看点病人,我曾经设法进入西医医院为病人诊脉,被洋医生认出来,讥为“末代中医”,这样的羞辱,没齿难忘。
1946年,国民党政府举行过一次中医考试,全称为“三十五年度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此次考卷之多,实为其他各科考试所未有。后来全国及格人员仅362名。四万万同胞,只有这区区三百余名中医师可以合法执业,为他们服务。
随即,全国的中医药学校被勒令停办,中医的前途就是等待这362位中医师消失后,自然灭亡。尽管如此,我从未想过改行易辙。和父亲的信念一样:因为中医对老百姓是有用的,我坚信它不会灭亡。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新生。我于1956年调入国有医院,从此开始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医院体系中的中医执业生涯。凡有大小杂病,必要望闻问切,寻根究本,力求对症下药;又医疗、科研、行政任务一肩挑,把中医科做成了上海铁路医院最有名的科室,直到后来成立铁道部铁路中医技术中心,继而创立衡法理论,到国际传统医学大会上宣读论文,与全球的中医同道切磋学术。
我看病很慢,喜欢探索,人家看不好的病,我总不服气,一定想方设法“抢”到病人,转到中医科,坚持用中医药治疗。我打过很多硬仗,很多疑难杂症都被我拿下,有些顽症,即使不能治好,我也会有精密的分析,告诉病家这病的来龙去脉,并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中医是善术,妙手仁心、大医精诚是祖宗留下的训诫,不可忘记。
以中医行世,要得到承认,真真不容易。坚持,勇于前进,勇于承担一切责任,什么事情都敢走在前面。有病人,就要“抢”过来用中医方法治疗;有杂志,就要写稿;有科研任务,就去接。做事情,不是为别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为中医做。
同行中,有很多改行的,也有很多变成西医的。我忠于中医,没有西化,没有去打针,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越是苦,越是坚持,越是能得到锻炼。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国破家亡,经历过战争和内乱,经历过反右整风运动和十年浩劫,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变故,各种各样的人情,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大家庭,由家而国而中医,多少苦,从来不提。
我很怀念南京傅厚岗1号。父亲在1956年调往南京后,一直住在城北中央路上的傅厚岗1号。中央路是鼓楼附近的一条小路,非常幽静,通往山坡的路两旁都是依地势建造的别墅,傅厚岗35号就曾是李宗仁的官邸。傅厚岗1号也曾是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屋内木门、木窗、木地板,我们和另外一户人家各住一层楼,冬暖夏凉,感觉很舒适。
那时候,傅厚岗一带是许多南京市名人、文化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傅抱石就住在前面的一栋独立小楼中,据说是他卖了80幅画而买下的。有一次,我到南京去探望父母,爸爸跟我说:“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傅伯伯。”就这样我们相识了,跟着傅伯伯,我看了很多名家作品。
中医界有很多人是诗书画俱佳。我的老师程门雪、秦伯未等就是其中翘楚。中国书画怡情、养心,从某个角度来说,都是健康疗疾手段之一。
林散之,我认为是中国怀素和尚之后狂草第一人,当然,中间有个张旭。我和林散之先生结为忘年交,我请他吃饭,他教我写字,叫我先练魏碑,再练习颜体,他当时耳朵聋了,我们就用笔来交谈。
中医界的老前辈也经常聚会,或是到汤山温泉洗澡,或是到栖霞山看枫叶染红,有时候还一起吃饭。马培之的重孙马泽人也在,他的儿子又成为我爸爸的学生。当时我爸爸有粮票,他都攒下来,等我去了,就请大家一起去南京最有名的马祥兴饭店吃饭,这个饭店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匾额。
这是一生难忘的闲适时光,也是中医人最适宜的生态环境。
但是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光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我斗了一辈子——与疾病斗、与西医斗、与要把中医灭亡的无形的有形的障碍斗争。我一直梦想,中医有一天能真正扬眉吐气,能真正获得社会的尊重,能让中医按照中医本来的样子去治病救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守望了一辈子。但我看到的是,真正合格的中医越来越少了,假中医大行其道,他们不仅没能完全掌握中医看病的方法,甚至改变了中医看病的方法。这是真正让人忧虑的。而社会上很多人对中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正因为不了解,被误解,中医被一些人所排斥,这是我们的大悲哀。
中医是古代君子六艺之外的一艺,与历法、农事、建筑、戏曲、武术、军事等共享同样的哲学本源,它教人养身、养心、养神,与天地和谐共处,扶正祛邪致中和。我即便学了一辈子,现在每天还是要看看医书,每每还有更深的理解。
现代医学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并不排斥,但是作为中医,必须确保中医的主体地位不能丢,必须确保用中医的思维来看病,我们应该把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拓展中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现代中医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荣誉。但是我最珍视的一个评价是:颜德馨是一个好医生。无论什么样的病人来找我,我总是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经常有几十年前的老病人辗转找到我说,我的病是你看好的,我来看看你,谢谢你。叫我感动。
我想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吧。一定要有热爱人民的一颗心,人民最后才会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