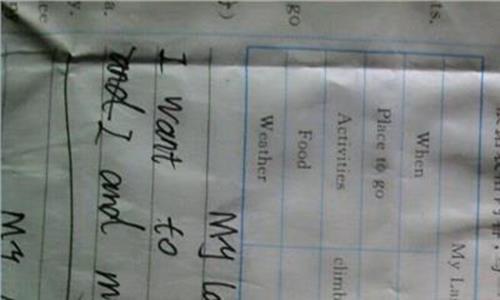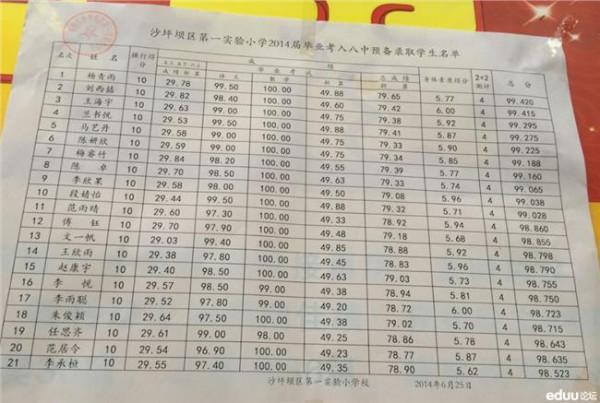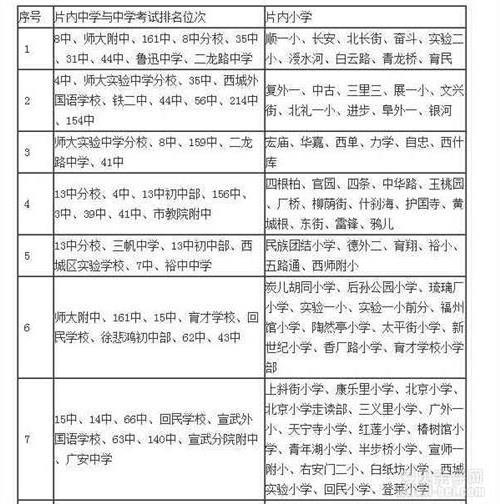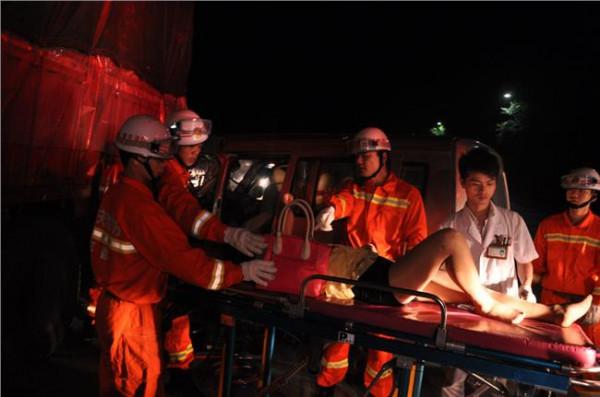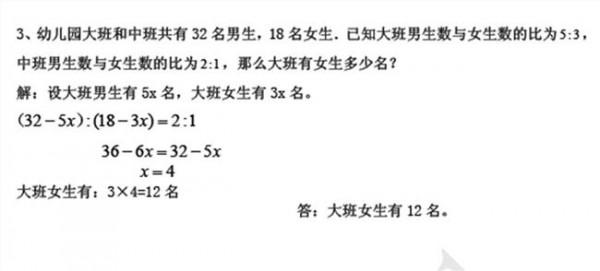顾炎武的名言 柯军谈《顾炎武》:天空没有古今 林冲就在当下
熟悉柯军的朋友形容他,你就是把柯军扔到工地上搬砖,他都会是搬砖第一名。这不仅仅是说他吃苦耐劳,更是说他无论选择了何种命运,或被何种命运选择,都有一种天然纯粹的无怨无悔向前走的力量,用心、专注,不怨不忿。这成就了他的昆曲事业,使之成为中国昆曲领军人物之一,也保全着一个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激情与单纯。

2018年,获奖无数的柯军荣获江苏文化艺术领域最高奖——紫金文化奖章,这一年,他也在原创大戏《顾炎武》中几乎“死过去”又“活过来”。在江苏省昆剧院曾国藩手书大牌匾“明伦堂”下,《文艺周刊》专访柯军。
《顾炎武》是我最重要的一出戏

■ 文艺周刊:明天,作为第二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的开幕大戏,《顾炎武》就要在江苏大剧院演出了。听说前几天您又去了一趟昆山千灯的顾炎武故居,在那里有何启示?
柯军:创排《顾炎武》后,今年已去了三次先生故居。5月5日第一次去,当时刚刚敲定《顾炎武》的剧本,我和当地领导一起去故居造访,寻找感觉。7月15日第二次去,整个剧组到先生故居参观学习,在先生墓前拜祭。第三次去就是10月31日,因为《顾炎武》刚刚在中国昆剧节、百戏盛典开幕式演过,反响不错,想去向先生汇报一下演出情况,希望先生的精神能够继续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把这出大戏打磨好,传递当代昆曲人对“这个社会需要怎样的精神”这一问题的思索。

这次是从上海去先生故居的,我约了一辆专车,但是地图导航导错了路线。以往都是走大路、进大门,在故居内穿堂过院,这次却开进了一条几乎不能通行的道路,过小桥,挤小路,绕小弯,等到下车,一下子就和先生墓地迎头撞上。

太突兀,我的眼泪哗一下子夺眶而出,我赶紧收拾自己的心绪,不好意思被别人看见。饰演顾炎武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如果不到他的墓前去看一看,他也找不到我,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他。他的思想和魂魄其实一直都在,我们在创作、排练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找他,寻他,他才有可能被我们找到。
■ 文艺周刊:《顾炎武》怎么会给您带来那么大的压力?
柯军:演绎故乡最伟大的先贤,我确实心力交瘁,可能太重视、太专注、太投入了。正值三伏天,顾炎武本身是文武兼备,排练我也不省工歇力的,总是浑身大汗,要换6-8件水衣,晚上也热,又是不停出汗,一夜要换三四件衣服。
我从小习武,身体底子是很好的,也感觉在体力上严重透支。还要琢磨戏,耗神费思,排练日记都已经写了55篇。有位老师跟我说,顾炎武这样的人物你们也敢碰,你们敢碰,就要扛得起,你不病才怪呢!是的,顾炎武的思想太博大精深了,一般的演员,不用心的,不爱钻研的,先生才懒得理你,只有用心的艺术家,当你在不断地找他、寻他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看你一眼。
这看你一眼可不得了,有可能就是赐给你智慧和力量,指引你把他的精神品格用戏曲的方式传承下去。
《顾炎武》是一出新编戏,但我们希望修新如旧,仿佛几百年前就有这出戏,这次只不过是把它复排了出来。我几乎愿意投入毕生的精力一辈子去演绎顾炎武,因为先生的精神世界太浩瀚了,光靠两个多小时的《顾炎武》,根本挖不完,他还有很多的思想和故事,等着我们后人深入地挖掘。
■ 文艺周刊:《顾炎武》尚未出炉,就被确定为中国昆剧节和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的开幕大戏。这出戏放到您个人演艺生涯的坐标中,大概处于什么位置?再放到整个当代昆曲新编戏创作的大背景下,又可以有什么位置?
柯军:《顾炎武》在我个人演艺生涯中是最最重要的一出戏。之所以重要,一是顾炎武这个题材在戏曲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哪一出戏表现过顾炎武;二是人物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但是能具备先生这样精神品格的知识分子很少。能够饰演顾炎武是我们当代昆曲人的幸运,也是时代赐予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放到当代的昆曲新编戏创作中来看,《顾炎武》的地位应该也是比较重要的,虽然这出戏还有待打磨,但它的选题十分重大,这一点毋庸置疑。昆曲人不能只是局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唱念做打多么美”里面,要跳出来,想想昆曲能够为现代社会注入怎样的精神力量,这正是创排《顾炎武》的初心所在。
传承和传播,一样都不能荒废
■ 文艺周刊:9月18日,您和奚中路、蔡正仁、史依弘三位上海京昆名家合演京昆传奇《铁冠图》,上海大剧院一票难求。听说,此次京昆群英会克服了跨团、跨剧种合作的重重困难,终于引进到南京。与新编戏相比,是不是传统经典剧目的魅力更大?
柯军:我是“单枪匹马”闯上海滩,客场作战,用的上海京剧院的班底,和上海的名家同台。很难,不敢掉以轻心。演得很过瘾,酣畅淋漓,演出了自己的最好状态。观众的热烈反馈,也让我明白,演员没有白练的功,没有白吃的苦。传统戏历经数百年的传承打磨,多少代前辈的舞台检验,不管是故事文本,还是唱念做表,确实都接近完美,否则早被淘汰了。
昆曲现在好像在复兴,其实危机从来没离开过。在明清鼎盛时期,昆曲有折子戏近3000折。解放初期,“传”字辈演员累积剧目还有600多出。再到“继字辈”“昆大班”尚有近300折。现在,一线正当年的生旦,每人仅余几十出。传一代,少一半,这个状况还不是危机吗?
我在江苏省昆剧院的时候,发起了演员个人专场制,逼着演员去学老戏。最近省里即将实施“名师带徒”制,也是促进传承,宝贝老戏不能跟着老师进棺材啊!学老戏是带演员成长最好的路径。比如我的戏很多都是文武兼备,你如果文不能唱、武不能打,就学不来我的戏,想要做我的徒弟,先去把这些都提高上来。功夫到位了,就有戏了。
至于和新编戏比,谁魅力更大?传统戏曾经是过去的新编戏,新编戏也许就是未来的传统。需要给新编戏一些时间。省昆的《桃花扇》《白罗衫》,其实都是对老本子进行改编发展的新编戏,经过了30年的时间检验,市场和观众确认是经典了,《桃花扇》去年全国巡演,处处轰动。
■ 文艺周刊:今年您的《说戏》出版,这本书以浅显的语言、活泼的形式,单刀直入传统经典剧目,糅以个人的感受思索,读起来特别过瘾。很多读者感慨:我们太需要昆曲人放低身段,把戏说给我们听了。
柯军:有次和作家毕飞宇聊起昆曲,毕飞宇说,我作为中文系的老师都听不明白里面的唱词,别的人怎么能知道你们在唱什么?这使我意识到,昆曲除了传承,还要传播。我在南艺美术馆做讲座,李小山馆长做开场白的时候说,昆曲特别好,但是门槛高,恨不得要自带梯子。很多人可能怕带梯子,也没有梯子,那么这个架梯子的工作我们昆曲人要做。
昆曲表演在舞台上一结束就没有了,但是文字留在那里,可以让你反复去看。而且,作为传承人,我身上的剧目,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昆曲史,我有责任说出去,所以我用《说戏》的方式,收录进我11个代表剧目,完全站在读者视角,“把昆曲拆开来给你看”,展示一个全息的舞台,它的台前幕后、台上台下,它的社会功能、人文关怀。
我不是学者,没有去做学术判断,但是著名戏曲学者傅谨老师说,还从未有人这样用实际表演的一招一式阐释剧目的戏剧性进程……认为我们开创了一种新的说戏的方式。这让我很受鼓舞,我想,如果这个方式真的好,我还有很多老戏,可以这样说出来,给戏曲人看,给全社会看。
现代性使昆曲有了流传与对话
■ 文艺周刊:《夜奔》《沉江》等都是您的传统剧代表作,观众看的时候,会感到剧中人物的命运其实也折射了人类的普遍困境,在古代故事的外衣下,对当代人类的命运表达了关怀。所以是不是可以提出“昆曲的现代性”的概念,来解释这些发生在几百年前的故事,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
柯军:昆曲本身就有现代性。无论是男女爱情、家国情怀还是面对命运的追问,这些都是跨越时空的永恒话题,所以昆曲不只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将来。在《夜奔》中,每次我唱到“哪搭儿相求救”时,总觉得这是在替所有人发问。我在古罗马露天剧场演出,仰望星空,感到天空没有古今,没有国界,林冲就在当下。
对演员来说,在传承时不能为了打开这种现代性,“讨好”观众,而把古人的生活演绎成今天的样子,我们应设身处地演绎古人如何面对盛世繁华和朝代更迭,如何应对自身命运的沉浮,如何想象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国。好的剧目、好的表演一定会把观众带进戏里的情境去思考:假如我是林冲,是史可法,是杜丽娘,我会怎么做?这样就完成了对传统戏曲的现代观照。
所以绝不是传统的东西没有现代性,而是恰恰因为有了现代性,它才得以流传,成为优秀的传统。
■ 文艺周刊:2001年,您受邀在“独角戏”国际艺术节上演《夜奔》,这场不期然的无伴奏版《夜奔》成为您做新概念昆曲的契机。后来您又做了《馀韵》《浮士德》《奔》《藏·奔》《录鬼簿》等多部新概念昆曲作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探索?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
柯军:说新概念昆曲之前,我要说明实验的边界。我们不在昆曲里面做实验,我们演昆曲,就要演原汁原味的昆曲,不能“转基因”;但昆曲的宝库里宝贝很多,我们可以借一点东西到外面来做实验。
我做的新概念昆曲,没有完整的叙事情节,拿出昆曲的一些手段,配合现代舞美,来表达我的思想——这时候,我从一个表演者真正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当我在思考、实验的过程中,我无比接近昆曲创作的源头,接近古代文人在书房里创作时的状态。现在的昆曲,附加物太多了,昆曲原本的素雅、干净,以及思想的高度和纯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所以我想给昆曲做减法,让它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凸显出来。
做实验确实受到一些西方的影响。我和香港艺术家合作实验版《夜奔》,每年在国际艺术节演出,已持续10多年。我意识到,传统昆曲在国外的巡演,在外国人眼中,往往只能达到“猎奇”“观光”的交流层面,而当昆曲参与到戏剧合作中去,才真正变成人人能懂的世界语。所以我们和全亚洲的非遗表演艺术家合作了“朱鹮计划”,昆曲和日本能剧、日本木偶戏、印度歌舞、泰国古典舞蹈等同台创作,寻找不同文化和艺术对话的最大可能性。
可是我几乎不在国内演实验剧。我好像有点“传统地先锋着,先锋地传统着”,也许我有点保守。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好不容易重新认识了传统昆曲,我暂时不要去干扰他们的认知。但可以用于国际对话。比如前年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我和英国莎剧导演合作了中英版《邯郸梦》,昆曲和莎剧同台,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国际交流形式,但在昆曲的故土,我会慎重演出这样前卫的剧目。
■ 文艺周刊:回看您的艺术历程,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艺术家,虽然担当着领导职务,但是自身的昆曲事业一直有条不紊地稳步前进。在传承和发展方面,有什么计划和目标?
柯军:这几年我一直在有计划地做舞台实践的总结,没有记录、总结和传播,很多宝贵的东西就过去了,影子都没有。去年5月30日,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就是要完成300万字的昆曲日记,目前已经写了将近40万字。写日记是为了让我保持自律和思索。
因为人生道路有很多岔路口,明明朝着目标走去,但不知不觉地就走岔掉。走得快或慢不重要,停顿也没关系,碰墙都不要紧,就是不能走弯路。往哪里走,你是谁,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时刻记在心中。我很少出去应酬,喊我吃饭喝酒的,我几乎都拒绝掉。作为一个昆曲传承人,我没有时间花费在那些事上面,更没有资格浪费、挥霍、灭失自己的天赋和使命。
书法家邰劲最近的展览特别精彩,我没时间去现场,但是看了图片,喜欢,就想把我刻的两枚印章“大梦”“无边”送给他,跟他约定:到2045年9月14日我80岁生日那天,我要演《铁冠图·对刀步战》,你把这两枚印章还给我。邰劲一听就来劲了,说真的吗?一定要好好收藏,等着看你80岁演戏。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传承方面,树了个靶子,靶心是80岁演《对刀步战》。你要能射中这个靶心,你的身体、功夫、艺术状态,就都不能退,这个戏演得了,其他戏没话说,我就可以一直挖掘、恢复、学习传统戏,创作新编戏,奉献给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