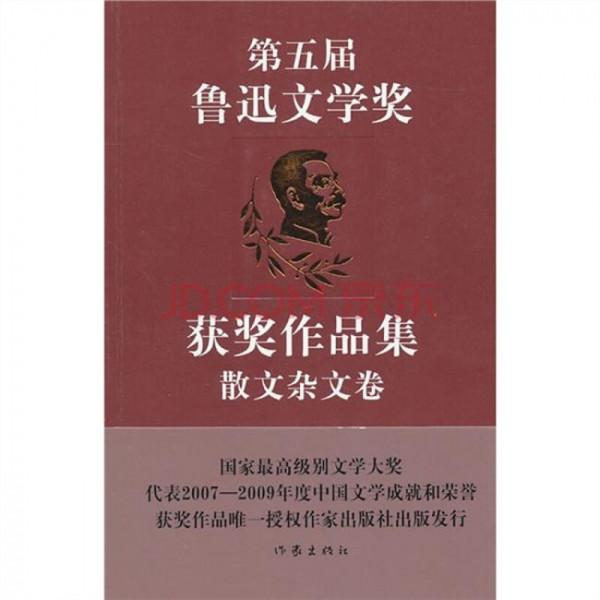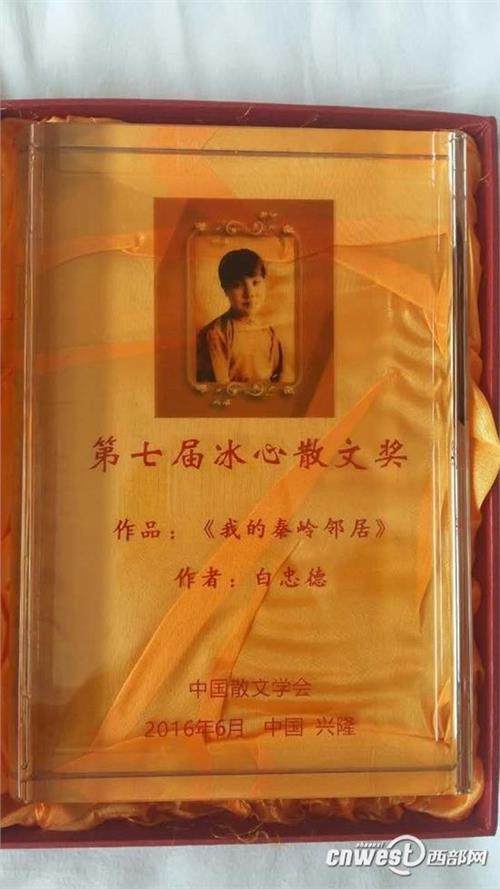朱以撒流水 朱以撒:流水(百花文学奖散文奖作品)
朱以撒,1953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委。
《 流 水 》
文/朱以撒
下课的时候,办公室秘书让我去签一份材料,说:学校让你65岁再退休。把字签完,心里想,如我这么一个高校教师,无党无派、无行政职务,本来就在台下,退不退都是一样的。很多年来,一个教授在学校里就是反反复复地做着一件事,已经十分熟练。
所不同的是,65岁前做事在学校,65岁后做事在家里,只是场所变化了。大学在使用教师是很有意思的,如同分解一条带鱼,切成许多片段,每人领一块回去,把它弄清楚了,靠它吃饭。有人钻研六朝文学,有人就主攻唐宋文学,彼此互不过界。
没有听说教先秦文学的去替明清文学的老师讲课——即便整个文学史都贯通的人,在课堂上,就是守住自己这一块,犯不着越位。这样的安排使人专业起来,毋须广,但求精,时日长了,不带讲义都能信口开河地讲它半天。
后来,我从中文系调到美术系,发现也一样,有人讲花鸟白描,有人就讲意笔人物;有人长于工笔人物,有人就于写意花鸟有过人之技。不同的是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写手,腕下波澜,奔腾不歇,不少人因此破格成了教授。
当我离开的时候,中文系已有教授40多人了。更让人惊异的是中文系善于打造学科,目标明确,手段有效,不消多久,博士点硕士点拿下不少。美术系侧重于个人单干,手工能力如何是最要紧的,画得好不好自己知道,同道也知道,由此更相信个人的努力。直到很后来了,换了识时务的领导,才幡然醒悟,紧赶直追,终于有所斩获。
一个人经历过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系,感受着不同的作风,很是可以品咂一番。一个是很有学问的系,乐于写文,更乐于阅读,腹有诗书。另一个是畏惧于写文,而长于笔墨点染不舍昼夜。现在,有人问,这两个系哪一个更适宜于我?如果时间不似流水,我可能会选择中文系,它的确让人有奔跑的激情,像是有一支鞭子高举起,就要抽下,而奔跑,是能够让人感到释放中的痛快淋漓的。
不过,一个人不是为学术而生的,比学术更需要的是日常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琐屑的、松懈的、柔软的成分。
我觉得美术系的生活更符合我日渐增长的年龄,它给予更多的我行我素的表现。在美术系里,每一个人都是个体手工劳动者,都要解决手头上的功夫问题,希望自己在这一批手工劳动者中脱颖而出。这显然是比伏案码字更让人感到舒畅开心的事。
有人认为在高校当一名教授最为单纯,几次和我这么说,我只是笑笑。不知道他指的是民国时的大学生活,还是现在。对一个在大学墙外的人说起来,还是不太知道里边的动静的。如果一个人真想单纯下来,那就埋头钻研自己的业务,像老僧守庙那样,达到专精。
真的到了庖丁解牛、郢人运斤的程度,谁还可以对你吆三喝四?他越往深入走,同行的就越少,以至走到深处,茫然四顾,形影相吊。这时,就十分个人化、私有化了。他人窥探不到这么做的玄妙之伎,自己也不对外炫耀,只是自我持守,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所谓秘方就是这样,千锤百炼而成了绕指柔,就可以藏匿起来,隐在指腕里了。
有位穆姓的教授认为全系只有一个人能与他对话古典文献。一方面表现了他的精深,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他的清高。据我观察,闲时教授之间不怎么较真学术问题,各自守着,最多在课堂上讲讲。就像我自己,如果讲了一上午的课,回到家里还要与客人论辩书法,真会让人愁烦——难道不能谈其他的话题吗?这使一些专业人员凑在一起,反而谈一些非专业的趣事,他们感到非常舒适。
倒是非专业的人,做生意炒期货之闲,会凑在一起很有兴奋地评说,细听起来颠三倒四,却也不乏消遣的快乐。
一个人几十年的辛劳,逐渐有些质量积储在他的内部,凭借它而产生力量、自信,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有时也目空一切,因为有把握了。这一批人单纯到只重自己的专业,丝毫不介入非专业的纠葛中,不知钟鼎为何物,冠冕为何制,翛然以游,陶然以醉,单纯导致了自由。
人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自古就有化简单为复杂,或者化复杂为简单二种。老子从简,孔子从繁。老子甚至不喜欢人多,小国寡民,鸡声相闻,互不往来。
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做自己的事。孔子则不同,讲业收徒,历聘诸国,彰显学说,交友广泛,一世劳禄。我比较倾向于老子,我一直认为简单是生活的原则之一,简单去掉许多芜杂的枝蔓,看到清旷中的光亮,一定会心绪开朗。
一个人和一个专业构成长久的联系,以至于喜爱、默契,应该视为命中注定。更多的人在寻寻觅觅,或者不断地变换,就是二者之间真的缺少了一点情致,使生命的品质进不去,也就不能久长,需要再去寻找。
后来,大凡一件事在起始时使我感到复杂,我就采取了放弃,不是因为学术的复杂使我却步,是学术的背后隐藏了复杂,而我恰恰无此能力。一个毋须与人合作的专业方向,真是够让人眉宇舒展的了,它省去了许多复杂的合作,使人身心轻盈,像极了秋日里摇曳的蓬松芦花。当然,到了芦花这个阶段,回首看,有许多日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留在大学里工作成了太多人的愿望。它的稳定、体面,甚至还有一些可以炫耀的元素。譬如教授的头衔,还是会让人觉得可靠——大学由来已久,毕竟还是有它的尊严和地位,尤其是百年老校,是会使人生出一些敬畏感的——如果不相信大学、不相信教授,那就不知道要相信谁了。
讲授《易》的教授趁便也替人看看风水算算命,生意真好。每个人都祈求通顺,不通顺的人则求解脱之法。他们忽略了自身的不少因素,只认为是老天不公与她们作对,便把命托付给算命的人,听他双唇开合时吐出的每一个字,还画了符,烧了符,喝了符水。算命看风水当然是世俗的说法,深奥一些叫“堪舆”,算命的人充当天地、鬼神间的使者,把天机泄露出来,然后收费。
人们更相信一个易学教授的法术强过街巷边上摆摊的江湖术士,正宗的、坊间的,需要的人会如何选择,一目了然。大学在背后撑着呢,便胜却江湖术士无数。大学的宽松也体现在对教师的管理之上,完全可以上完课后精心料理自己的公司,或者让青年教师来自己公司打工,没有哪个部门会来指责和制约。
一个老校,有的家庭几代人都设法留了下来,以至盘根错节、连跗接萼,借助大学之名,可以轻巧地为其所为。清人刘熙载就一针见血地谈到“借色”,把个人的真本色遮蔽起来,以借色行于俗情。
大学给借色的人免费提供了便利。留在大学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即便是优秀的博士也未必有如此好运。一个人和一所大学的关连确实存在着某些偶然性,但是,从青年直到老年一直保持这种关系,就可视为必然了。像一棵树种下,就不再移动了。
有时,我指的是深秋,在校园里走,看黄叶飘了下来,就会想到一些与宿命有关的问题,那一年,一位工厂的同伴和我一起高考,他止步于此,当时并没有觉得多少失落。他是仪表工,每月有四十多元的工资,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少。
而我却因了上大学,丢掉了这份工资。十年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变,他先是下岗,回到老家打工,太太过不了清贫日子,跑了。年纪大了,各种疾病又相继而来。他说连给我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十多年前他向我借了500元,至今没有能力归还。
我只能暗暗庆幸当年进入了这个校园,日子走向平和、安定。在这样的日子里,性情像一潭水,无游移不定,绝少涛澜之惊。有个记者曾经问我,如果当年考不进来,生活会如何呢?我最不喜欢假设了,尤其是对于人生,没有假设。
那些需要在年青时用速度解决的问题,一旦无法实现,心里就不快乐了。真文人也罢,假文人也罢,都是很看重面子的,没有谁会轻看职称的评定。那种超然物外无动于衷的人在我视野里是没有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如一拨拨潮水涌来,有的如愿了,有的被打了回去,明年再来。
有能耐的就走破格之路,寻常的就排队等候。如果跟不上趟的,渐渐就与自己这一年龄段的人拉开了距离,落到下一个方阵中去。下一拨的小将勇猛精进毫不谦让之意,加上研究成果丰硕,让老者很是抵挡不住。
于是内心着急惶惶不安,茫然不知所措,面子上,何以堪。职称带来的是相应的物质利益,也带来外表的光彩。光彩是虚的,像影子一样,它缀合了某些神秘的成分,给外界一些明示,或者一些暗示,获得不同的反馈。一个人可能对小助教不置可否,但是对一名教授,至少会礼貌一些。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快乐也会随之而来。她说的就是一种追求的速度,这个速度如果在青年时期就达到,那他的快乐指数不知提高多少。被人憧憬的名分多数是很遥远的,时间消化着速度,有些憧憬此生就烂在肚子里。
一位教过我的老师,退休前两年才凑够了他的成果,他认为是够了,但是评委们认为还不够。个人在评委面前是很渺小的,又无从申辩,只能再抓紧弄一些成果。最终,还是不行。每个人都有想当教授的心思,这个想法肯定是错的,它只是给一部分人准备的,《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是这样的:“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如果都想当面子就会生出许多痛苦来。
一个人的工作习惯随着年龄渐长而徐缓下来。美术系的画室总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是颜料、墨渍、废纸,散发着隔夜的味道。笔洗里的水永远是浑浊的,砚台上的沉渣已经积起了一层。以前我总会因此不快,让他们打扫干净,新水新墨,神清气爽。
我以为从艺者还是要有点精神洁癖的,像晋人那样,有着明月出袖,清风入怀,新桐初引,清露晨流的新鲜,少一些不衫不履乱头粗服的作派。这些作派是没有用的,至少对于我是不屑这一套的。下课的时候我就走出来倚阑看景,黄槐树上缀满了黄橙橙的花朵,玉兰花的香气会淡淡飘了过来,这些澄明鲜洁之物是一种方向,似乎可以作为引导,规避不雅不洁。
偏爱洁净有时成了一种负担,更多的人、更多的场所是不洁净的,好像这样更有艺术范儿。这种气息也会慢慢地改变一个人,有一种随意或者信手的意味,还有一些闲散、慵懒。有些过程是囫囵一团的,不那么条分缕析精到细腻,零乱杂错有时也培养了一些写意的笔调,不那么严密,又很可意会。
翻翻民国间的私人教学似乎是这样,为师的随意地聊,海阔天空,就看学生有没有这种敏感,能够捕捉其中的吉光片羽。捕捉不能在时代疾驰的马背上进行,只能徐缓下来,在书斋里,或在画室里。
画室里总是会有一套茶具,不知是哪一届的学生留下的。大凡有茶具的地方,时间就会变得慢一些,心弦会显得松一些。有学生会去泡茶,或铁观音或大红袍,大家围过来喝。路过的学生也会跑进来,喝它一小盅。
所谓“功夫茶”就是打发时日的,慢功夫才能品出茶的滋味,因为内心已经准备好了,每日里有一段时间就是以慢的动作出现的。我也是后来才学会品茶的。人能够坦然地坐下来,不去想那些只争朝夕的事,看着学生熟练地操作,乌龙入宫,春风拂面,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些动作,清香弥漫开来,此时的情调,更接近旧日文人的生活了。
品茶的松弛,消解了年长、年幼间的在意,无意多了起来。艺术生活更像这样的接续,浓了淡,以至于无。为师的能坐下来,品茶,至少也默认了这种无为的过程,那些用意、刻意的痕迹,被茶水一点点地淹没了。
接下来,等待下课。
我对大学的空间倾向于小雅、朴实,就像我读大学时的老校园,骑着自行车就可以轻松地走遍它的角落。建筑经风沐雨久了,就会少一些铅华多一些质朴,让人亲和,感到它的积累不是浪得虚名。有些人报考之前,会进来考察一番——我当时就是这样,喜欢上了它的优雅之气。
后来,没课的时候我会在校园里走走,看风雨沁入红墙的痕迹。联想当年几个晚清遗老就可以盖起一座学堂,在流水的时光中成了现在这般模样。想不到后来的新校园这么大,这么远,像是夸张的喜剧,内容无多却膨胀得不得了。
大而无当、无味,明摆着都是一些失控的力量所造成的,大了之后就永远小不回去。虽然学会了开车,却未有闲情开着在大校园里闲逛,我不喜欢大而虚的空间,它的非常态特征使我感到突兀,有些疑问只好悬置起来。
秋天来了,有些饱满的石榴还悬在枝头无人采摘,终有一日会在秋阳下忍不住炸开,口子大张。现在我利用的校园空间很小,只须把车开到教室门口,下车上课,渐渐就成了一种持久的动作。
我相信每位教授活动的空间都很小,他们是来上课的,把自己固定在某几条线路上就可以了。一个人没有办公室,就多了一些流动的因素,像一只鸟,飘进教室,飘出教室。以前没有车开,每个人的动作都会和缓一些,会开车了,脾气也急了起来,在校园里也开得飞快,停不下来。
机械的产品多了,大学的气息就是另一种,华丽、堂皇,还有一些洋气。我有时觉得这分明是两个学校,老的不是新的前身,新的不是老的今世,精神、宗旨都有着许多差别,只不过挂着的招牌是一个样而已。
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故乡感、故园情,缘于无特征空间太多了,储存不了什么差异。如果有人把自己居住的小区、别墅称之为故乡,那简直就是笑话了。我在这个城市搬了几次家,说卖就卖,说搬就搬,全然没有对待故乡的依依不舍的态度。
老校友们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聚会都会放在老校区,一定要在这样的物证背景下,使聚会生出更多可以联缀的东西,那些同窗时的旧事会像泉眼,细而密,汩汩而出,按都按不住。这是大而新的校园所不能引导的,它还需要有长久时日的储备。
小助教修成了老资格的教授,就像一根弦,开始绷得很紧,而后渐渐松了,最后松开。年龄大起来成了资历叠加,相应地脱略了一些约束,获得一些自由度,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已臻无法之法。他还必须准时参加会议吗?还必须认真地填写各种表格吗?还必须一篇接一篇地撰写论文吗?此时全然看个人的兴致。
随意——这个字眼用得越来越频繁了,由于不随意太多,它甚至成了日常生活的向往。孙绍振先生快80岁了,还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不停地应邀参加活动。
信手写,信口说,他一定是因此才感到快活的。他曾对我认真地说:整个学校就咱们二人最为著名。他的这种想法,也助长了骂人的爱好,他说骂人是可以出名的,因为骂得准,谁也不好说什么。他让我多多学习他骂人,老教授骂人谁都要让三分的。
他的声音很尖细,语速又很快,好像不必经过大脑就涌了出来。像他这样情性的当然不多,更多的人是淡漠,觉得整体状态就是如此,骂了也没用,反而耗费自己的精神,沾惹一肚子的不快乐。
从事的专业决定着与社会牵连的疏密,有的人教训诂,课堂上已让人畏惧,更不消说到社会上去传播。学问闷在肚里,渐渐就淡化了、寂寞了。孙先生还是很活跃,他和社会活动勾连很紧,他像年青时一样地向前,没有闲愁。
大学是个什么样的空间呢?有人说是江湖。师生关系倚仗知识的传授来维系,在施与受的过程中,将时光推向深入。不过,即便是名气很大的教授,风云一时,也会随着一届一届新生的涌入,渐渐淡去,以至到后来提起,没有什么人知道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段,在台面上,像名角那般地水袖翩翩唱腔生动,许多人在下边听着,聚精会神。但是,再过些年,上台已经听不到太多掌声。时光把曾经主流的人事推到边缘,此时,是要考虑谢幕了。《一代宗师》里的宫二小姐这么说:“所谓大时代,不过是一种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了留在属于自己的年月里,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她居然把绝技六十四手给忘了,我倾向于她这个选择,因为时光已经过了,把它忘了就没有牵挂了。
杜子美说过:“老去诗篇浑漫与”,觉得随着人的老去应该越发任意散漫,化解各种法度规矩,信手拈来,无所羁绊。就像吴昌硕,身边没有刻刀,就捡了一支生锈的铁钉,三下两下,反而刻得率性。年纪大起来的教授会有这种感觉——严密的讲授渐渐少了,多了一些随意的牵扯、发挥,有的扯远了,收不回来;成绩似乎也越打越高了,尽管只是一些数字,数字多起来也是让学生高兴的事。
至于自己下笔就更明显,漫游似地,白云苍狗,形散神也散,再加上简淡、朴素,像秋风带走了草木饱满的汁液和色泽,不禁几分清瘦了。
时光如水——无数次地见到这样的比喻,觉得如此的老旧、寻常。只是再也找不出更为恰切的比喻,像流水这般地让人明白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