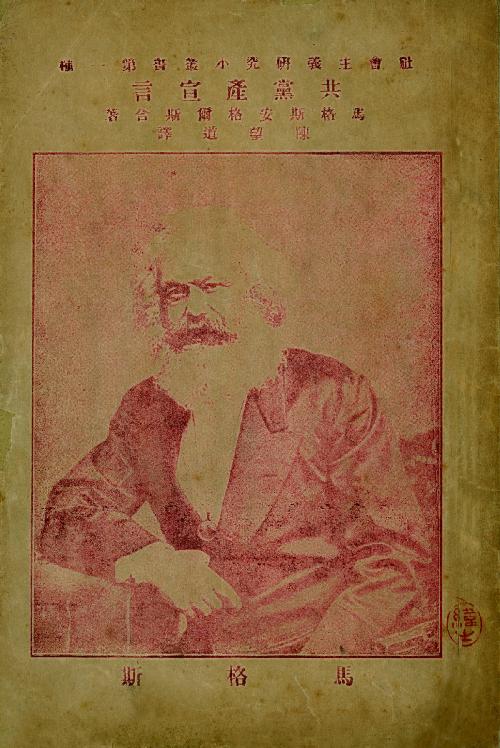是历史选中了陈望道 解密:陈望道为何退党 翻译《共产党宣言》历史细节
关于参加建党的重要活动——陈望道主编《新青年》时,对稿件采取某种宽松态度,主张不同思想倾向的稿子,可以照登
陈望道于1920年4月末来沪后,与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当时,建党成为他们整个工作的核心。于是,一些新的重要任务兴起了,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教育。他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担任了3个月的劳工部长,亲自下厂组织工会、开办职工补习学校、指导斗争,成就是很大的。
可是,这些他未曾有过的工作经历,与他的秉性并不甚适应。他在“一师”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水平文化宣传,仍然是建党工作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报刊宣传成了当时他所承担的主要任务。
这期间,陈望道拥有两大报刊的宣传阵地。影响最大的是扬名全国的《新青年》月刊,他来沪后即被陈独秀任为编辑,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深受赞誉。1920年11月,陈独秀调赴广州工作,陈望道担负起该刊主编的重任(八卷五号开始)。
他对此很认真,为便于工作,将自己的住地搬到了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楼上是《新青年》编辑部,楼下是当时上海建党小组的办公室。陈望道称,他和参加编辑工作的“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天天碰头商讨问题”。
他非常注意坚持该刊原有的优良传统,但又着力进行一些适应形势的改革。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对稿件采取某种宽松态度。当时的《新青年》已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党刊了,但他认为对原有作者一些不同思想倾向的稿子,可以照登。这既可以扩大影响,使他们跟过来,又可以在舆论高压政策下,起掩护作用。《新青年》还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着力宣传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不断发展的新成就,鼓舞人民奋勇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另一报刊宣传基地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该刊的主编是与陈同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邵力子(陈曾寄居邵家),他们相互合作得很好,邵忙时陈就代为编辑。在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觉悟》奋起和《新青年》并肩战斗。
不同的是,《新青年》打的是实力拼搏的“阵地战”,而《觉悟》副刊进行的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陈望道在和我们谈话时称:“我们常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觉悟》副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约50余篇。
《觉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着意发表系统性专论,而是注意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探讨与争论中精心阐发,参与者大多为学校师生和知识青年,文字朴实,通俗易懂,社会影响很大。
关于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名称——陈望道提到“内部叫共产党”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期间,上海出现的第一个组织,就是1920年5月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年8月,陈独秀召集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开会,决定成立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书刊上纷纷称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就其性质称“共产党发起组”,避用“中国共产党”称呼。有些文稿中虽提及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史实,但其正文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如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是这样。
近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02年版),发现在介绍上述1920年8月会议时,直称“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词消失了。这是我所见的第一次,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令人赞赏。
陈望道是1920年8月会议的参加者,当然知道其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情况。可是,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却未提及,只是讲了一句“内部叫共产党”,也算透露了一些实情。
陈望道对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名称的认识,在1920年8月前不存在什么问题。其后,他和大家一样,放弃“中国共产党”真名,而采用盛行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列为党的发起组名称。
这种情况,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常有发生。如把1920年末他接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对于陈望道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列为上海党的发起组名称,我认为还是有其道理的。
因为这一新建的党组织成员,差不多全来自“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领导成员并无变动,所奉行的纲领也是一脉相承。在这种情况下,说它也属上海党的发起组,是有合理依据的。不过,这里也要分清“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1920年8月前后之别,其前三个月不在本讨论之列。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被确定为代表,却不去参加。一般的说法是,因为当时陈独秀到处说陈望道和李汉俊要夺他的权,争当书记,陈遂愤而拒参。但陈望道仍是共产党员,不久出任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2年5月该委员会改选时,因他正式提出辞呈,不再当选,就此也离开了共产党。
陈望道离党的原因,在和我们谈话中称是“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其他场合也有类似的说法。1923年,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劝说陈望道取消退党。他称:“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
看来,陈独秀蛮横的家长作风,工作上专断的做法,是造成陈望道退党的直接原因,这当时是大家的共识。但我又想,把这看作全部缘由所在,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规程,党员的组织观念也相应淡薄,这和陈的退党有很大关系。
这里我尤其要指出的是,陈望道本人具有某种自由散漫的秉性问题。他的挚友邵力子称:“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朱顺佐:《邵力子传》)。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就团体组织问题投票时,他赞成:建立严密组织的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同上)。
他还不了解组织性对党的工作的重要性,曾对沈雁冰说:“我在党外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但是,陈望道退党后(包括宣布退党期间),一直忠诚于党的事业,不论何时何地都真心实意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于退党的错误也渐有悔悟,解放后他曾作恳切的检讨,并于1957年重回党的怀抱。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原来还是密切的。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他说陈独秀对革命工作“很有勇气,胆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也能身体力行”,发生矛盾后也渐有改善的表现。1940年秋,陈望道去四川重庆任教时,和同时寄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次聚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