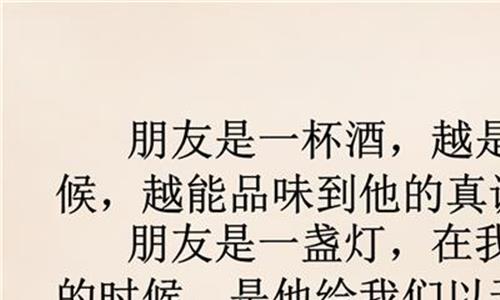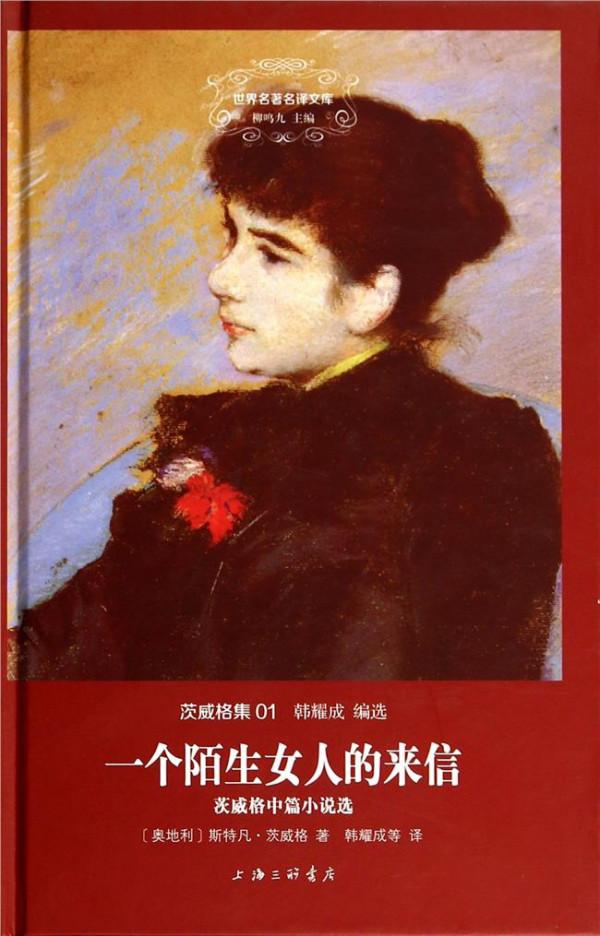高尔基的作品 《洛丽塔》作家竟说高尔基是庸才 为何这般“毒舌”?
纳博科夫的强势自有其底气。他出身于一个贵族世家,一位直系祖先是维罗纳的王子,曾庇护过流亡中的大诗人但丁;祖父在两任沙皇手下当过八年的司法大臣;父亲是个自由派政治家,第一届俄国杜马(注:俄罗斯议会机构)的议员、司法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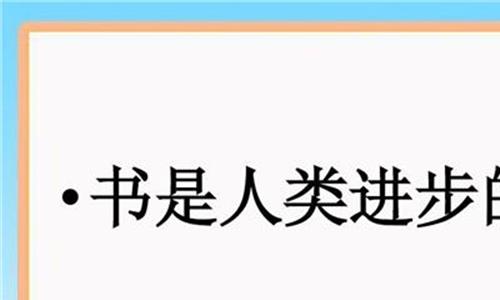
优渥的家庭环境使纳博科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很小就会说俄语和英语,5岁时又学会了法语,以至于他后来在回答哪种语言最美时诙谐而又骄傲地表示:“我的头脑说是英语,我的心灵说是俄语,我的耳朵说是法语。”

十四五岁时,纳博科夫已经用俄语通读了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用英语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用法语读了福楼拜的全部作品,还有大量其他文学作品。然而,纳博科夫最初的志向并不是当一名作家,他自小喜欢和迷恋蝴蝶,12岁时,曾梦想去咖喇昆仑山寻找蝴蝶。

他说:“如果没有俄国革命,我很可能完全投身于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根本不会去写什么小说。”移居美国后,夫人薇拉曾开车15万英里,陪伴他游遍了北美,为的就是寻找和捕捉蝴蝶。对蝴蝶和昆虫学的深入研究,赋予了纳博科夫学者的严谨和细致,这些体现在了他在美国斯坦福、康奈尔、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中,也体现在了他的小说创作中。

优越的家庭教育环境,十月革命后漂迫异乡的经历,父亲被法西斯暴徒暗杀的悲剧,加之移居欧美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洗礼,形成了纳博科夫热爱自由、憎恶专制、独立不屈的个性。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憎恨和鄙视独裁。”他反对文学的流派、团体等观念,崇尚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劳动:“我对文坛上诸如团体、运动、流派这类东西不感兴趣。
我只对个体的艺术感兴趣。”他否定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社会目的,也不传递道德信息,我没有一般观念需要阐述,我就是喜欢编造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
”他对取悦大众的写作不屑一顾,直白地表明:“我的写作只取悦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这些,都显示了纳博科夫的清高与特立独行。
纳博科夫自嘲自己是缺乏大众魅力的人。他在美国的大学授课,都是事先认认真真写好讲义,上课时照本宣科,绝无那些有如簧之舌、可以颠倒众生的教师的感染力。他也厌恶靠谈论作家的八卦新闻来推销作品的手段,“我真正喜欢的更好的公开谈话是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公众面前建立可信的作家的形象,而不是暴露负面的品行。”他对在他的《洛丽塔》中寻找性的人嗤之以鼻。
为了将普希金长达5500行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翻译成英语,纳博科夫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仅索引卡片就做了500张,放满了三只长条鞋盒;他坚持用散文体忠实地翻译这部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之作,坚决反对损害原著的意译,坦承自己的译本不好读,但却是“可靠的、笨拙的、沉重的、奴隶一般忠诚的”。在执拗地主张并践行文学的直译这一点上,纳博科夫与鲁迅先生坚持的“硬译”,有相通之处。
在评点同代或已故的知名作家时,纳博科夫不仅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而且火力全开,毫不留情。比如,他为自己在课堂上将《堂吉诃德》批驳得体无完肤而自豪;嘲笑艾略特“算不上一流”,庞德的诗歌“肯定是二流”;讥讽高尔斯华绥、德莱赛、泰戈尔、高尔基、罗曼·罗兰是庸才,宣称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绝对算不了什么”;直斥萨特的《恶心》是结构松散的二流作品。
他推崇的作家是莎士比亚、博尔赫斯、乔伊斯、罗伯-格里耶,但即便如此,依然直言,“莎士比亚的语言比他的戏剧结构更胜一筹”,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得好,但《芬尼根守灵夜》“只是没有形式、枯燥乏味的一堆伪民俗、一盘冷布丁、隔壁房间的不息的鼾声,令我难以入眠,苦恼不堪”。
对于风靡欧美的弗洛伊德的学说,纳博科夫更是深恶痛绝,斥其为“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纳博科夫的犀利尖刻,也许让人不习惯,但至少要比表面上温良恭俭让、暗地里扒人祖坟的口是心非来得光明正大,何况他的不少点评的确直击要害、入木三分。就像郑板桥所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纳博科夫坚持将“毒舌”进行到底,也难免有荒腔走板之时。比如,他承认自己不太懂音乐,却又说看不出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有什么真正直率的东西”,这多少就有些无知者无畏了。不过,纳博科夫毕竟是纳博科夫,他不从众,不媚俗,我手写我心,尽显高韬狂狷之士的本色。
“事实上,我也像是任何界限分明的大陆。我是大西洋上空的一片羽毛,我的天空多么明亮和湛蓝,远离了鸽舍和那些泥鸽”。纳博科夫的这段话正是他为自己画的最好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