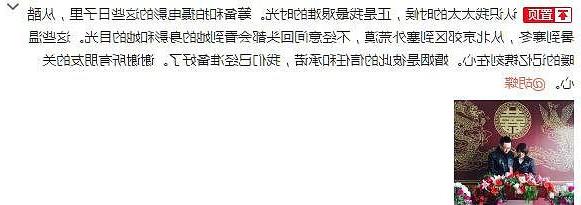李宗仁德公回国了吗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
临终前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本书即为此口述之集结版。 当代爱国名将李宗仁先生第三任夫人胡友松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1月25日去世,终年69岁。胡友松生前曾经详尽回忆自己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以此献给其心目中永远最怀念的德公,深情缅怀和纪念李宗仁先生逝世40周年,谨以此隆重纪念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大捷胜利70周年。

刘澍,出生于西安。 曾出版《往事述说一银幕内外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艺海情侣百年婚恋》、《中国电影幕后往事》、《银海艺影——庞学勤、杨洗伉俪画传》等作品。
序言:梦里花落知多少 引言:周总理亲自迎接的特殊客人 第一章 没家的孩子 “家”和明星妈妈胡蝶 我的养母 校园中突然发生的事件 涉世之初的美好憧憬 演员梦与初恋 渴望幸福 第二章 我嫁给了德公 与德公初次相识 等待新的工作 突如其来的求爱 轰动世界的婚礼 不寻常的新婚时光 德公追忆回祖国前的日日夜夜 蒋介石密谋刺杀德公 当年预测欧洲战事的远见卓识 台儿庄大捷——德公一生的骄傲 程思远神秘的北京之行 辗转归来之梦的前奏曲 意大利记者采访德公 分别多年终会面 难以言表的依依惜别 神秘的异国之旅 德公夫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亲切接见德公 坦然面对“李宗仁回国事件” 郭德洁病逝 德公的另外两次婚姻 随风而逝的往事并非如烟 第三章 与德公风雨同舟的日子 德公的情操感染了我 德公说“命” 乘坐“红旗轿车”的一场风波 德公给我嗑瓜子 德公给红卫兵讲故事 周总理保护李宗仁 德公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 “梅花党”奇案风波 德公不幸患上了直肠癌 在新家度过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最痛苦难熬的日子 陪伴德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第四章 让德公长留人间 离开北总布胡同 在广州、北京的不同遭遇 我喜欢劳动改造 时来运转遂人心愿 情牵一线的桂林之行 李秀文在广西桂林老家定居 钻进书画境界 为李宗仁史料馆捐献文物 好事接踵而来 附录:李宗仁声明 致谢

第一章 没家的孩子 “家”和明星妈妈胡蝶 我是1939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的母亲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电影皇后”胡蝶,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后来社会上流传我是胡蝶和戴笠的私生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稍微有些时间概念和普通常识的人只要一算就知道了,因为胡蝶是1945年到了重庆以后和戴笠认识的,到了第二年才和他同居,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长到八岁了。

所以说,这个漏洞百出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那个时候,我自从出生就随生母托付的养母一起在南京居住,那时生母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若梅”,我随着生母胡蝶的姓。
我跟生母胡蝶只是断断续续地生活在一起。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大人们在最有名的上海大世界里跳“国际标准”舞,那男男女女的舞姿真是好看极了,我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会跟着生母胡蝶到这些高级的娱乐场所里来,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热闹。
那个时候,我母亲胡蝶还很当红,她早在1933年就获得了“电影皇后”的称号,虽然不是中国电影界第一个“电影皇后”,但她获得的这个称号却是叫得最响亮的。
我还记得上海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百乐门”,那里面一天到晚放的全都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还有美国的爵士乐。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那些歌女在台上唱歌,或者是我生母胡蝶和一些电影界的人士登台表演,我就手里拎着一个小花篮在场里来回走动,每当观众投进来钱,我就点头微笑着说“谢谢”。
我长得很可爱,又打扮得很洋气,无论是观众还是电影界的人都很喜欢我。
所以,我跟着生母胡蝶的那段日子,是感觉最快乐的一段美妙时光。 但让我感到不高兴的是,生母胡蝶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她经常到香港去拍戏,再加上抗战时期一直在外颠沛流离,我们母女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生母胡蝶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我,况且她还有自己正式的一家人,我就只好住在那种长期包下来的饭店客房,里面有服务生,定时有人送餐。靠着生母胡蝶的名气,我好像还认过很多干妈,每次出去见她们,都被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一样。
生母胡蝶不在的时候,就只好不断把我托付给这个阿姨那个阿姨的,她们大多数都是一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我就称呼她们为干妈。那个时候,在生母胡蝶出入的交际场合里,除了我就没有别的小孩,所以,我就跟这些干妈们在一起,看她们玩麻将呀、跳舞呀什么的,她们很爱打扮我,还经常带我出去看电影、看戏。
现在年龄大了,好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却记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
在我记忆中,胡蝶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非常讲究穿。她身穿花旗袍,脚蹬高跟鞋,很时髦,她的服装档次也很高,款式新颖,日常穿的都可以随时上镜。特别是她一笑,左脸蛋上还浮现一个酒窝,所以,我印象中她总是特别漂亮。
后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又从上海搬到了南京,记得在我七八岁的那一年春天,我当时已经懂事也记事了,有一次跟着保姆到夫子庙去玩,无意之中撞到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卦桌旁。
我好像记得这位算命先生对着我瞅了又瞅,望了又望,模样很怪,他跑过来追上我的保姆说了一通算命的话,我当时根本听不懂。只是回到家里,听保姆对我说,不让我乱跑,说我以后能遇到不凡之人,我听了,并不理解话里的意思,看保姆的样子,她好像也是似是而非的。
我跟着保姆回到了新街口的一家大饭店,那时候,我们就住在这家大饭店里,这就是我的“家”。由于生母胡蝶跟这家大饭店的卞老板关系很好,我后来就被寄养在这个大饭店里。
我只是朦胧地知道生母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在我出生以后,她就一直很忙,经常是上海和南京两头跑,有时在上海的时间比在南京还要多。到了我该上小学的时候,生母又重新给我起了另外一个大名,叫胡友松。
我一直不知道生父是谁,曾问过生母,她回答我说,你没有爸爸。 记得我是五岁就开始上学了,在南京的白鹭洲小学读的书。平时,在饭店里只有保姆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生活费靠着生母的接济,倒不觉得清贫,只是常年不能跟着亲生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感到缺乏母爱的关怀。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妈妈已经逃难到大后方去了。那个平时我叫宋阿姨的保姆对我还很不错,她除了每天接送我上学、照顾我吃饭睡觉之外,就是给我讲故事,教我背唐诗、唱儿歌,算得上我最早的启蒙教师。
由于还小,我每天除了上学做作业,倒也衣食无忧。只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又有妈妈又有爸爸的,我心里总有说不出来的难受,所以,在没事的时候,就整天坐在饭店的大堂里盼着妈妈能够早点回来。
虽然说,妈妈的模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盼望妈妈的心情却是很迫切的。有一天,妈妈突然回来了,她把我抱过来,在我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又一口,然后,又让我唤她身后站着的那个一点也没有妈妈和蔼的女人叫“沈阿姨”。
就是这个讨厌的沈阿姨替代了以前那个对我特别好的宋阿姨。 有一段时间,妈妈和那个我并不喜欢的沈阿姨住在大饭店里,整天在一起玩牌聊天。到了晚上,和我睡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才和我说说话。这段日子,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但同时也在心底盼着那个沈阿姨快些走,因为我不知怎么的很讨厌她。
不巧的是,这一年的夏天还没有过去,我就得了肺炎,而且浑身还长满了湿疹。我也没法上学了,整天待在饭店的“家”里,妈妈有时候陪着我,但大多数时间好像并不在我的身边,陪着我最多的依然是我最不喜欢、本能就敌视的沈阿姨。
我的这场病是时好时坏,一直拖到初冬也没有完全好透。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天下午,妈妈从外面回来了,给我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还给我买来了一件翻毛皮上衣。
我当然是很高兴。晚饭的时候,沈阿姨也过来陪着我们母女俩一块吃,我那时年龄小,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什么反常的迹象,我哪里知道这顿晚饭竟成了我和生母的最后一顿晚餐。
在饭桌上,妈妈和沈阿姨都争着给我夹菜,这样反常的举动我当然是一丁点也看不出来,我反而还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我只记得妈妈对我说:“若梅,以后妈妈会很忙,没有时间照看你了,过两天你就跟沈阿姨去北平吧。
以后你要记住你的小名叫若梅,大名叫胡友松,你没有爸爸,只有妈妈,以后沈阿姨就是你的妈妈。”我从记事起就经常独自一个人待在酒店里,当时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似乎并不感到十分的意外,只是心里极不情愿妈妈走。
所以,还傻乎乎地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看得出来,作出这样的决定,妈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的心里有很多的难言之隐,我也看得出来她是非常难受的,我用眼睛盯着妈妈,妈妈不敢再抬头,她慌忙掩饰着自己的神态,可是,在她转头的时候,我还是看到她的眼泪落在了胸前的白旗袍上。
那天晚上,我和妈妈仍然像往常一样地睡在一张床上,说了很多话,我都记不清了,最后困得我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是沈阿姨在推我叫我起来,妈妈早已不见了,沈阿姨说妈妈天不亮就走了……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生母是要随着一家人到香港定居了。
医生提出建议,说我得的这个病最好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北方的气候干燥,适宜休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军阀张宗昌在济南死了,他的姨太太沈文芝就跑到南京来当家庭教师,生母就委托她把我带到了北平。 后来,我又听说在1951年,生母胡蝶曾到北京来想接我到香港,只是这个可恶的养母提出许多条件,还非要找胡蝶要一笔钱,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胡蝶很不利,胡蝶唯恐待的时间太久,事情有变,再说她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钱去满足养母的要求,只好连我的面也没有见,就忍痛含泪地匆忙离开了北京。
胡蝶临走前交给沈文芝一个装满首饰的手提箱,嘱咐她一定要供我上大学。
可惜沈文芝挥霍成性,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个装满首饰的箱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阴错阳差,就彻底改变了我整个人一生的命运。
没家的孩子 就这样,在1946年的初冬,我跟随沈阿姨来到了北平,她让我改口叫她妈妈。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在哪里的一家四合院内,我们安顿下来了。由于是冬天,北方时常刮着大风,感觉到很冷,和南京比起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北平。
这大概也是我在南京住得太久的原因吧,当时我已经长到七八岁了呀。 刚到北平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沈阿姨对我还可以,她老是逼着让我改口叫她“妈妈”。可是,还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所谓的“妈妈”就突然对我莫名其妙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她每天打牌、赌钱,随后还渐渐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我们的日子自然会越来越贫穷,由于整天缺吃少穿,一家人大眼瞪小眼地都指望着这个女人,她的脾气和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几乎是天天发脾气,动不动就拿我来出气。
这样的日子是我长这么大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由于自己的年龄还太小,所以不能独立。 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我要不是因为年龄小,好多次真想一咬牙一跺脚离开这个不像家的“家”。
在我倔犟的个性慢慢形成的同时,我也在寻找时机。于是,我改变了以前总是和她顶着干的做法,故意对她顺从一些,表面是屈从和改变了一些,这样,她以为我服了软,对我也变得温和一些,不像以往那样凶神恶煞,非打即骂。
有时碰到打牌赢钱的时候,她也会把我拉到身旁说一些我有时听得懂有时又听不懂的话题来。渐渐地,我也就对这个姓沈的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原来这个名叫沈文芝的女人,是奉系军阀张宗昌最小的姨太太。
沈氏自幼还练就了一身的好武功,并且在张宗昌发迹之前当旅长的时候就做了他的姨太太。 在1932年9月2日的下午,张宗昌在济南火车站被韩复榘派去的杀手给打死了。他的家人听到消息后,顿时感到不但失去了靠山,而且马上要大祸当头了,就各自管自己,纷纷逃命。
可沈文芝却一反常态,她认为自己虽然是张宗昌的姨太太,但也是明媒正娶,所以,当张宗昌死亡的噩耗传来后,她并不像张宗昌的其他大老婆小老婆那样逃得无影无踪,反倒是在家中为死去的亡夫摆上灵牌,披麻戴孝地祭奠起张宗昌来。
后来,官兵们开始搜查张宗昌的房子,实际上是为了强占他的财产,沈文芝这才凭借着自己的一身武功,拼杀着跑出来,最后逃到南京,东躲西藏,一直隐姓埋名地靠给人接生来维持生活。
过了几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沈文芝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生母胡蝶,她很会做事,很快就和胡蝶攀上了,两个人无话不谈,胡蝶把她当做知心朋友,我的出生情况自然也被这个姓沈的了解得清清楚楚。
也许由于我是一个私生女,生母为此有诸多难言之隐,沈文芝千方百计地说服胡蝶同意收我做她女儿,这样无形中也替我生母解了围,因为我整天住在她朋友的饭店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就这样,生母经不起沈文芝的一番花言巧语,就把我送给了她,这样一来,生母似乎也从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认为自己的亲骨肉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沈文芝带我到了北平以后,隔了好长时间,才告诉我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听了这些话之后,感到更加迷惑不解,那时我小小的年龄哪里能够懂得这么复杂的东西,有时候我会一个人悄悄地跑到离家不远处的什刹海,坐在水边,想着连自己都解答不了的疑惑。
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是谁?她跟着丈夫潘有声去了香港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又为什么偏偏把我交给这个我从心底里恨得咬牙切齿的女人,让我跟着她整天受罪呢?我最后得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恨我的生母。
过去发自内心的朦胧的爱,变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恨,恨她的自私,恨她的无情,恨她的冷酷无情。
人在顺境的时候,感到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快乐,但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就感到很难受、很消沉。我那时感到在北平的日子可真难熬,简直与在南京的那阵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
1948年的夏天就来到了。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加紧打仗,北平的形势很紧张,傅作义将军一开始是奉命进行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在死守着北平城。白天听到远方的隆隆炮声倒不可怕,主要是到了晚上,就感到炮声特别的响,常常吓得我从梦中惊醒,虽然我已经九岁了,但还是个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