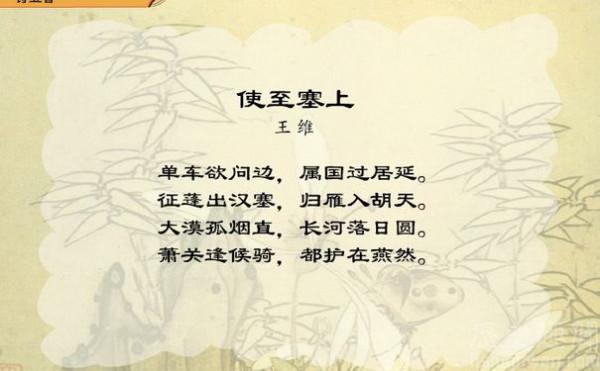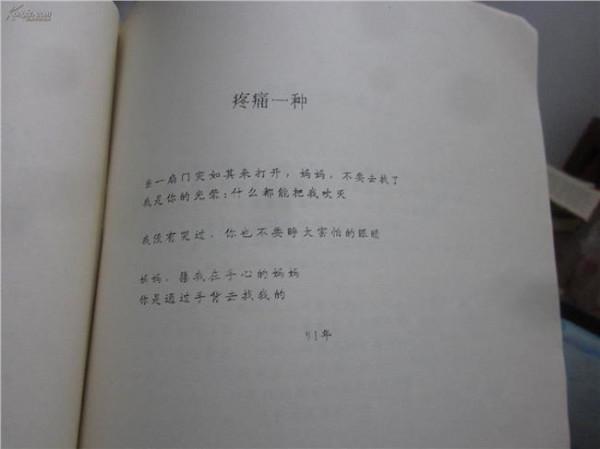汪静之西湖派诗人 汪静之:岂是风月能笼盖
1993年,汪静之已经过了90高龄,早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写了一份“实话实说”的关于自己的小传,最后总结说“我在解放前,都靠不谈政治,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一世平安,没有受过政治上的灾祸”。“苟全性命”云云让人觉得心酸,“明哲保身”云云让人觉得遗憾。这话由一个世纪老人说出,让人心灵震撼。
“一世平安”云云是汪静之对这个世界的善言,因为他并非一世平安,生逢乱世,他为了生计,到处奔波,做了许多违背诗人天性的事,甚至是有损人格的事,虽然不谈政治,但在泛政治环境里,他不得不与政治周旋。早在21岁时,还是学生的他由于父亲破产,不得不靠朋友的接济生活,旋即辍学,被迫离开花都杭州,到武汉去做中学教师,但很快连这个饭碗都丢掉。
1926年,为了得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这个职位(郭沫若介绍的),他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
1927年,宁汉分流时,他总算脱党。但是,1938年4月,他“拖儿带女一家五口逃难到武汉”,生活受到威胁,由于武汉形势不稳,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谋划迁都重庆,连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都没办法帮他找到工作,只好南下广州,“饥不择食”地到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任教,翌年还因为“无法另谋职业,为了保持饭碗,只好被迫加入国民党”。
1929年底,他仅仅因为介绍夏衍到建设大学代上“世界文学思潮”课,而被军警搜捕,靠跳窗逃脱。
抗战期间,他颠沛流离,到处兼课,胜利之后,还得靠与人合伙开小馆子维持生计。1954年8月,他由正式编辑改为特约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了他的工资。直到1956年5月,他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但工资非常低,哪够让一大家子人吃饱饭;为此,他曾以几乎是乞食者的口吻给当时的作协领导写信,一面“感谢党的救济培养”,一面求助说“望给我大力支援,给我最低必须的创作条件”。
其实,当时,只要他愿意去教书,生活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但他愿意过比教书更清苦的生活,愿意为自己写作的雄心而吃苦(1957年12月26日给作协办公室的信和1958年3月11日给邵荃麟、刘白羽和郭小川的信)。
汪静之一生多次临近政治的旋涡或泥潭,但最终能免祸的原因,除了不谈政治外,还有三个。一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二是人生态度方面的,三是诗人形象方面的。
他与郭沫若关系非同一般。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于1921年,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紧接着于翌年就出版了,成了郭沫若在新诗阵营里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正是因此,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从而结识了他生命中的贵人郭沫若。郭沫若确实在他的危难关头多次伸出过援助之手。
汪静之懂得进退之术,并没有太固守某种人生观,能和光同尘,能与世浮沉,而且始终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当然,有符竹因那样的红颜知己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也是重要的保障。1965年11月,在文革的风雨即将降落北京城时,他毅然离开了风暴中心,前往杭州隐居;这是他能避祸的明智先见之举。
20岁时,汪静之就以新诗史上第一部情诗集暴得大名,从此他给公众的形象始终几乎是“爱情诗人”,谈风月,而不谈风云,而风月,无论怎么谈,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恩准的、保险的。
其实,汪静之的文学形象哪里仅仅是“爱情诗人”?《蕙的风》一出世就以其中只有一首三行的短诗《过伊家门外》而备受封建卫道士们的訇骂和围攻,那三行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啊。
”最冒犯人的是“瞟”字。鲁迅曾为他扛起封建卫道的闸门,让他这条欢快的小河能自由流淌。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鲁迅为他辩护道:“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
”1925年8月26日,他去拜访鲁迅时,鲁迅亲口鼓励他说,道学家越仇恨恋爱诗,越要勇敢地大唱恋爱诗,让他们去恨!“一个反封建的恋爱诗人,还不够大胆,可见封建礼教在人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1929年11月25日,他再次去拜访鲁迅时,鲁迅明确告诉他:“现在不是写恋爱诗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25年秋,在第一次拜访鲁迅后不久,他因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理论著作,而有以革命诗代恋爱诗的念头,写出了《劳工》和《破坏》等空洞但对革命可能有利的作品。
因为他自认这样的转换没有成功,所以干脆连诗歌创作的热情也下降了很多,转而写起了小说和论著。1926年,他的重要作品不是诗歌,而是小说集《耶酥的吩咐》;1927年,他的主要作品是论著《诗歌原理》;1928年他的主要作品还是论著《李杜研究》(持论比郭沫若出版于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客观公允得多)。
这套朴素、大方而不失精美的文集把汪静之各方面的文学才华、成就和轨迹都涵盖或展现了(包括大量的书信、自传、日记和检讨等),相信有助于补正长期以来读者心目中的他的文学形象。(北塔)
《汪静之文集》(全6册),飞白、方素平编,西泠印社2006年第一版,1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