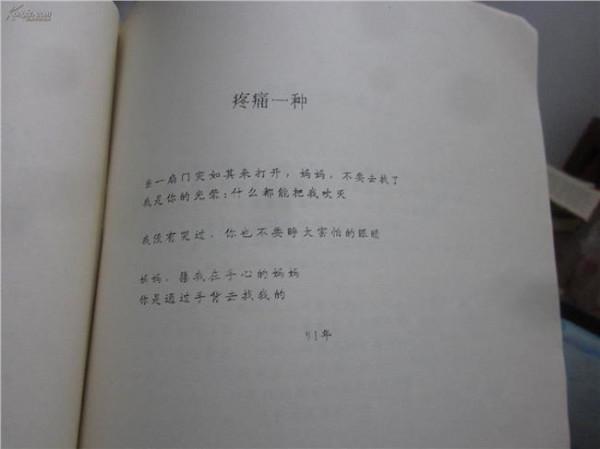汪静之简介 汪静之和西子湖畔的“湖畔诗社”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读中文系时,就狂热地爱上诗歌,几乎阅尽中外著名诗集。当时我就知道,在西湖边诞生了我国“五四”以来最早的第一个诗歌团体——“湖畔诗社”。由当时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后为杭州高级中学)的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等四个人自发组织。当时,我从图书馆借来了我国第一本白话爱情诗集——汪静之《蕙的风》,认真拜读。
读后,大有惊世骇俗之感。怎么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可以这样直抒胸臆,对心仪的姑娘如此狂热地表白爱情的追求?可在我读书的那个“革命年代”,爱情是属“资产”或“小资”的感情。同学之间即使有爱慕之情,绝对不会直白地说:“我爱你!
”而是隐讳曲折地表达:“让我们在共同学习战斗中建立同志般的友谊吧。”即便如我这样的“叛逆者”,胆敢写爱情诗,也只能偷偷地写在日记上,悄悄塞在女同学的书包或饭碗里,怎么可以如《蕙的风》那样毫无顾忌、无所遮掩呢?这位汪静之大圣不知是何方来的“情魔”。
也许是因缘际会,“文革”结束刚不久,我在主编《西湖》文艺杂志。一位年轻作者来编辑部告诉我:在城东郊区的望江门外工人宿舍中,来了一个北京退休的老诗人,叫汪静之,恰好是他邻居。汪静之,不就是《蕙的风》作者吗?曾是我一度崇拜过的爱情诗人哟。于是,穿过十年的情感荒漠,勾引起我爱的缪斯,我就在一个秋日的下午,骑着自行车越过城东铁轨,到望江门外的工人区去拜访这位汪静之。
乍见面,我有些失望,眼前的诗人绝对不是如同徐志摩那种温文儒雅、风流倜傥的招牌式“诗人”。眼前是一个矮矮憔悴的小老头,花白头发,小圆脸,眼睛不再明亮,瘪嘴也不善言辞,神情似乎十分木讷。他,就是写《蕙的风》的爱情诗人吗?怎么与工人区那些在铁轨边敲石子、捡煤核的老头毫无二致。
开头的谈话极为平淡。他只是简单告诉我:解放后由于冯雪峰的关系,他长期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最近才退休到杭州定居。对“文革”的遭遇,对当时自己的政策没有落实(包括工资、待遇),他只是轻描淡写,没有什么愤懑与埋怨,脸上也没有诗人惯有的那种激动表情。
但当我问他,您祖籍安徽,怎么会决定到杭州来度过晚年?他突然目光闪烁,露出了诗人独有的神采:“我对西湖一往情深哪!年轻时,因为向往西湖,才乘船沿屯溪、新安江,来杭州读书;因为爱西湖,才同冯雪峰他们组织了‘湖畔诗社’,为西湖歌、为西湖哭;因为日夜与西湖相伴,才产生那么多爱情风波,留下那么多爱的回忆,才有《蕙的风》……”
老诗人一打开话匣子,就关不拢了,非常坦率地谈起他与几位姑娘的爱情纠葛,甚至把胡适也毫不隐讳地牵涉进来了……我再一次惊讶不已!这位似乎木讷的老人怎么一谈起爱、谈起情,竟然会如同青年人那样热情奔放、激动不已!忘记年龄、忘记时间,那次采访,他同我一谈就谈到暮色苍茫时分。
从此,我常在西湖边碰到汪老。当时我们编辑部在西湖边六公园,而汪静之每天要绕西湖走一圈。古稀老人竟然有这样的精力、体力,秘密就在于汪老常说的一句话:“对西湖一往情深哪!每天如果不绕湖一周,就浑身难受。”啊,他难道光是钟情西湖的湖光山色吗?恐怕还在寻觅青春的湖畔回忆吧,我想。
打这以后,汪老除了修订《蕙的风》重新出版之外,还整理出不少旧作与写出新诗。虽然在技巧上跟不上年轻诗人日新月异的现代步伐,但还是袒露老诗人的一腔真情。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诗潮正在中国大地上飞速发展。
80年代初期一个夏天,浙江作协在莫干山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诗歌研讨会。汪静之作为老诗人代表也赴会参加,没想到居然在会上与风头正健、血气方刚的“先锋派”青年诗人发生了激烈争论。焦点是“朦胧派”与“传统派”孰优孰劣,中国诗歌应向何处去?由于某些“先锋派”诗人言辞过于激动,伤了汪老的心,老人家一气之下居然不参加最后的会议。
当时,我作为负责诗歌的副主席,得想法安慰这位老诗人。晚饭后,就陪汪老在芦花荡的竹海幽径中散步,他才谈出自己心中的观点,他并不是笼统反对“先锋派”,自己当年写《蕙的风》也属“先锋派”。但诗歌明快也好,朦胧也好,都要率真,都要抒发真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他们的“湖畔诗社”,也有徐志摩他们的“新月派”,更有卞之琳、李金发、戴望舒的“现代派”,正因为互相切磋、共容共融,才有“五四”新文化的辉煌。这,就是我每次经过六公园“湖畔诗社”纪念室时的一点小小感触吧。
薛家柱
汪静之和西子湖畔的“湖畔诗社”
诗人,西湖,爱情,湖畔诗社,诗歌
微观杭州
微观杭州
杭州杂志(ID: hangzhouweekly)
在西湖边曾诞生了我国“五四”以来最早的诗歌团体:“湖畔诗社”。汪静之是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