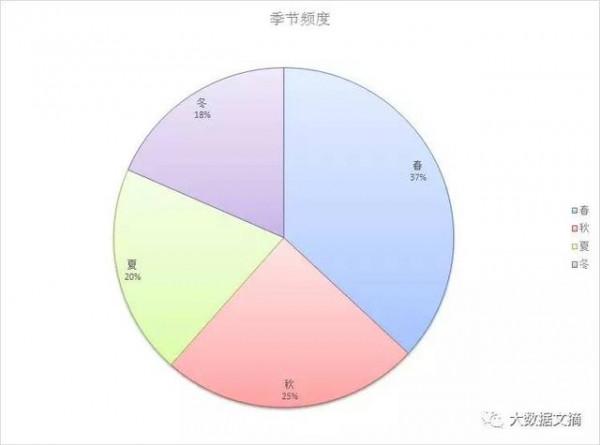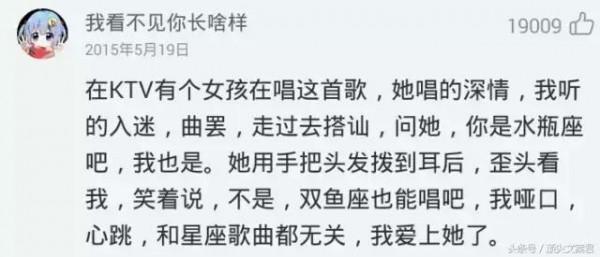黄伟文垃圾四部曲 黄伟文:林夕是神 我只是凡人 !
香港乐坛素有“两林一黄”的说法,其中一林为林夕,一黄为黄伟文。林夕可说是当今歌坛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名气自不待言,而与之齐名的黄伟文,影响力则似乎大为减弱,但是他的歌真的曾经无数次炸裂我。

黄伟文的“丧”值得一提,我相信那些沦落折堕到失去骨相的歌词曾经陪伴许多人渡过失恋或失意的时光。这种丧,在黄伟文和陈辉阳打磨下,诞生了《垃圾》、《绝》、《漩涡》、《破相》四首歌,统称为“垃圾四部曲”。虽然同属一个系列,但前三首是每年出一曲,《破相》则是十年之后老友鬼鬼聚在一起再次书写爱情悲歌。
《绝》、《破相》最为照应,都写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如何摧枯拉朽的破坏一个人的整个人生,一个是“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一个是“快乐再光临,可惜我没能力重生”。
《垃圾》则像极了张爱玲,“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旁观者常常无法理解这种失去自尊的爱情,然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总有人甘之如饴。
他为李蕙敏写的两首歌,《你没有好结果》和《活得比你好》,都以第一人口吻写分手后情人的心态。对于“你”,“我”记恨、诅咒,希望你能够“恶有恶报”。而“我”则要在未来的生活中把“你”比下去,试问这样对人对己的心态我们何尝没有过,所以在听到这样歌词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这首歌原来在唱自己。
《无人之境》写婚外情,毫不掩饰主人公耽溺其中的快乐。 “这个世界最坏罪名,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罪名”。
《裙下之臣》以裙代人,不同质地的裙代表不同类型的女人,但各有其可爱之处。“为那转呀转呀的裙,死我都庆幸。为每个婀娜的化身,每袭裙,穷一生,作侍臣”,以战喻情,笔触直白而激烈,情场即战场,男女欢爱竟如刺刀见血一般,何等危险,又何等诱人, “遣妾一人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的故事,我们也听得太多。女人,似乎天然和战争有一些神秘联系。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黄伟文的词不光写爱情。父子亲情、小人物的沉浮、时光的流逝、城市的繁荣兴替都在他的笔下一一展开。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多疼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一次寻常的父子踩单车,却成为儿子难以忘怀的亲密时光。黄伟文在采访时曾经强调,这首歌与其说是写父爱,不如说是写自己对父亲的怨念。含蓄隽永,语不直白的典型中国人,总是习惯以沉默的方式来表达爱,最后难免从“不善”流于“不愿”。
“那年十八,母校舞会,站着如喽罗”,让我想起简爱对罗彻斯特那段痛彻心扉的自白,即使是一粒微尘,心里也渴望阳光的映照。原来《浮夸》,不过是我们被逼到悬崖了的纵身一跃,是万马齐喑前的最后一丝怒吼。
“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陀飞轮》以名表反映中年心境,有对逝去时光的追忆珍惜,也有对时代的质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将人生视为一场竞赛,哪怕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起点和终点究竟在何处;又是谁,教育我们要风雨急、岁月赶的不停往前冲,再也没有时间去看看沿途小小的风景,与路上遇到的行人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给十年后的我》是一封自白书,歌词全部以疑问句形式展开。由黄伟文这样的过来人写出,又由当时年纪尚轻的薛凯琪演绎,题目虽为现在关照未来,但歌词句句乃是经历过的人回望当初,词作和演绎互动为一种特别的况味。
这样的歌词还有很多,《年度之歌》反思流行,又透露出对人世无常的感慨。《反高潮》借电影手法敲打人性,展示我们受困于这个娱乐至死年代的困惑和挣扎。《活着多好》则模拟逝者的口吻,对吊唁的宾客窃窃私语,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又颇具陶渊明《拟挽歌辞》的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真味。《喜帖街》、《山林道》以香港街市兴衰折射时代变迁,饱含香港本土人对故旧的依恋。
黄伟文和林夕。二人都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比起林夕白衬衫、黑西裤,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恬淡气质,黄伟文剃光头、穿长裙、带鼻环,课余时间为杂志报章撰写时装快讯的前卫形象总有点离经叛道的感觉。
他也曾说:“我从来不和林夕比,他是一个神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对这里的“普通人”,我理解为他以普通人的姿态,用细腻笔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但这恰恰是两人的相通之处。除去一些以禅味入词的作品,林夕绝大部分歌词依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泥淖中挣扎的模样。听歌越多,会渐渐无法分辨黄伟文或者林夕。如果非要将二人加以对比的话,那我更愿意说说他们的同。
两人最直观的一次合作,应该算是为陈奕迅写的国语版《Last order》和《new order》,同样写酒吧一个晚上发生的故事,黄伟文从酒客的角度切入,讲述捉襟见肘的酒客在喝醉后向酒保喋喋不休讲述自己的经历,却碍于面子,欺骗对方这只是自己朋友的经历。
林夕则化身旁观客,静静听着酒客讲述他们的心酸故事,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因这样的故事实在是无时无刻不在酒吧这种地方上演,他一面善意的安慰,内心却满是企望早日实现自己开家花店的梦想。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写隐而不发的爱情,林夕告诉我们“谁须要日后被谁记住,谁贪你想起我的好处”,黄伟文则说“传闻就算你正跟我,秘密拍拖。然而预知了后果,手也未够胆拖”;
写缺乏沟通的亲子关系,林夕说“shall we talk,shall we talk,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黄伟文则说“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
命硬侧田 - Justin
写不被看好的爱情,林夕说“明年今夜至少跟我自助餐上同坐,唱活一首情歌,求大家给你认错”,黄伟文则说“二百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
写抓住时间,爱需从急。林夕说“风花雪月不肯等人,要献便献吻”,黄伟文则说“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而接你变着目送”。
中国的方言有很多,但可以自成一派,在普通话主流之外,生出另一种音乐流行形式,并得到多数人的喜爱,粤语歌是一个奇迹。
能够在上学路上、上班途中、公交车、电台、百货商场听到某一首歌,然后停下两秒,也许是被旋律或歌词吸引,也许勾起了遗忘已久的记忆。无论是哪一种,这些歌曲都曾在某些时刻给过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一点慰藉、一丝温暖。
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欢和珍惜粤语歌,因为“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