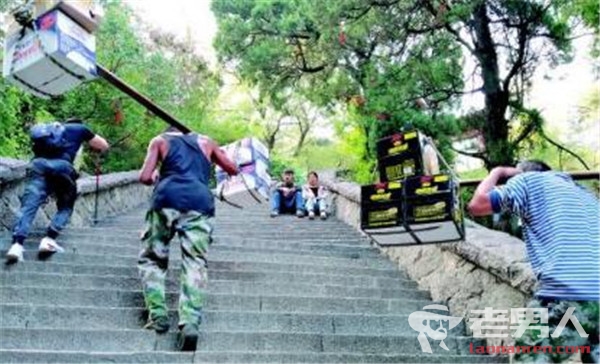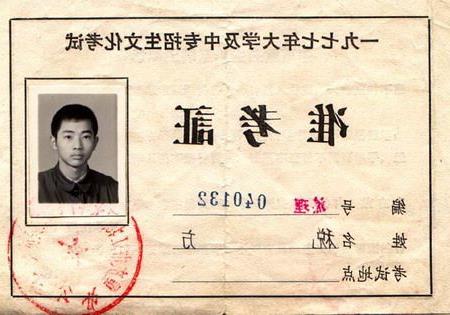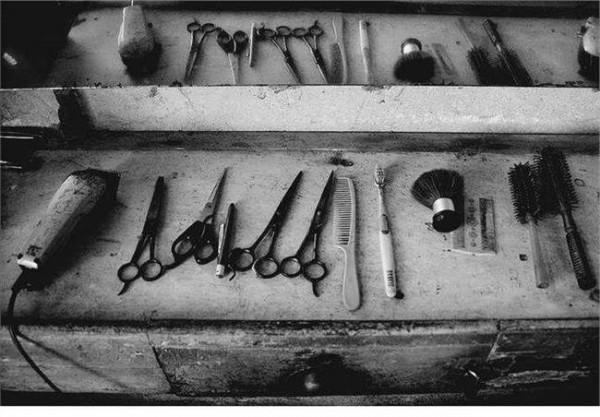周汝昌俞平伯 三十年前周汝昌与俞平伯的“靖本”风云
整整三十年前,也就是1986年,香港《明报月刊》1月号上发表周汝昌先生文章:《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迷》,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这是一篇异常奇特而又重要的“故事”,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异闻记”。这个“异闻记”,实以南京尹延宗先生的采访调查报告为基本主体,我是一个受益的运用者。为了方便读者,我才做了一些附加工作。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凿的根据,调查记录或录音由尹先生妥存,其他文献原件皆在我处保存,必要时可以提供复制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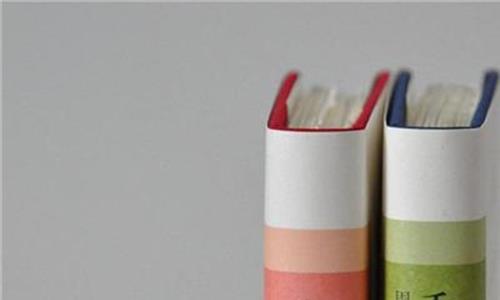
靖本的发现,到现在已有20多年,岁月长流,各人的记忆有相左之处是难免的。况且这20多年的前10多年,又是多事之秋,即或靖本落在某位手中,由于当时特定条件而不便明言,也未及公之于众,这是不足为异,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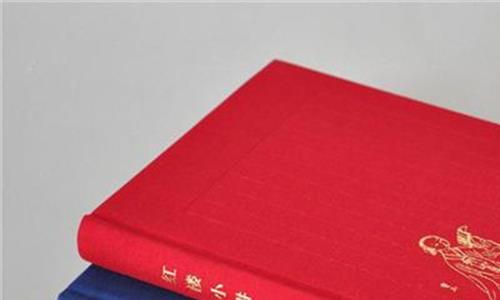
今日神州大地,情况迥然不同了。因此,我相信有关人士终会把此事的真情说出来的。如果早年由藏主让赠,更属事所常有,书的所有权自应归于受赠者,这是有法律保障的,任何人都不该也无意多口多舌,我不过是希望这部极其珍贵的祖国文物,至少能够以影印的方式供诸学界研究,所关匪浅,贡献至重,而且也可以给传抄批语的毛国瑶先生做出最好的佐证。

我们对于原藏主、现藏主的长期保存了此一珍宝,都表示同样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衷心地期望它重显于世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毛氏出示尹延宗的两件明信片所叙内容,一是索还借书,一是说托带之书已经由其女儿取到——此点与陈氏记忆完全相符。问题在于“红楼梦稿”一名究竟何指。

那么。第二件明信片所说的“红楼梦稿”一词,显系一个泛称,而非专名——其意即谓:“某一部《红楼梦》之手写本。”据毛氏言,靖本之文字,亦每与他本不尽相同,有抄写时代更早的痕迹——然则称之为“稿”就是可以的了,何况这是在“明”信片上,简单数语,又不便让局外人得悉何书,那么用“红楼梦稿”四字以代之,完全可以理解。
这种情况,如与靖氏一门的言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观察思索一番,便觉其中隐隐约约,有无穷的丘壑奥妙在。他们所加于我的种种诬罔言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由疑案的解决由他们出来“系铃人作解铃人”吧。】
这里周汝昌强调,其实靖本没有失踪,是落到叉叉叉手中,这个叉叉叉自然就是俞平伯,甚至威胁要写信给中央领导揭发,俞平伯因刚刚得以舒缓政治压迫,对此事愤怒至极又不好发作,对于无端造谣诬陷,只是无奈地表达“这样的人,由他吧”
本文无意炒作红学内部的勾心斗角,谁被谁给做了,又有谁被谁又做了,这些算红楼公开的八卦,只说矛盾重重中个人所持观点:
关于批书人,周汝昌继承胡适说法,脂砚斋畸笏叟就是一个人,并在此发挥到极致,脂砚斋就是生活在大观园的人,因此对应的原型,贾宝玉是曹雪芹,脂砚斋是曹雪芹红颜知己,也就是大观园里史湘云,关于史湘云,周汝昌的文章写过不少篇章,牵强附会,陈腐愚昧,有兴趣读者可以自己查阅。
俞平伯在胡适红学影响下,晚年逐渐苏醒,对胡适路线有很大程度的背叛,修正了自己年轻时期的观点,并在批书人问题上,客观指出,畸笏叟与脂砚斋绝非一人,经典依据就是靖本批语“前批知者: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
因为畸笏叟都说明了脂砚斋死亡,畸笏叟跟脂砚斋怎么会是一人呢?这大大打击了周汝昌死活强调,畸笏叟就是脂砚斋老年时候的另用的号。
对于靖本,俞平伯还有两个比较卓越的认识,由于毛国瑶说,摘抄的部分批语,原来抄手笔迹实在拙劣,很多语句,都是不通顺的,在第十三回“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一句有批语为〖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常村〗,俞平伯根据甲戌本“其弟棠村作序”,认为很可能落款是“棠村”抄误,这一点得到了主流红学,包括周汝昌在内的广泛认可。
值得指出的是俞平伯另外一个认知,他对畸笏叟经典批语“前批知者: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俞平伯认为,“杏斋”是抄误,应当是“枩斋”,也就是前八十回出现的批书人“松斋”,这一点,红学不能认可。为什么不能认可?
因为这个要是松斋,那么他们九牛二虎之力从《四松堂集》找到的“松斋”白筠就被排除了。
(《四松堂集·潞河游记》)
这里的松斋是白筠,跟畸笏叟“丁亥夏”落款的记载死去的“松斋”不可能对上号的,因为主流红学认为,丁亥年就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这个时候的白筠活的很滋润,所以始终没有人接受这个“杏斋”很可能是“枩斋”的抄误。
当然,本人也不能确定杏斋就是松斋,但是,从《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吴祖本或吴本)问世以来,我们看到,后28回过录本居然多出出现了“松斋”批语,而据传播人何莉莉确认,前80回中,也未见“杏斋”,所以,俞平伯的“枩斋”推论,红学不能接受,但科学未必就能排除。
因为,《石头记》本来就成书与康熙年间,相比之下,曹寅《楝亭集》中的大兄“松斋”更加靠谱。而这个曹寅记录的“松斋”,跟“枩齋”一样,早已被红学悄悄隐藏在人们话题之外。
逝者如斯,整整30年过去,俞平伯早已去世,周汝昌也离开了人间,今天的人们,谁会想起那些荒诞不经的往事,谁又会对红学有过平静而深刻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