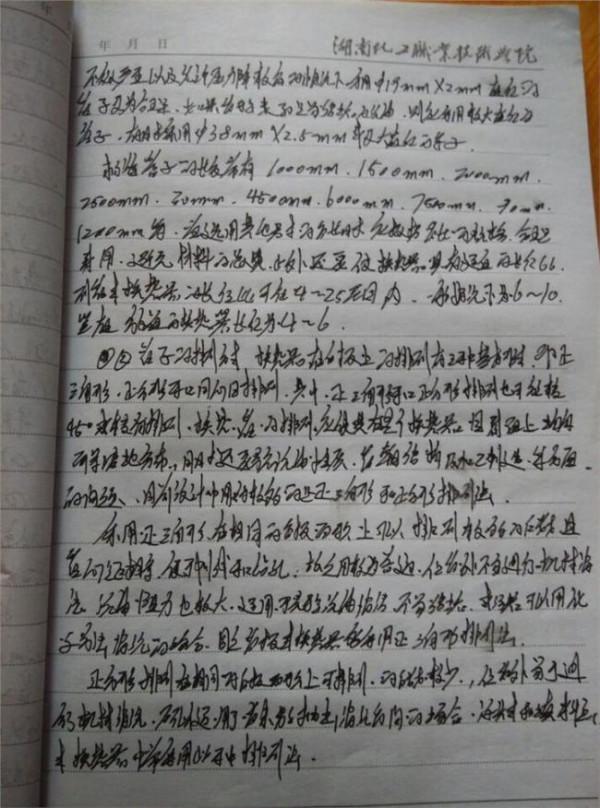曹聚仁杂文集 曹聚仁:从读书说到作文
"好厨子能把一只旧鞋子做成一盘好菜;好作家能把极干枯的东西说得津津有味。"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引西谚 "我们要是永远念人家的作品,那就永远不会使人家念我们的作品。" ——波布(Alexander Pope):登西亚德(The Dunciad) 许多人相信书读得多,文章就做得好,尤其是读古书。
许多人由于这个愚妄的"相信",以致终身在这方面演悲剧或喜剧。他们也许想不明白,永远想不明白,不读书怎么能够写文章呢?当然啰,睡在床上是睡不出文章来的,但读书以外,并非只有在床上睡的一件事可做;譬如在树阴下坐坐,或爬山过岭地走走,或到草原上捉几只虫儿鸟儿玩玩,未始于写文章没有益处呀?说"开卷有益"的人,不是哲人,便是呆子;哲人无所不通,左右逢源,自然可以开卷有所得;呆子则分不出什么有益无益,只知道去开卷,反正不会有所得。
袁子才(枚)问得妙:"你们说做诗作文要以古人为法,请问那些古人又以谁为法的呢?"但天下多少呆子只知道读古书,不知道古人并未读古书,而居然为天下后世所法的。
我在幼年时候,就听说一位姓陈的乡人,他读了一肚子四书、五经,负"书箱"的成名,可是他的文章,三行都写不成器。后来我知道金华有一姓郭的,他所读的更多,听说连《资治通鉴》都背得出,可是他写一张取伞的便条,一写就是五千多字,比天书还难懂。
我一生也经过了许多名师,其学问博通的,文章都不怎样高明;文章高明的,学问又未必博通。其实呢,多读书莫如清代的朴学家,而其文章可观的,却是寥寥可数。此中消息,约略可以窥见了。
清代松江有一大学者,有一子二女,他期望那儿子甚切,督责甚严,读书不熟,鞭责以外,还当街罚跪。那儿子不必说做不成文章,连书也读不好。那位大学者甚为懊丧。可是他的两位女儿,既未受严父督课,也未曾受过责骂,居然诗词散文,斐然可观,学问也通达有条理。
这岂不是从另一方面透露着此中消息吗?原来"读书"者,如叔本华所说的只是走别人的思想路线,而作文是要走自己的思想路线;要是胡乱采用别一个人的思想路线以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就等于穿上我们所不知道的客人放在一边的衣裳一样,决不会称身惬意的。
所以我们讨论读收与作文这问题的关联,只能开宗明义,大喝一声,先把"读书"和"作文"打成两截。("清汪凝载少聪明,读书一再过,辄便记忆,故《十三经》、《史》、《汉》,皆能滚滚暗诵。
及试作破题,睫腊未就;薄视之,'然而'两字也。其师曰:'巧冶不能铸木,工匠不能斫金,是子已矣'"事见《明斋小识》,可引作多读书未必能作文的佐证。)
依学习的程序说,"作文"实在先于"读书";因为从咿呀学语时起,我们学习代表意念的词语,学习词语的连缀,用以发表自己的情意。当我们开始读书的时候,最低限度的思路已经通顺。初步读书,其实是开始学习另一种符号--文字,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识字"。
作识字基础的书籍,前人由《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到《四书》、《五经》,大都不和学习心理相适应,又和素习的口语相隔太远,叫孩子们无法去沟通。所幸入塾的年龄正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叫孩子们死读书,记下那些符号。
可是孩子们的心性是软弱的,这一来便把已经通顺的思路又塞住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语言"代表意念,和"文字"代表意思念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古人的思路,他们既已走不通,自己的思路反而被塞住了。
所以幼童"读书"的时候,正是他们的"作文"停滞不进的时候。学习文字符号,大约得有五六年光景,才识得千多个方块字,三五千个词语,逐渐可以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情意了。
不幸一般人所谓"文",只当作酬应或说教的文章看待,定叫他们做"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论"或"业精于勤荒于嬉说"一类的论说,写"劝友人节俭书",或拟"陈伯之答丘迟书"一类的信,那一套符号本来运用得还未纯熟,还叫他们表自己所未有的情,达自己所未有的意,其结果不独做不出好的来,连坏的也写不出了。在千万个秀才中,难得有三五个能写通顺的文章的,就是这个原故。
所以,要认真说到学作文的诀窍,实在无从说起;书呢,无一可读,也无一不可读。吴稚晖先生说他自己人冷摊上看到一本用"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开场的小说《何典》,悟到了文章的作法,这并不是笑话,他说他以前作文,拘拘于师友所告诉的义法,不敢放胆去写;直到看了《何典》,才敢打破义法,什么词语都敢用,什么语调都可用,使他恍然明白文章的秘诀在此不在彼的。
(例如《何典》中"肉面对着肉面"那一句多么土俗,而下面接上"风光摇曳,别有不同"句,又多么雅致;这决非桐城文伯、阳湖名家所敢使用,此于吴稚晖的文章风格大有影响。
)古语说得好,"学无常师"。其实作文亦无常师。吴先生从一本闲书悟得文章秘诀,我们也可从别一方面开出路来。换言之,对于张三有益的五经,对于李四也许正是毒药,拘拘于一定方式的,终必妨碍思路的开展的。周作人先生告诉青年,爱看什么就看什么,这是指导读书的好法门,也正是指导作文的好法门。
一个人的思路,到了十五六岁以后,又渐渐开展起来。那时候,学习文字符号的工程已告一段落,而所接触的世界,逐渐广大复杂起来,思考力因此加强得多。又因为生理的成熟,男女之爱萌生着,也由单纯的进为复杂的多面的情感;那时,自我的意识渐明,对于自己的圈子重新加以估量。
这种对于环境的反应,对于世界的再认识,其实便是无字的抒情文、记叙文、议论文。一个青年,他的生活经验假若是丰富的,假若时常运用他的脑子去想一想,假若有胆量抒自己的情怀的,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作家。以作文为主,以读书为辅,把一切书都当作作文的资料看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书也读通了,文也做好了。
举个例来收场吧:在私塾读书,一开口便读《三字经》,高声念道:"人之初,性本善。"假若那学生聪明伶俐一点的,他问先生,什么叫做性;那先生眉头一皱,不知怎么说才好。可是塾中另一批十二三岁的学生,先生出题叫他作文,已经开出"性本善说"的题目了。
"性本善说",当然十个学生九个做不好,假若有一个顽皮一点的学生,从"食色性也"那一句想出一点意思来,写着:"K镇上今晚有两台戏,听说班子很不错呢;我要和那漂亮的表妹一同去看呀!
"那他就要挨先生一顿手板了。他莫明其妙地挨了一顿手板,又想想圣人所说:"食色性也"的话,只好当作闷葫芦闷在心头。大概要再过五六年,他才知道性善性恶的问题,是从来圣贤所不曾解决,不仅他自己不懂得,连老先生也不懂得;不独想和漂亮表妹去看戏有性之一相,即先生打他一顿也是性之一相,这样一来,文章可写了,不仅可以做成一篇小说,而还可以做成一部书的。
于是他才开始懂得作文的法门,那时他大概有三四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