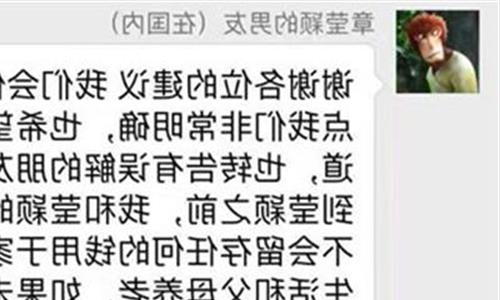邓玉娇案律师 邓玉娇案程序疑点 大案要案律师为何总遭“解雇”?
上周二,邓玉娇案一审判决落幕。有罪免罚的实体结果广受关注,但邓玉娇案从始至终,一些涉及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问题并没有被舆论足够重视。
一些受访的刑法学家对此表示忧虑,中国的司法如果不在程序正义上下功夫,那可能因为舆论关注而保障了一个邓玉娇的权利,但无法保障其他邓玉娇的公正。被他们探讨的邓玉娇案程序正义涉及三方面。

侦查阶段,律师有没有调查取证权?
邓玉娇案中,5月21日、5月22日,发生了一场“证据争夺战”。北京律师夏霖、夏楠会见邓玉娇后,爆出性侵犯情节,请求警方保存邓玉娇案发时穿的内衣内裤。然而第二天,邓玉娇妈妈张树梅称,内裤已被她清洗。

当天,在律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警方封存了已经失去效力的证据。
这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学者对刑事诉讼法33条的质疑。该条规定是:“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这条规定事实上否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这是值得反思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行法律对律师的调查取 证权表述不清。而刑诉法96条又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有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新修订的律师法对调查取证权也没 有完全明确。

陈卫东认为,这种规定是有问题的。在中国,律师很少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辩方自己聘请侦探搜集证据都是允 许的,律师的辩护不分侦查、审查起诉、开庭审理阶段,是连续的。
”陈卫东说,而我国,连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都有诸多限制,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很多人就认为律 师的身份只是一个“法律帮助人”。“作为辩护律师,我们通常是针对控方的证据找出漏洞辩护。”北京刑辩律师许兰亭这样介绍,在侦查阶段,律师几乎施展不了 手脚。
这样不完整的辩护,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控辩双方的权利不对等。其直接结果是,侦查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案件 的证据材料进行筛选,其筛选过程没有任何监督。冤假错案的发生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卫东也认为,在侦查阶段,确实存在控方根据自已的需要“筛选”证据的情况。他认为,按照刑事司法精神,律师只要接受了委托,他就有权利调查取证。这项权利属于非公权力,不应有所限制,只要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侦查阶段是律师取证的最好时机,错过了,就取不到了。
邓玉娇的律师有多大的信息发布权?
邓玉娇案中,律师对邓玉娇遭受性侵犯事实和细节的披露,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批评律师擅自公布案情违反了规定。律师有没有信息发布权?这一问题在学界也有不同看法。
对律师信息发布权,萧瀚持维护的态度:“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和警方同样拥有发布信息的权利。”他认为,犯罪嫌疑人通过律师对外发布信息,不但是律师 的基本职业权利,更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只要没有撒谎,没有捏造,除了一些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不愿意公开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刑辩律师就拥 有自由、完整的案情信息发布权,“他们无需看政府的脸色行事”。
对此,陈卫东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律师发布信息的权利是从律师调查取证权引申而来。律师对案情进行调查后,能否公布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不能把侦查程序完 全等同于审判程序。即使是侦查机关,也不适宜把案情全部公布。”陈卫东说,侦查机关有时还需要秘密的侦查,如果律师不受限制地向外发布信息,可能会影响侦 查机关的侦查。
这其实是公众知情权和侦查保密权的冲突。陈卫东认为,为解决这种冲突,控辩双方都需考虑这几点:“不妨碍侦查、不泄露案情、不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他也指出,在邓玉娇案中,律师公布性侵犯情节,不涉及这几方面的内容,所以没问题。
大案要案的律师为何总遭“解雇”?
关键证据损毁后,巴东局势出现了明显变化。5月23日,巴东政府发布新闻,称张树梅声明解除与律师的委托关系,此时张树梅尚未决定。下午4点,张致电夏解除委托关系。两天后,巴东政府再次发布新闻,宣布张树梅另聘湖北籍律师。
陈卫东对该现象的总结是:和杨佳案如出一辙。法院认为杨佳不接受北京律师,接受上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决定的。然而该案律师是上海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遂 使公众怀疑律师成了政府工具。“这些案子都有一共同的规律,就是北京律师不受欢迎。”陈卫东分析认为,本地律师在辩护策略方面,会受到当地政府意向的左 右。而外地律师尤其是北京律师不可控因素很强。
因为行政权的干预,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出现高度信任危机,中途被意外“解雇”,这是严重侵犯辩方程序权利的行为。清华大学副教授易延友认为,出现这些情况的 原因是惯常的行政思维在作怪,“某些官员想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完全排斥跟他们不属于同一条道路的律师和媒体。他会天然地认为,这些人是不可靠的,不可 掌控的”。
易延友认为邓玉娇案的程序有问题,“他们对实体的处理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妥当的,就是放在美国法院,可能也是这样的结果。但有一个问题是,实体正义是不 容易看见的,而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如果未按程序做,即使是实体没问题,都会让人生疑”,“会有一种放大的不公正感”。
易延友指出,在中国,刑事案件一旦成为公共事件,都不是在诉讼架构中运行,法律规定控辩双方权利对等、控审分离,都被虚置,“刑诉法一旦遇到大案要案,往往就被政府的行动架空”。
易延友认为,漠视程序权利是中国司法的严重问题。如果遇到一个善良的、开明的领导,或者受民意的压力,可能会在实体上实现正义。但这样做永远都只是个案和偶然。而且,政府这样做尝到甜头后,会不断重复该行为模式,这样对制度建构的破坏力非常大。
故而,受访学者均期望,邓玉娇案后,公众与政府均能更重视程序正义,“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