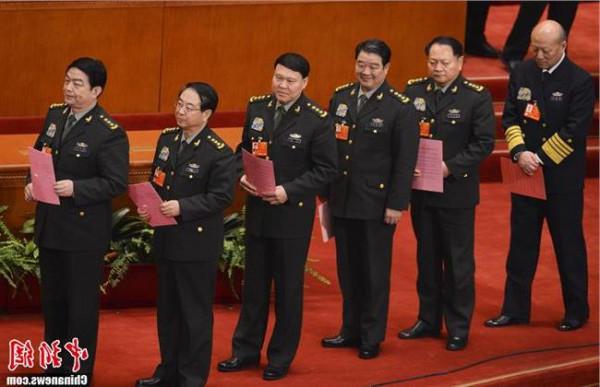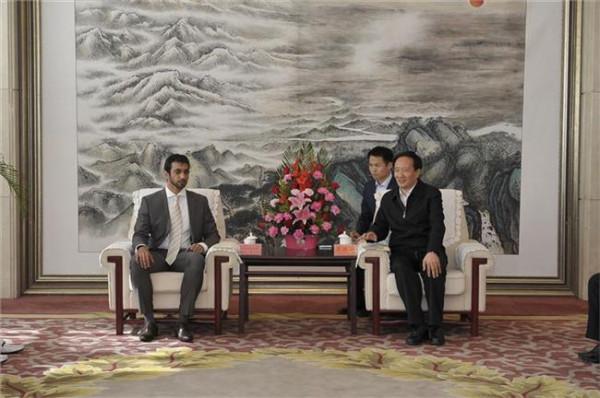赵汀阳共在存在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
本文试图表达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共在存在论”。它是一个中西混合理论,尤其发展了儒家和道家的有关哲学观念。它力求对存在的基础问题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并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提供哲学基础。
1.给不同世界不同的存在论
哲学一直没有给人的生活世界准备一个与之相配的存在论。一般存在论是为科学世界以及逻辑世界准备的,它不适合解释人的存在方式。一般存在论研究存在以及何物存在,这些问题在生活世界中并不重要。比如,在生活中,人存在( is),这不是困惑;人被做成什么样的存在(made to be),这才是问题。
在生活世界中,人不是一个预先完成的概念,而是一个可选择的概念。人是一种自相关的存在,人的存在即生活,人选择生活就是选择存在方式,选择存在方式就是创作自身。人的存在因其自相关性而不确定和不可测,因此人的存在有了命运问题。
命运之不可测,不是指自然的偶然性,而是指人为的创造性和自由度。命运由人们所做之事所定义,事可成也可不成;命运不是自己能够独自完成的,而必定与他人有关,因此,命运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就是命运之所在。
人的存在不是一种自在存在,而是互动存在;人的互动是创造性的,互动关系创造了一个仅仅属于人的世界,一个存在于互动关系之中的世界,一个不同于物的世界(world of things)的事的世界(world of facts)。
2.事与物
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事(fact)而不是物(thing),哲学不能“向物而思”(to the things)而只能“因事而思”(from the facts)。如果说科学是关于物的世界的解释,那么哲学是关于事的世界的思想。
当说某物是如此这般时,关于某物性质的断言限定了某物而把它封闭了起来。这种封闭性有助于获得关于某物的确定知识,但其中未见关于物的思想,思想已终结于其封闭性。物的形而上学把一切存在都看成有着既定本质的封闭个体,个体物或个体人,诸如此类。
物的形而上学中可明确定义的个体对于逻辑和科学是必要的假设,但这种假设不适合哲学问题,因为哲学问题与物无关而关乎事。哲学需要一种事的形而上学。事是人在生活中的有意行为,物只是在事中出场的各种实在。
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物的自身存在不可能自己选择别样的存在方式,因而也就没有制造出哲学问题。所以说,关于物没有思想问题而只有知识问题,物可知之而不可思之。
物只是知识对象,事才是思想对象,因为给思想造成问题的是事而不是物。如果问:这个物是什么样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如果问:这个物有什么价值,这其实不是在追问物,而是在追问涉及此物之事。只有当物进入事中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物进入事中,物的自身存在(being)就成为在事中的在场存在(existence);物因事而被赋予了在其自身之外的价值,价值就是物被卷入事的方式。
事乃有意所为,事的存在( is)同时必是“意在”(means to be),或者说,事总是因意而在(tobemeant to be),意至而有事,造事而生问题。事是人做的,人必须对人所创造的事情和问题负责任。关于事的问题就是关于人要创造什么存在的问题。
3.事的世界的创世问题
心是自由的,自由就要出事。人做事意味着人有着超越必然的自由,事包含着人的自由所能制造的所有麻烦以及所有困惑,自由是使存在产生问题的原因。自然而然的存在必然如此这般,既然是必然的,就不需要我们替它构思,无须构思就没有思想问题,所以哲学问题与“就这样存在”(to be asit is)无关,而与“就不这样存在”(to be as it is not)有关。
换句话说,如果说物是自然而然的(to be as it is),那么,自由就是能让事不是这样的(to be as it is not)。
能够“不是这样的”意味着是什么样取决于做成什么样。在这里,存在论问题由“是”(to be)转变成“做”(to do)。
相对于物的存在,做事都是创造。这一区别意味着,既然物的世界是必然的既定存在,物的世界的创世问题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存在论问题。于是,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都是后创世问题,我们只问何物存在,而不问何物应在。
而事的世界是人的创造,而且一直在创造的过程中,甚至不可能完工。其证据是,事的世界———由生活定义的世界———没有普遍必然规律。因此,事的世界的存在论就无法回避创世问题,而且创世问题是事的世界之核心问题。“是”(to be)和“做”(to do)的同一性说明事的世界的存在和创造是同一个问题。
4.“是”就是“做”(to be is to do)
一般存在论的存在概念不足以表达事的自由性、创造性和历史性,所以不能表达事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单纯的存在只是时间性的持续,没有历史也无所谓未来。这样的存在概念对于物的世界或许合适,但对于事的世界就缺乏表达力。
做事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人有历史有未来。未来不是现实的单调延续,而是事的预先概念:对于人的存在,未来先于现实,现实是实现了的未来或是破产的未来;甚至,未来先于历史,历史是根据未来的概念而不断重新书写的。
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存在不是“如其自然”(to be as it is)的一般存在论问题,也不是“如见所现”(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的一般知识论问题;人的存在是一个制造存在的问题。
“是”(to be)向“做”(to do)的转化揭示了存在论(ontology)所隐含的道义学(deontology)问题,但这不是以伦理学去取消存在论,而是说,伦理学问题与存在论问题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形而上学一致性。
在通常意义上,应在(ought to be)和存在(to be)是两个不能还原的问题,就像平行线不相交,但在事的世界这个不寻常语境中,人必须决定何事存在,于是,存在变成了应在的结果。
这是以何种价值去做事的创世问题,是一个道义化存在论(deontological ontology)的问题。存在的责任问题的典型表现就是莎士比亚问题“存在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人必须决定让某事存在或不存在;甚至决定让某一个事的世界存在或不存在,在此抉择面前,价值问题与存在问题交汇成为一个问题。
5.“我做故我在”(facio ergo sum)
笛卡尔谓“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胡塞尔进一步证明“我思其所思”(ego cogito cogi-tatum qua cogitatum)而建立了意识的对象结构。但我思只能说明关于世界的知识图景的根据,却不能说明事的世界的创造和运作。
知识图景是我思以自身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事的世界却是互动行为形成的,多边互动问题显然不能还原为思的问题。简单地说,我思解释不了事的世界,我思管不了事的世界。
既然我思没有解释生活也不能解释生活,因此就需要另一个形而上学原则来建立关于事的世界的分析框架。既然“是”(to be)落实为“做”(to do),那么我们寻找的原则就是:我做故我在(facio ergo sum或I do therefore I am)。
“是”(to be)落实为“做”(to do)是“是”的人化。做事使存在变成一个价值事实而不仅是自然事件,人的存在也因此成为具有价值的存在。我思是孤独的,而我做创造了人际关系和互动行为。存在的意义必定在存在之外;我的存在所以制造了意义,就在于我做的事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关系,把他人变成在我的事中的存在,而正是他人担保和证明了我所做的事的意义。
因此,我做不仅创造了我在,同时还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共在,而共在关系创造了事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做故我在”不仅是主体的存在论原则,而且是事的世界的存在论原则。
每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先于共在而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共在之前,我只是一个自然存在而尚未成为一个价值存在。我思也许先验地拥有世界的概念,但我思不可能为我创造一个真实世界,因此我思只是想象了世界而并不拥有世界,我仍然无处可在。
在我创造共在关系而实质性地创造了事的世界之前,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虚在;即使有着完美的我思,我仍然没有世界而一无所有。只有当所做之事将我与他人化为共在之时,我才在共在中获得一席之地,我才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成为在场存在。
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强调做人所暗含的深刻含义:人不在自然意义上“是”人,而必须在“做”中实现为人,而做事就是与人共在。因此,“我做故我在”蕴含着我与人共在而存在。
人本身没有存在论目的,人的存在意义是无着落的;这个问题在存在论中无法解决而成为一个釜底抽薪的隐患。神学目的论是一种替代性的解决,它试图以神意去解释人的的。但神学解释有一个缺点:它证明的其实是神的意义而不是人的意义;人是依附性的因此缺乏自足意义,而缺乏自足意义终究还是无意义。
人必须能够在人那里证明人的意义,这才是完美的解决———孔子把存在的价值论证限制为人间的在世证明,这是精明的选择。人自身虽不能自证其目的,却能在做事中创造目的;人在做事中请入他人而互相作证。
人不是因为自身有意义才做事,而是因为做事才有了意义;做事所创造的共在关系使每个人的存在意义获得互相印证,而互相印证的循环性表明了人的意义内在于生活的在世绝对性。
6.关系、奇迹和幸福
事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事,而事的内在结构是人的关系,不同的事情意味着不同性质的关系。由各种可能关系所表达的事具有无限变化而决定了事的世界的创造性。中国哲学聚焦于事的可变性(易)而不是物的确定性,这一方法论对于事的形而上学非常重要。
一般存在论假定,一个存在的本质是这个存在本身确定不变的性质,而关系只不过是存在的外在联系,比如说,给定x、y,那么由x、y的既定性质可以定义其关系R。这样的存在论可以解释物的世界,却不能解释事的世界。
在事的世界中,关系是可选择的,只有选择了某种关系才能确定其相关存在具有什么意义。在被纳入关系之前,一个存在及其本身的性质并不产生问题,不确定的动态互动关系才是形成问题和解决问题之所在。
一种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被卷入之存在的特殊意义,或者说,关系决定了相关存在的在场表现。因此,我们需要由关系去理解存在的在场表现,即从关系R去确定x、y的在场表现,在其中,关系掌握了主动权。很明显,事的世界与物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论问题。
研究规律与思考命运完全不同。规律是确定的和必然的,而命运是不确定的和创造性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是对奇迹和创造的否定;如果去掉了不确定性,就无所谓命运了。人有可能创造和修改命运;正因为命运是可变的,生活才有意义。
假如一切皆为天数,人谋无非徒劳,人就无事可做,也无事值得做,历史、成败、荣辱、善恶、爱恨、贵贱、幸福、自由、尊严等等就都失去意义。严格地说,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创造性的奇迹。自由是奇迹,道德是奇迹,幸福和爱更是奇迹,一切使生活具有光辉的事情都是奇迹。
当“是”(to be)化为“做”(to do)之时,奇迹就成为可能,而奇迹的秘密在于关系。如果人们以个体原则为准去计算利益和价值,冲突就是无解困境。
只有当人们能够以关系原则为准去理解利益和价值时,合作和幸福才成为可能。人们难以合作的原因与其说是自私,不如说是愚蠢: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私最大化不等于利己最大化。最大最重的利益和幸福是无法独占的。幸福的不可独占性颠覆了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同时证明了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
以个体原则为准的存在方式必定陷入事与愿违的困境:自私最大化却达不到幸福最大化,自私求福变成对幸福的否定。自私个体的痛苦、孤独、无助、失望、迷茫和受挫感等等“存在论”上的深刻不幸,都是因为个体原则拒绝了幸福。
当哲学对幸福问题束手无策时,人们就求助于宗教。宗教许诺在另一个世界里给人们幸福。这虽有安慰作用,但彼岸世界永不在场的虚幻性却是一个画饼充饥式的困难。彼岸世界与真实世界无法兑换,生死之间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存在论鸿沟。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而非一个概念上可能的世界。尽管贝克莱相信上帝感知一切可能世界而使万物存在,但那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