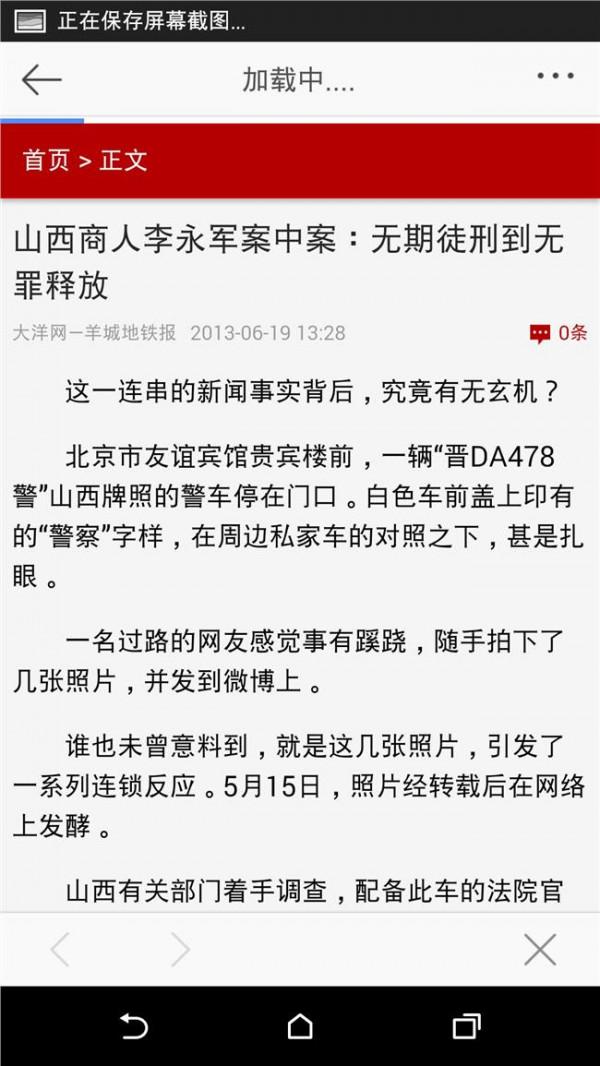北京画店黄永厚 张瑞田:忆黄永厚
20年前,是春天,陪伴儿子到北京参加艺考的颜家文问我:知道黄永厚吗?我点点头。他又说:他住通州,明天去看他,一同去吧。我又点点头。
那时我在北京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工作,外景拍好,正剪片子,不忙。闲时看书写字,访朋拜友,颜家文邀请,自然乐于结伴同行。黄永厚住通州梨园,两套房子,一套居住,一套画画,不奢华,却也宽敞、适中。与颜家文进了客厅,坐下,客套几句,就无话不说了。

趁颜家文与黄永厚聊天之际,我看了看黄永厚的客厅,沙发背后,是儿子黄河的书法,画案的左侧,是刘海粟的行书:大丈夫从不流俗。黄永厚的画案让我好奇,画案站着一摞摞书籍,其它的地方是凌乱的报纸,画画用的颜料,笔筒,印章,寂寥地靠在一边,似乎画案不是它们的主场。

黄永厚穿一件淡灰色夹克和一条暗格蓝色西裤,语速极快,不仔细听,如在雾中。黄永厚个子矮小,动作敏捷,肤色白皙,嘴边有一个不浅不深酒窝,笑起来阳光灿烂。
那一年黄永厚70岁,步履、谈吐、表情、思维出奇地年轻,应验了小个子长寿的推断。与黄永厚谈画,他知道我不在行,只是浮皮潦草地说了几句徐渭、八大、石涛、渐江、虚谷什么的,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颜家文说我写字,黄永厚的眼睛亮了,又同我说了一阵子文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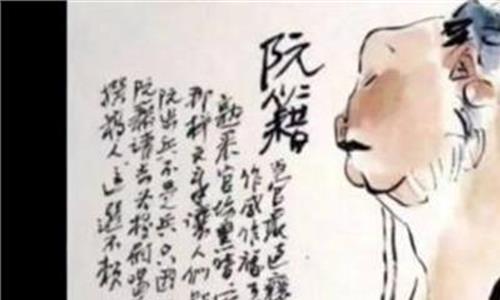
谈着谈着,他忽地站起来,有一点秋天扫落叶一样把画案清理出一块空场,抻过一张六尺宣纸,写下了清人宋湘的联句:直将羲颉开天意,横写云霄最上头。落款的时候,他回过头,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他就在上联的右上角写下了“瑞田惠存”,又在下联写上他的名字,钤印送我。

我当然高兴,但也觉得突然,没有精神准备。一位长者,又是饮誉画坛的名家,写字相送,激动也感动。
放下毛笔的黄永厚拿出他的画作让我看,画幅不大,有斗方、四尺三裁大小的画,画人物,画静物,精巧、生动。尤其耀眼的,是画上的跋语,言辞优美,语义深挚,书法亦行亦草,张弛有度,节奏感强,与所描绘的景物相映成趣。我翻阅黄永厚画作的手有一点抖了,我看到了黄永厚画作的深处,也掂量出黄永厚画作的分量。我简单讲了看画的体会,黄永厚笑起来。
黄永厚留饭,筵席上,谈到湘西、沈从文,以及黄永厚的大哥黄永玉,挺投缘的。
从通州回海淀的路上,我对颜家文说:“我喜欢黄永厚,他深刻。”但我没说谁浅薄。对湘西的了解,对湘西文化老人的靠近,颜家文是领路人。时任《芙蓉》文学杂志主编的颜家文也是湘西土家族人,应该说,他与黄氏兄弟是一家的。
几年以后,我在北京买到一本黄永厚的画文集《头衔一字集》,放到书包里,走到那里,看到那里。《头衔一字集》的“后记”是伍立杨的《生命、生机,活法、活力——主客纵谈黄永厚》,其中写道:“他是黄埔军校二十一期的高材生,他的绘画天才,在那时就泉涌而出了。
那时的军校学生,很多是从别的大学一、二年级转来,基础相当优良。因世运突变,有的去了海峡对岸,有的起义在刘伯承、陈赓部队服役。几十年后,那些人早已经是中将以上的退役将领了。
我们的老先生虽然离开了部队,彻底‘解甲归田’那只是气蕴风云、身负日月的质地改变了流向:倘若我们也仿照古人来个‘乾嘉诗坛点将录”“光宣诗坛点将录”,凭了他的随心所欲,自成宗派,谁说老先生不是文人画一百零八将之‘都头领’呢?谁说他不是画坛一言九鼎的‘五虎上将’呢?他的画一动笔便不期然而然地携带儒家仁民爱物的气度,道家物我相忘的襟抱和释氏慈悲为本的情怀。”
我是一步一步走近黄永厚的。颜家文的引领是第一步,伍立杨的文学绍介是第二步。在伍立杨的文章中,我隐约看清了叫黄永厚的老人,不仅仅是拿毛笔画画的人,他曾在军中行走,还写得一手上好的文章——“他的文章同样能镇住内行。且看他在《工商时报》《中国经济时报》《书屋》杂志等处所开的专栏,文笔跳荡奇突,无往不收,无垂不缩,调控驾驭,如臂使指,‘艺高人胆大’,端的是叫人欲罢不能。”
在我的阅读史上,《头衔一字集》有特殊的地位。读书明智、识理,作者可以缺位。但,读《头衔一字集》不行,内容不论,那个性鲜明的人格力量,分明来自那位个子矮小、性格开朗、思想深刻、忧国忧民的画家、文人黄永厚。
《头衔一字集》让我感受到作者的博览群书。赵本家透露,黄永厚在上海办画展,一位花鸟画家不解地问:这是中国画吗?著名画家朱屺瞻听到质问,便说:“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过了,要读很多书,还要有自己的见解,我也读过许多书,画不出这种画。”
我喜欢《头衔一字集》中哪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败兆》《下台之后》《顾准审西门庆》《开卷考官》《吮舔擂台》等作品,以笔为刀,剖析假大空的时风和溜须拍马的习气,防腐反腐,弘扬社会正气,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糟粕,理解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电话里向黄永厚谈了我读《头衔一字集》的体会,他依然爽快地说:你来吧,我刚出一本画集,送你。我去了,他把《黄永厚画集》送我,画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八开,收录了黄永厚两百余幅画作。与他此前出版的著作不同,《黄永厚画集》的序言是他的大哥黄永玉所写,当然写的好,其中的“‘幽姿不入少年场’自然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慕为人了解”的评价,极其准确,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实的黄永厚。
对于大哥,黄永厚尊敬,但不趋附、迎合,他是他,自己是自己。
那一天,一家出版机构计划出版一本黄永厚的随笔集,要求他请哥哥题字,他委婉谢绝了,他不愿意让哥哥来为自己的事情“操心”。我还劝他,请哥哥题字有什么。他摆摆头,又摆摆头。
21世纪初,颜家文退休,到北京居住。来往的机会多,去黄永厚的家也频繁了。过春节去拜年,黄永厚回赠的礼物是小幅生肖画,鸡年来给鸡,猴年来送猴,笑呵呵的老人,真诚、质朴,特别生活化。看他画画,少不了一泻千里的跋语,他常说:中国画没有跋不行。
他在《关于中国画的实践和一点感想——就〈冰炭同炉〉答友人》一文里说明白了跋语的意义:“‘中国画’最大的传统是什么?是看不见荒诞,也不承认荒诞,只有莺歌燕舞。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里讨生活、甚至还想讨封赏,不封闭自己的视听、不摈弃良知能得几人?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作品,必然训练出什么样的鉴赏家。”
这时,他和陈四益在《读书》杂志开设的“画说·说画”专栏与读者见面,在知识中体察真理,在幽默中调侃猥琐,在画面上挖掘诗意,在文字里体悟理想。这时,我们看到了黄永厚文人画家、哲人画家的一面。
逐期、逐篇、逐幅,读《读书》,读陈四益,读黄永厚。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画中有文,文中有画。看久了,就觉得黄永厚用画笔思想,陈四益以文字当刀,自然是‘思想’给力,‘刀刀’见血。刺世讽俗,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惜物质利益所惑,当下文人、画家争相恐后当工具,帮腔或合谋,没有一点读书人的风骨了。
”去看黄永厚,免不了谈“画说·说画”,他告诉我,“三联书店”结集成册了,我说:给我一本呗。他停顿片刻,说:我只有一本,你喜欢,拿去。他找到《忽然想到——画说·说画》,在扉页上写“瑞田弟教正。黄永厚,2012、4、25,于通州”。
我转行当策展人,是傅雷和黄永厚的影响。读傅雷与黄宾虹的手札,我知道了1943年在上海举办的黄宾虹80诞辰纪念画展,我发现,展览馆是友谊的桥梁,也可以是思想的平台。与黄永厚相识,在他的画作中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同时明白了,用色彩描写世界的人,也会描写人心。
2007年,我与斯舜威共同策划了“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确定展览作者时,我想到了黄永厚。他是画家,也是作家,“胸中丘壑,深沉无比,于是神出鬼没,撒豆成兵。文章做到这个份上,无法不谓之‘妙到毫颠’。”伍立杨讲得再恰当不过了。以作家的身份参加一个同人展,希望有黄永厚。于是,我去通州梨园找他。
他愉快地答应了。我问:何时来取。他说:你等等。
黄永厚一边说话,一边走到画案前,铺上一块宣纸,提笔写了三个篆书“捉蒲团”,然后密密麻麻地写了下去——
“无地置跪草,放胆笑贞观。辛酉冬获梦麟书,云欲归庐,而为奔走,不果,举措茫然,愧对梁汾,因作是图寄梦麟,梦麟复诗《毋渡河》,数为涕塞,不忍卒读,今更录之,志厚之不能也。
“痛哉梁汾屈膝处,生亦难,死亦难,菜根涩,布衣寒,平生意气犹轩轩,傲骨何曾向人屈,宁不痛哉,而今为我捉蒲团,有人金龟宝马能换酒,有人狂歌直上天子船。我公赤条条地一身之外无长物,更况是筋老皮厚不忍看,拼此躯因我折,痛甚至哉,登楼狂笑枉槌栏,我读永厚画,气尚温,肠已断,乌头马角总是幻,铜山铁券不值故人一片丹,山阳惨笛岂忍听,飞霜不击雪漫漫。
休,休,君毋渡河,毋渡河,君勿捉蒲团,令我摧心肝,丈夫膝下有黄金,文章得失岂由天,三更拍枕频惊起,似闻鬼哭心倒悬,宁古塔前倒身拜,雨霰似泪迸江南。黄永厚书。”
书毕,他看了看,在左下角画了一个写意古人,应该是顾贞观吧。
黄永厚写完,问:可以吗?我的心情有点沉重,虽然他没有介绍书写的内容,但我知道这段散札的典故和深意。我还能说什么?
此话长了。文革后期,陈梦麟看到黄永厚的画作《石虎行》,觉得这是赞扬邓小平的画作,作诗咏赞。黄永厚看到陈梦麟的诗,有觅到知音的感觉,二人手札往还,不亦说乎。“四人帮”被打倒,陈梦麟希望当局平反自己在文革中的冤屈,他寄希望黄永厚的哥哥黄永玉帮助。
然后,他致函黄永厚,说明情况。不久,陈梦麟收到黄永厚的一幅画,中间是垂首的顾贞观,拿着一个蒲团,一脸无奈的样子。画作的名称就是《捉蒲团》,下面是一行字:无地置跪草,放胆笑贞观。
无地置跪草,放胆笑贞观,什么意思?陈梦麟毕业于浙江大学,古典文学修养深厚,他看到黄永厚的画,思绪回到了清代。清初诗人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获罪,被流放宁古塔。他的好朋友顾贞观知道吴兆骞的冤屈,到处求人,欲救吴兆骞于苦海。
他认识了纳兰性德,这位刚刚考上进士的词人,也重情义。抓一个人易,救一个人难,纳兰性德也一筹莫展。时间过去了18年,顾贞观念念不忘,他到纳兰性德的家里,跪下求情。纳兰性德小顾贞观17岁,深为他的忠义感动,答应敦请父亲明珠出面。
然后,在顾贞观下跪的地方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梁汾屈膝处”,以记录顾贞观的德行。梁汾,是顾贞观的字。在纳兰性德的努力下,吴兆骞回到北京,在纳兰性德的家里看到“梁汾屈膝处”,泪流满面,哽咽难言。
黄永厚不是不帮忙,是没有力量,置放跪草的地方都找不到,何谈找到纳兰性德一样的王公贵族。黄永厚是自嘲,也是安慰。陈梦麟懂了,他填词《毋渡河》以赠,表达自己的感念之情。
黄永厚以浓情厚意所写的手札,堪称杰作。
“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在北京、杭州、石家庄、深圳、东莞、砚台、大连等地巡展,黄永厚的手札会放到重要位置,我导展,都会喋喋不休地绍介黄永厚,绍介陈梦麟和《毋渡河》,当然,也要绍介吴兆骞、顾贞观、纳兰性德。历史中的舍命救友和现实中的真诚慨叹,是中国文人正义感的直观体现,是知识阶层对人性与良知的精神书写。
愿意临帖、写字,那是2012年的秋天,我用隶书抄写了顾贞观给吴兆骞的词作,拿给黄永厚指教。他看得非常认真,一字一句读起来:“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我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繙行戌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读完,黄永厚叹了一口气,说:“顾贞观这样的人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