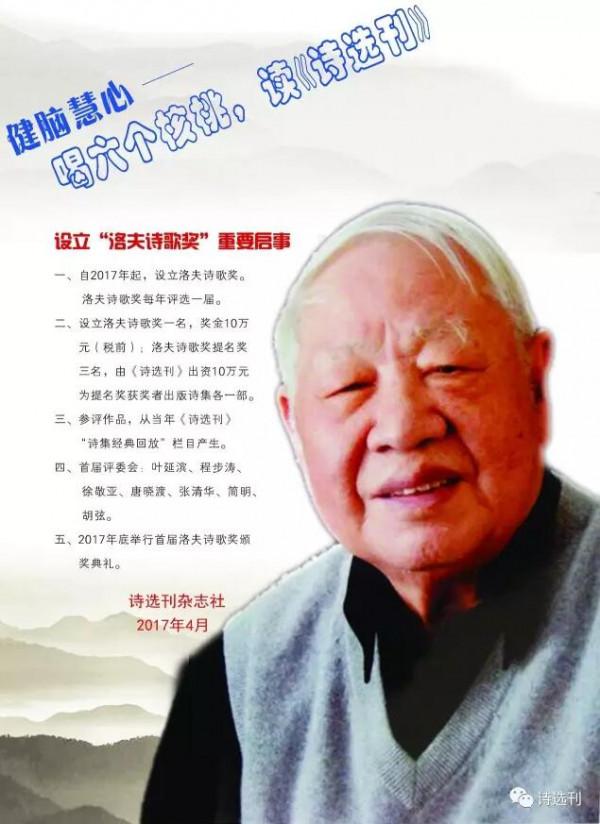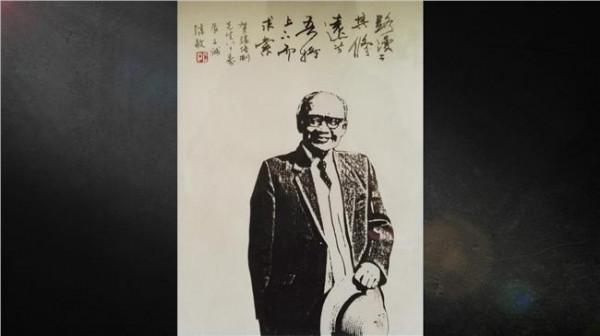张枣诗选 第三届张枣诗歌奖获奖者杨子诗选
第三届张枣诗歌奖获奖者作品 杨子诗选 杨子,1963年生于安徽,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居广州。 评语: 杨子以他的激情并以他尖锐的呼喊与这个古老帝国的现代文明紧张地对峙着——在工业崛起的城市与礼俗没落的乡村之间——他企图以"火焰般的诗歌"来拯救遭受科学、物质、利润等多重现代性因素挤压下的孱弱灵魂。
其敏锐的体验、无望的绝叫、宏大的悲悯及鲜明的表现性风格,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诗歌写作潮流中,独树一帜,并彰显了永恒的人道主义价值。
因此,我们决定将第三届张枣诗歌奖授予他。 灰眼睛 蓝色的乌鸦,在穷人的天井里歌唱, 雨,在瞎子的灰眼睛里闪光, 铁锤把虚空敲响。
如果一只燕子称得上春天, 如果整个大海是某人的一滴泪。 风啊,把女孩压抑的蓝布衫掀起来吧, 让世界看看 她们有着多么无辜的肉体, 多么无辜的欲望! 1995 撒在哑巴舌头上的盐 黄昏,那些被大风刮得东倒西歪的树 像一群悲痛的哑巴打着奇异的手语。
河流在我们头顶轰响, 四周的建筑像魔鬼的旅店, 等着我们投宿。 越来越黑了。 我睁大了眼睛, 徒然地要辨认出 大地上种种乖戾的细节。
河流轰响但是看不到流水。 鱼的喊叫越来越微弱。 在更深的黑暗中, 一扇铁门缓缓关上。 远方闪烁的星星, 撒在哑巴舌头上的盐。 1995 这地方已经一文不值 这地方已经一文不值。 水泥厂,加油站,阴影带着可疑的气味压住一亩一亩冬麦。
土地,被遗弃的母亲,吃了太多农药,脸色蜡黄。 光秃秃的小树林里, 斑鸠的叫声,仿佛临终呼喊, 令人胆寒的虚幻。 风暖了。空气中淡淡的氨 是这个农业国度最后的一点点气味。
一头猪冷漠地跟在汽车后边,走进傲慢的城市。 唉,命运终于给了严峻的安排—— 当思乡的斑鸠从光秃秃的小树林飞走, 它揪心的叫声会让一亩一亩冬麦因悲痛而生锈,死掉。 1996 霜花 饥饿喂养了四周的黑暗。
我们的饥饿, 正义的饥饿。 形同鬼魅的树 转眼就会扑过来, 把我们不爱的果实 硬塞进我们的喉咙。 窗玻璃上的霜花 太美了, 仿佛在诱惑我们 去死。 太美了, 深渊般的天空, 我会从爱人胸前爬起来, 纵身扑进你的怀抱。
1997 胭脂 车过广州大桥时, 我瞥了一眼身边的孕妇 和窗外死去的河流。 一个清洁工 在打捞河上漂浮的垃圾, 像是给死者整容。 他们在城北建造意大利风格的建筑, 他们在城南种上非洲棕榈, 草坪也做好了,种籽是德国的。
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啊, 八百万人做着一模一样的梦: 钱,钱,钱! 而钱不过是抹在 他们死去的生活上的 胭脂。 2000 卡在喉咙里的刺 今夜,谁在村里走走停停, 望着失魂的母鸡和冰冷的烟囱, 想到父亲的命运,自己的命运,热泪盈眶? 今夜,谁穿过麦地和祖坟, 两手空空,像个幽灵, 不敢让人看见? 奇异的光环在寒酸的屋顶升起。
田野,池塘,仿佛被恶意罩住。
哦,连鬼火都不光顾这片土地! 祖国!你是他们的尴尬, 你让他们排了那么长的队, 领取贫穷和羞愧! 在夜色中闪光, 穷人的牙齿, 穷人鼓胀的肚子。 他到家了,无人迎接, 他走进漆黑的屋子, 像孤魂野鬼。
池塘闪着蓝色的寒光, 和他一起钻进冰冷被窝的 只有压低的啜泣。 你在他喉咙里,祖国! 你是卡在他喉咙里的一根刺, 让他从头到脚那么难受! 2000 死月亮 在堕落的人世上方, 在银行大厦的尖顶, 月亮又来了, 神情哀伤。
再也没有人向它投去深情的一瞥了。 在金碧辉煌的工业制品中, 它普通得像一个肮脏的足球, 一张相貌平平的女招待的脸。 我们回忆起早年的激动, 回忆起颤栗的爱情 曾被它镀上银质的光辉, 竟然有些懊悔。
不再有神经的悸动, 不再按它暧昧的指令行事, 不再受它刺激,分泌出伟大而愚蠢的冲动, 在这个月亮最受崇拜的国度,月亮已经死灭了。 2001 契诃夫书信 (1890.
6.29 致妹妹) "我正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 这里的苍蝇很大, 这里为了一丁点事 就会人头落地。 白天,野羊游过黑龙江, 夜里,荧光闪闪的昆虫 在我们的船舱里飞。 同船的契丹人宋路理 整夜都在说梦话。
吸了太多鸦片,他醉了。 早晨他开始吟诵扇面上的诗。" 2001 从地下穿过天安门 谁都不知道,这飘扬在空气中 飘进我们眼睛 吸进我们鼻孔和嘴巴的尘埃 是谁的尸灰。 在首都地铁里, 一股凉风灌进我脖子。
车厢很明亮, 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小姑娘坐在我对面, 放肆地调情。 当我从地下穿过天安门的时候, 我对它没有任何感觉, 我对天空细小的尸灰没有任何感觉, 我对我的生和死没有任何感觉, 我对千千万万人的生和死没有任何感觉, 只感到那股凉风,还在固执地往我脖子里灌, 只听到车轮催命鬼般急促的敲打。
2001 小教堂 现在我能够平静地对待他们的死亡了? 很多时候,我一点也想不起他们,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彻底离开? 但只要有一分钟想起他们, 想起他们的脸,他们的笑,他们的愁容, 他们的眼泪就会比别的眼泪巨大, 他们的笑容就会比阳光灿烂。
他们的肉身毁灭五年,十年, 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变成什么? 我并没有被亲人的死亡教导成更好的人, 反倒成了刻薄的,忘恩负义的家伙。
唉,我需要一个小教堂, 一个从未被不洁的脚踏入的小教堂, 去对着他们的笑容和泪水忏悔, 去挖出压在心中的悲愤的石头, 在冷酷的冰雪中浸洗我那一刻也没停止放纵的肉身, 把我迁徙到一个我能认清自己的地方。
2002 两座教堂一座寺庙 八百万人口的大城, 只有两座教堂一座寺庙 供人下跪,忏悔,以泪洗面。 几百间药店,成群结队的医生 有什么用呢? 谁来诊治灵魂的感冒,咳嗽和坏血病呢? 2003 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 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 古怪的气味 阴郁的眼神 无论怎样转身 都会遇见。
公共汽车从我们头顶驶过, 一堆抽搐的废铁。
燕子紧贴大街飞行,预示着暴雨将至。 已经发生过很多揪心的事了, 谁也不来过问, 我们重金聘请的博学之士也无能为力。 这么多的头漂在肮脏的日光中, 这么多的忧虑堵在喉咙里, 这么多的失望,这么多的呼喊, 这么多炉渣一样失去了光彩的眼睛…… 有人把失败藏起来了, 有人把宣判藏起来了, 但那预兆清晰地印在人们的额头上, 就像妇女脸上的雀斑, 就像囚犯脸上的刺青。
恍惚中,你看见摩天大楼广告牌上的美女 换成巨大的"死"字。 握在一起的手多么无助, 碰在一起的目光多么无辜, 拥抱在一起的身体 冰一样冒着冷气!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组织站出来说 是我们的罪过。
没有一个博学之士站出来说 总会有办法。 没有一只燕子带领我们去见识玫瑰下边的腐烂。 药片从嘴边落到地上。 喝下去的饮料像是有毒。 啊,那从每个人脸上掠过的 仿佛中了邪的眼神!
我们向谁提出我们的诉讼? 我们向哪个法官展示肉体上看不见的伤痕和毒刺? 我们控告汽车业、美容业、交通业还是保险业? 我们踢广告,踢电视还是踢舌头抹了蜜糖的官员? 我们把自己叫做什么? 我们把我们疯狗般的生活叫做什么? 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
他们都有一个身份, 纨绔子弟,傍大款的美女,公交车上的小偷,天桥下的拾荒者, 法律顾问,营养专家,家庭主妇,化妆品和春药推销员, 地下通道里的流浪歌手,古典音乐、女权运动和长跑爱好者, 警察,司机,清道夫,士多店老板, 他们都有一张脸,一个口音,和一些癖好,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活在哪个朝代, 所有的人, 衣衫褴褛者和西装革履者 大腹便便者和骨瘦如柴者 滔滔不绝者和沉默寡言者 狼吞虎咽者和素食主义者 全都那么惊慌,那么失色, 他们对着镜子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对着亲人说不出斩钉截铁的誓言。
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 这荒凉落在他们口腔里, 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淤泥和死尸的气味, 这气味像他们的集体签名, 这胆怯的抗议 被他们咽进肚子…… 2003 蠢城 这蠢城,正忙于用一幢刺破青天的摩天大厦,用五百家银行,一万家夜总会,八百万沉默的 劳动者,书写它的自传。
一个心脏里卡着电钻的庞然大物, 它亢奋的震颤惊吓了少女和老人,惊吓了夜鸟和游鱼。 一个一年四季都被挖掘机开膛剖腹的怪物,一个卓越的受虐狂, 一个额头和脚趾安装了探照灯照射夜空的白痴。
有人怀疑市政工程总指挥脑子里有屎,否则交通不会混乱十年,二十年,看样子还要混乱 一百年。 他没看到,总指挥脑子里有一部飞快运行的计算机,闪着祖母绿色的荧光。
那些小头目也 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部飞快运行的计算机,闪着祖母绿色的荧光。 这蠢城,用金粉银粉化了妆,要去参加国际愚蠢大赛并且发出指令让少女夹道欢送。遗 憾憾的是它那截露在礼服外边的尾巴,被我们看到了。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