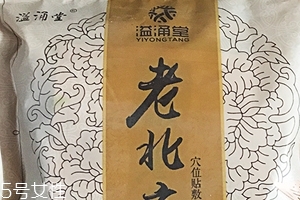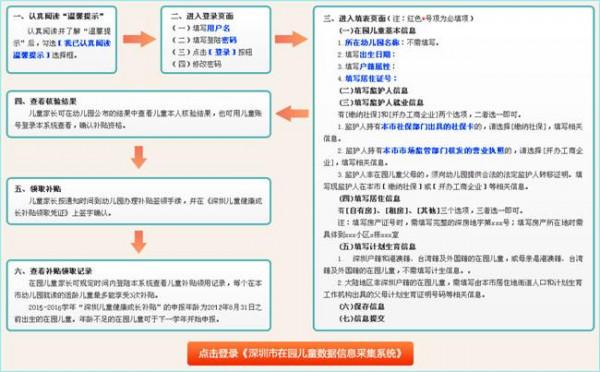傅国涌:神化特权今犹在 傅国涌:“神化”“特权”今犹在
2月19日,得知戴煌先生在北京去世的那天,我正好看到一本纸已发黄的旧书,其中有一篇1957年8月7日新华社批判戴煌的文字,这则三千多字的新闻,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刊登在次日的各大报纸上,让他足足承受了21年的劫难,他在回忆录《九死一生》中曾全文转录了这篇奇文,我其实早就看过,再次遇到,还是要重温一番。
他的“反党言行”首当其冲的是企图组织“**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新**”、“第三党”,目的是“消除干部和人民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所谓他要组织“**革命委员会”,是他妻子在新华社贴大字报揭发的,不过是夫妻之间的一句闲谈而已。有一次晚饭后,他多喝了两口酒,说起苏北家乡土皇帝、新恶霸横行,愤愤不平,随口说了一句:“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当时就遭妻子反驳。
他的另一“反党言行”是一封还没写完、更没有寄出的“万言书”,这封写给“毛**并党**委员会的同志们”的信是他自己主动交出,以明心迹的,不料又给对方送去了炮弹。他在信中提出“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他在6月13日的座谈会上提出了“神化和特权”问题,他认为各级领导自认为高于一切,把自己神化了,“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给予抑制与消除,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相隔近六十年,他当初的判断不仅已被历史所证明,也继续被今天的现实证明着。
我读过他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直面人生》等作品,更钦佩他为许多求告无门的弱者、冤沉海底的亡魂仗义执言的壮举,特别是他曾多年在河南被冤杀的农民曹海鑫呐喊,为高勤荣蒙冤入狱而呼号。对于饱受委屈的人他几乎怀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他也有独立思考的**惯,所思所想往往不从个人私利出发,而是忠实于他看到的真相,并尽其所能地揭示真相。
他之敢说真话,敢于直面人生,既与他的个性有关,也与他的品格有关,更与他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敬畏感有关。
1957年他因直言罹难,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笔。1978年之后,他回到新华社,重新拿起笔,他就开始为平反冤假错案奔走,为许多受屈的人抱不平,为恢复失落已久的正义执笔。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在不断地为正义呼喊。
1949年以后的一部中国新闻史,如果没有刘宾雁、戴煌这样的新闻记者,将会变得更加惨不忍睹。正是他们给这个不堪的时代保留了一点正气、生气和人气。拉开时间的距离,尤能显出其珍贵来。可以说,他们的新闻作品是党管新闻、舆论一律的夹缝里开出的花朵,透出了一点点人的气息,就因为他们保留了人的良心,敢于面对真实、书写真实。
与刘宾雁不同的是他侥幸没有被第二次逐出这个党。他们属于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者,从小追随**,成为**打江山的坚定基础。
在**坐江山的时代,无论是1957年,还是1978年以后的漫长时光中,他的良心与组织性或者说党性却不断地发生冲突,林昭1957年在北大校园提出的这个命题穿过长长的历史隧道,至今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戴煌无疑是一个良心胜过了党性的人,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员的戴煌,而是一条硬铮铮的汉子,一个活得坦荡、不苟且的人,一个以良心执笔的记者,注定要被留在新闻史上的名字。
虽然今天在八宝山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遗体覆盖着镰刀斧头的红色党旗。但他属于那种老派**人,虽然是在**的新闻队伍中成长起来,终身也没有抛弃少年时选择的共产主义理想,却有着人道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底色,对事实的尊重,对人类良心的守护最后成全了他。
在我看来,他所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还不是那有形的文字,而是透过他一生特别是后半生的作为所彰显出来的人格力量。在一个铜墙铁壁般的舆论控制国家里,他凭着勇气、正直和长久岁月形成的影响力,尽最大可能地发出正义的人的声音。
与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氛围显得格格不入,与这个唯上唯权、奴颜婢膝的主流新闻界更是形成了深刻的反差。他是红色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典范,说人话、写真相的典范,也许将来的人们会为对他身上的红色印记感到遗憾,但他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是从时代的风雨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的女儿对记者说,他晚年念兹在兹的是他最后写下的十万字文稿能否出版,内容是关于他这一代抱着共产主义信仰、参加革命的人,“当初的热情和热血、后来的反思与批判。
”
比他晚一辈的记者卢跃刚在《老战士戴煌》一文中指出,“从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纪实著述,从张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到深沉的批判现实主义,从宣传式的新闻写作到思考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大幅度转变,良知与认知,缺一不可。
” 期待那还没面世的文稿中看到他对这一转变心路的自述。这些年来,他和那一代历经风雨雕琢、有良心的老辈正在不断凋零,时代也在急速变化的途中,不变的是他们身上历久弥坚的精神和品格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怎样显赫的荣华和名声也不过是一堆粪土。
我与戴先生只见过一面,大约十几年前,在北京一个饭店里,《中学人文读本》座谈会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高大、白发、方正,尤其是豪爽,让我一点都没有陌生感,其实那天我们只是简单的交谈了几句,他读过我的一些文章,也不生分,临别时还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在以后的岁月里,偶尔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一开口“我是戴煌”,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亮堂,连笑声都是那样的明朗。在这个噩耗不断的早春写这篇文字时,我总是想起他在电话线那头的声音,我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戴煌先生洪钟般的声音将回响在未来的世代,揭示真相的力量不会随风飘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