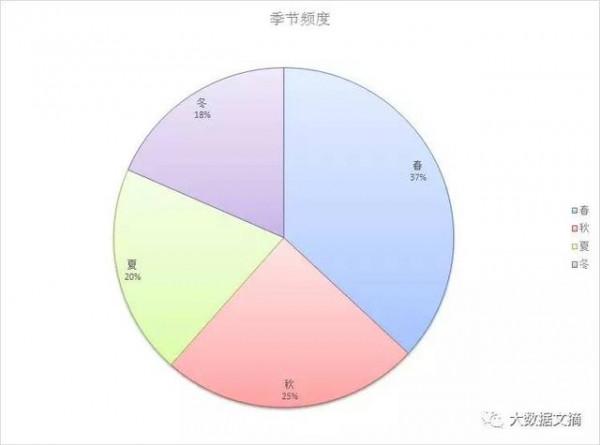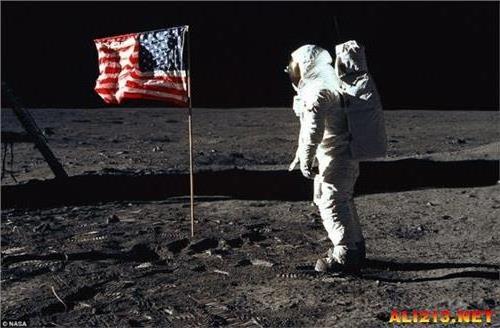绝黄伟文什么意思 如何理解「林夕领进门 皈依黄伟文」这句话?
灰常抱歉,我老是把《告别娑婆》记成林夕的词,实际上是林夕写了一首《逆苍生》(也很推荐,主题是探讨人类的权威的塑造与崇拜),然后小克有感而发,和了一首《告别婆娑》。
小克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词人,创作初期天天不是和林夕词就是和黄伟文词,大有郭老的风采~~~~

《告别娑婆》非常有林夕的风格,顿挫沉郁,探讨生命与轮回。小克还写给陈奕迅写过《张氏情歌》/《哎呀咿呀》,《床头床尾》,风格非常多变。我始终认为,倘若新近一代粤语词人还有人能达到甚至超越两个伟文的水平,那绝对不会是林若宁,一定是小克。
以及昨天六一儿童节突然想起Wyman的《青春常驻》,看张敬轩和谭玉瑛的剧场版,哭成狗。
----------------------------------------原谅我并不知道打分割线的正确方式----------------------------------------
高中的时候喜欢林夕,那时候林夕和王菲还是捆绑销售,陈奕迅还唱着我觉得这歌到底有什么意思的《十年》,林夕给我的印象是《笑忘书》《红豆》《美错》,这种真·缠绵悱恻的风格碰上年少多愁的浪漫幻想期是不是想想都中二得让人都醉了~
研究生的时候初识黄伟文,第一首歌是《痴情司》,惊艳无比,不知道有人写词写得能这么感人。同时,沉迷于粤语歌的我再也不能听林夕的国语词了,作为真爱粉真是每次看林夕写的国语词心中都狂冒无数弹幕。PS:你们不觉得林夕在国语歌里面很喜欢用“纪念碑”这个意向吗?每次在歌里听到简直尴尬症爆发,更尬尴的是林夕这个意向(还有其他一些很鲜明的用词风格)被他徒弟林若宁继承了,林若宁在整体作词素质上又差了一大截,于是经常形成尬尴的N次方现象……
嗯,就是忍不出吐槽的天性对不对?说回《痴情司》。
《痴情司》是一首为舞台《贾宝玉》剧创作的主题曲,但凡有点文学素养的人都看过《红楼梦》,然而黄伟文从!来!没!看!过!据说他是听了何韵诗花了四个小时给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然后写出的《痴情司》。而传说林夕是很爱《红楼梦》的,非常爱,笔名就是来自于“梦”这个字嘛。
林夕也写过以《红楼梦》元素为素材的歌,还泪、赎罪、大观园什么的,但是没有一首能与《痴情司》相提并论。何以一个对《红楼梦》有大爱有研究的人却反而不及一个听了四个小时故事的门外汉?特别是在两者的文字素养与感受力天赋差不多的前提下?
性格。
如果你看得多黄伟文的词,你会发现黄伟文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纯真。你从《黄色大门》看到绚烂童话“窗纱外,小鹿给我送枝花,梳化上,下凡天使共我喝著茶”;你从《青春常驻》看到清澈的童真“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矢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你从《薄情歌》看一个过气宝宝的委屈“我有唱错了什么?至会拆散你和我,还是传说里听者薄情的说法不错?”——宝宝好心塞你们都不喜欢我了是不是!
黄伟文始终保有一个孩童的心,他的哭、他的笑、他的领悟都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你,就算《苦瓜》《陀飞轮》这样的歌词,你都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很真实的光头胖子,低回又真切地跟你讲述一个他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他把他丰富而敏锐的体验、深刻而感性的阅历,都通过他的笔触温柔而细腻的铺展开来,让你感到他的可爱、他的敏感、他的解脱、他的幻想都是实在而纯粹的,像曾经纯真的我们。
所以为什么黄伟文在不十分了解《红楼梦》的情况下能写出那么契合原著精神的作品?因为他的个性让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故事的本质:那种对于纯与美的怀恋与哀悼。
而林夕则不同,林夕的一切都是浪漫化、艺术化、解脱化了的,生于世上也许辛苦,然而他始终要为我们寻找出路。“拦路雨偏似雪花”唯美吧,然而“谁能凭爱意让富士山私有”?“吞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践雪径也未绝望”很激昂吧,然而“笑你我枉花光心计,爱竞逐镜花那美丽”,咱们都是“为悲欢哀怨妒着迷”的愚蠢人类啊!
林夕的出色绝不在于什么华丽辞藻,而在于他对一切苦痛和不公充满了伟大的怜悯与同情,《似是故人来》是林夕的锦衣华服,但《阿猫阿狗》才是林夕的底色。林夕绝对写不出《痴情司》那样的作品,因为他本身应该是觉得人世间很苦的那种人,他觉得他自己苦、世人皆苦、有爱的和无爱的、生离死别、蝇营狗苟、虚伪造作,都是痛苦。
他想解释一切、怜悯一切、他想通过他的词来表现这些感受,并试图为这种永恒的苦痛找寻一个出口,然而没有用。就像《富士山下》的访谈,林夕说创作的初衷是想为人们解套,但是听歌的人又上了另外一个套,又有什么法子呢?(顺道夹带私货,个人最喜欢林夕的几首作品是:《阿猫阿狗》、《失忆蝴蝶》、《斯德哥尔摩情人》)
林夕有点像苏轼,黄伟文有点像李煜。苏轼一直生涯辛苦,然而创作了很多貌似可以去“解套”的词,所以大家觉得苏轼好洒脱,可是没有对烦恼的开解,又何来洒脱的结果?洒脱岂非正是烦恼过后的余波?余有多少洒脱岂非更论证了之前有多少的哀苦烦忧?而李煜是另一种套路:我好开心,我好伤心,我好绝望。
他不解脱,他没法解脱,他只感受,他感受到“一向偎人颤”的欢愉,感受到“垂泪对宫娥”的无奈,感受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绝望,他感受什么,就说什么给你听。苏轼是文化,李煜是真心,所以很多词人说李煜不可学,因为他拥有那颗赤子之心是无法以文学教养来填补的。
就像我知道苏轼文学造诣更高,我还是心疼李煜;我知道金庸主旨更博大精深,我还是偏向爱烂尾的古龙。我仍旧对林夕的深刻洞察与智慧的同情高山仰止,然而我就是觉得黄伟文实在是太可爱了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