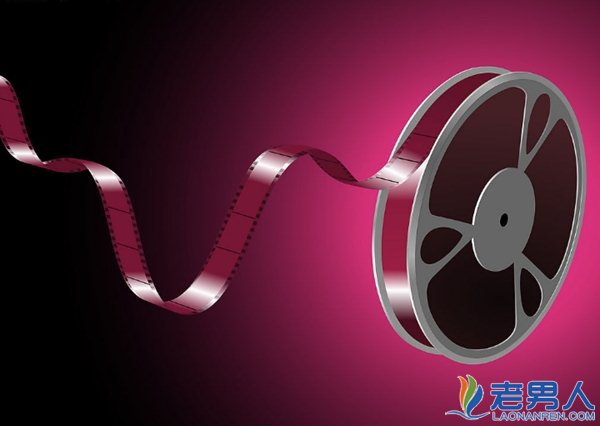霸王别姬分析 看懂电影《霸王别姬》 就能明白张国荣为何自杀
4月1号,除了是愚人节,同时也是哥哥张国荣的忌日,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哥哥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影片于93年上映,标注的类型为爱情、同性,在90年代的中国,关于同性这方面的电影,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但是丝毫不妨碍这部影片成为经典之作,即使是在今天,影响依旧深远,一直处在豆瓣TOP250的前3名。

哥哥一生所饰角色无数,但唯有程蝶衣,与他的形象气质完美契合,他的断袖情结、他的戏子身份,令人分不清哪个是戏里,哪个是戏外。而蝶衣“霸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挥剑自刎,却不幸一语成谶,化作东方文华楼下那潭鲜红刺眼的血。

电影曾获一九九三年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被认为是陈凯歌导演所拍的最完美的影片。影片场面精致华丽,人物刻画细腻丰满,故事荡气回肠,充分体现了导演驾驭镜头语言的娴熟程度。
电影讲述了戏子程蝶衣从20年代开始学习唱戏到70年代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练唱并最终自刎于他所饰演的“虞姬”最爱的人——楚霸王面前的戏梦人生。程蝶衣与师兄,楚霸王的饰演者段小楼,共同经历了20年代到70年代这段风雨历程。

师兄段小楼跟他感情甚佳,段唱花脸,程唱青衣。两人因合演戏曲《霸王别姬》而成为名角,在京城红极一时。蝶衣自小便被灌输“我本是女娇娥”的论断,渐渐长大的他也慢慢接受了这个观点,与师哥产生了雾里看花般的暧昧情愫。很快,这种局面被一个叫菊仙的女子打破……

故事氛围营造的可以说非常成功。人物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间满是那个年代的风情,精致的戏服之下缓缓流淌的是惆怅与感伤。作为第五代导演中最懂戏的陈凯歌,多次巧妙地将戏曲完美的勾勒出中国传统气息。
开头对于“磨剪子嘞…锵菜刀……”的声音和寒冷的冬天北京城的极力描画,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也营造了冷冽而略带悲怆,惆怅而略带苍凉的氛围。画面共三次出现了这充满了京味的叫卖。第一次是在北京灰暗的天空下,风尘女子抱着儿子走进戏班子之前。
叫卖被拉得很长,像是画面出现的逼仄胡同。画面以冷色为主,营造了淡淡哀愁的氛围。第二次,在寒气逼人的戏班子外面,女子亲手将儿子怪异的第六指生生的砍去了。暗色的背景,深色的棉袄,与画面上鲜红的血迹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此时的全景镜头缓缓移动,像是一把刀钝钝的,一下一下将人带入刻意营造的带着一丝丝绝望的氛围。画面突然又转向了那逼仄的胡同,京味的叫卖,不得不佩服导演的神来之笔,原本不相关的情节被紧密联系,仿佛“磨剪子嘞…锵菜刀……”的叫卖就是小蝶衣的痛苦叫喊,灰暗的天气就是他内心的阴霾。
第三次,是蝶衣挥舞着鲜血淋漓的手,一路跑向师傅的厅堂,摁下了学戏的契约。镜头在交待完拜师之后,又移向了胡同。背景音乐适时出现,舒缓了绝望的氛围。冰冷的冬日在有了音乐的镜头下变得有些暖意,之前情节的跌宕得到了很好的缓解,氛围在傍晚的微醺灯光下变得抒情、夹杂挥之不去的怅然。
程蝶衣为日本人唱堂会中杜丽娘的华美唱腔和堂会安静到诡异的气氛,营造了和谐安宁甚至是美好的氛围,在这层表面之下,是巨大的苦楚与压抑。导演用一个移镜头将程蝶衣映在窗前唱戏的身影慢慢呈现,使得巧妙出现了一格一格的移动画面,表情木然的日本士兵把守在门外,这样的画面呈现了流畅的精致之美。
画面又回到了堂内。蝶衣的扇若翩跹的蝶纷飞,他的表情是杜丽娘的寂寞:“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伤心乐事谁家院!”眼神早已化为千年一曲戏梦中的伤情,也怪不得捧角儿的袁四爷赐与他“出神入化”的匾额。
他的戏梦人生全是为爱伤透了心的女子。所以,他也成了女子,成了虞姬,为情所伤。一曲终了,余音绕梁。可下面竟是一群想体验“生活”的日本兵,他们礼貌的用白手套鼓掌,“啪、啪”,沉闷的声音使屋内的氛围变得古怪而沉闷,这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梨园文化与日本只会欺凌别国、根本不了解京剧的士兵所碰撞的必然结果。
导演苦心安排了一个叫青木的官员,他懂戏。程蝶衣这样的戏痴,将他看成是上宾。以致几乎忘了他的初衷——他是为了救师哥段小楼而被迫唱的戏。
在堂会中,青木第一个鼓掌,表现了对于蝶衣的首肯,后来鼓掌的近景镜头让画面呈现略微繁复之感。蝶衣的痛苦,蝶衣对于青木也懂戏的兴奋,在大堂沉闷鼓掌声中交织在一起,巨大的苦楚与压抑在整个空间化成无形的网,压向程蝶衣。
影片的最高潮,程蝶衣声嘶力竭的控诉,菊仙绝望的眼神,段小楼口不对心的呈述罪状,将故事的氛围推向了最高峰,营造了斗争激烈、悲愤绝望的氛围。文革时期人性的丑恶,师兄弟之间的情愫,戏子与妓女的爱情,都在那个火盆面前,扑向了盛大的死亡。
程蝶衣被压倒在火盆前,妆花了一脸。他望着说着他罪状的段小楼,面部的特写让蝶衣内心活动表现在脸上,惊诧、失望、绝望,从那双眼睛里,所说着太多太多。他突然站起来,“我也揭发,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颓垣!段小楼,你,自从和这个女人成亲之后,我就知道完了。全完了。……”
从他的语无伦次里,从红卫兵“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里,从菊仙惊恐的表情里,所有人性的丑恶,都在这阳光下暴露无遗。陈凯歌导演用人的角度审视了这一场文化浩劫,用直白的几乎像记录片的镜头,表现中国下九流的“职业”中的戏子与妓女不被中国人所认同,营造了悲愤的、绝望氛围。
寂寞的戏梦已伤千年。舞台上的蝶衣表情决绝,一把抽出“霸王”段小楼腰际中的宝剑。程蝶衣在戏中完成了最美的轮回,而霸王,一如千年之前的错愕。
哥哥是九零年代华裔男演员中极为抢眼的一位,他和陈凯歌、王家卫等大导演合作的《霸王別姬》《阿飞正传》《东邪西毒》等片,在国际间都有举足轻重的评价,而他在这些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阴柔气质,不但成为紧扣影迷心弦的魅惑,更成为一种电影艺术的议题。关锦鹏曾以此为主題和张国荣共同完成了一次极为难得的访谈。
以下为访谈内容的节选,看看哥哥自己是怎么来评价电影《霸王別姬》的
关锦鹏(以下简称「关」):在《阿飞正传》 《新夜半歌声》 《霸王别姬》这些戏里,导演似乎都把一些自恋的、美貌的、甚至阴柔的特质,落到你身上,你觉得导演们是不是针对你本身的个性因势利导?
张国荣(以下简称「张」):我想是有的。毕竟我在舞台上的形象总是很强烈的,或许别人也就这样认为拿一件不漂亮的衣服给我穿是不对劲的,而要继续美化它。很多导演自然会给我一些美化的角色,对于这种状况,我无能为力,因为那是导演的意思,我要尊重他。
关:那么你介不介意我问你,你本身是不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张:绝对是!一定是(他用了英文Absolutely,笑得很是自信)!这件事是没得抵赖的。
关:OK!我们看到过去有许多电影,片中有很多男性的角色是由女性来扮演,这当中多少会有一个现象:那个年代一些女性观众把她爱慕的对象投射进戏里的人物里面,这难免会有一些危险,但是如果那些男性的角色由女性来扮演,那就安全多了。今天,这个例子少掉了,而一些比较阴柔软性的角色你也拍的不少,你认为你处理这些比较阴柔的男性角色,与以前那些女性反串男性角色,其中的分别应该在哪里?
张:以《霸王别姬》为例吧,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我演这类角色时,很多人是很认同的,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演这样一个花旦的角色是不妥的,是会惶恐不安的。我认为,一个演员除了追求功名之外,还必须让观众信服!
关:你觉得这样一件事是与你平时在舞台上的表现,或者你一出来给人在性格、在外观上的印象等等的结合,而建立了让观众信服的结果?
张:(笑得很谦虚)现在,我当然希望观众能够认同「只要是这种角色,就非张国荣莫属」。我不需要去展现我的肌肉,像蓝波·阿诺那样,这方面成龙已经做得很好了,而如果在「阴柔」这个特质上我是第一名,why not?
关: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可能不需要很用力,就可以以一个男性演这类角色而令人信服,那么,你认为你演的这类角色时有没有你对自己的看法而非别人对你的看法?
张:我的确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有东西是其他人所没有的,这件东西就是连观众也都认同的——有些观众认为我很敏感,尤其在对爱情的态度上,使用一种比较细致优雅的方式来表现;或许也有人认为80、90年代的男人应该表现威武雄风(抬起拳头勾了几拳说:「你拼得过我吗?」),但是这当中的感觉就有差别了,所以我想,总有些东西是我有的,而别人可能没有。
关:有一些批评提到,陈凯歌在新的《霸王别姬》里面与罗启锐曾经做过的版本最大的不同,就在这最后一场。罗启锐把它结束在程蝶衣与段小楼两人在浴室里话当年,而陈凯歌则变成程蝶衣角色的自杀,因此,就有人质疑陈凯歌有同性恋恐惧症,以你跟他合作的观察,你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张:我想应该可以这么去解释,就是因为......(在这里思考停留了有15秒之久,才接出下一句话),因为写《霸王别姬》这本小说的李碧华是个香港人,近年来,香港对于同性恋资讯的摄取与思考基础多半不脱欧美的范围,他对同性恋的看法是比较西方的观察角度,而陈凯歌看同性恋是很中国化的,很地道的中国,或者甚至是很北京的角度去看,对于他的判断,我无从批评是对是错。
其实,在拍结尾戏的时候,我们是有过相当激励的讨论的,我曾经极力要求保留两个男人在澡堂的一段对话,然后如何合理地结束这个故事;但是陈凯歌的解释是,经过文革的一番激情,葛新死掉,这个时候段小楼如果自杀,会凸显这个角色是最伟大的,他并不想这么做,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把文革当这部片子的高潮,在这个地方喊停,然后在若干年后再重新发展一个故事,那又必须加长电影的篇幅才能说服自己;关于这点,其实是没得争的,大家看的东西本来就很不同。
至于你问我陈凯歌有没有同性恋恐惧症,我认为他没有;但是你问我他是不是那么懂的同性恋,以我对现代同性恋的知识来看,我认为他并不懂。关于在结局意见上的差异,虽然是很矛盾、很对立,但是,我是一个演员,我应该尊重导演最后的执行意见。
关:程蝶衣这个就角色现在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先前也曾经邀请过尊龙来饰演,你可不可以客观的谈谈你与尊龙在诠释这个角色上可能有怎样的不同?
张: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个人的优点,阿尊或许没有我所能表现的那么细致(我认为阿尊的「本我意识」会大过我)。有人以为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人在争这个角色,其实并没有有争过,我一向厌恶与人争东西,主要是当初他们提出的合约条件与我无法完全契合,之后,他们与阿尊谈的合约也出现问题,所以又回过头找我。
至于在表演方式上的不同,我不知……,基本上,我是以一种相当细致的手法来演,而且,也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学普通话与京剧等等。阿尊是一个好演员,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认份地去忍受一些苦,《霸王別姬》确实是一部拍起来很苦的戏,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同时,我想,我演的程蝶衣会阴柔过他,毕竟无论怎么看,他的外型看起来多少是比我英气一点,这一点就会让我们两人对程蝶衣的诠释有所不同,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就比较好。
关:所以,就会有人以为如果要你重新选过,你会挑程蝶衣胜过段小楼。
张:确实!因为我觉得段小楼似乎就没事做了,在戏里面,他总是被带来带去。有许多观众会认为程蝶衣是个极其宿命与悲剧型的人物,我却不那样认为,程蝶衣其实是个很积极的人。
在舞台上,他可以醉生梦死地演出,在舞台外,他与师兄的感情却是可以完全不理旁人的,这样的态度,在中国的同性恋发展上他应该是一种先驱。在我们做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不止在京剧,其他地方戏曲中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只是许多人将它掩藏不说,我们拜访到的老前辈们就说,即使不明言,从一些当事人彼此互动的小动作都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程蝶衣就是整部戏的灵魂,做为一个演员,做为一个诠释他的演员,我觉得他这么做是最佳选择的。
关:(这里未出现关先生提的问题,就直接是张国荣的叙述了。)
张:一个观众买票进戏院,每个人的接收能力都不同,譬如,1000个看《霸王別姬》的观众之中,我想大概会有50个人觉得很闷,500个人认为很好看,大家看到的都很不同,但是,我认为有一样东西是演员必须有的——他得有他自己的魅力。
在整部戏里,观众看得最多的人是你,如何让他们认同你的角色,这是需要个別议论的,不是每个人对任何角色都能胜任的。我敢打赌如果请周润发来拍这部戏,恐怕就完蛋了,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是这样的。
就我而言,从影以来,我拍过六十余部电影,饰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近几年来,也有很多人肯定我是一个很扎实的演员,而现在接演这个角色也正是时机,如果早个五年、十年,我接下这类角色恐怕也行不通。
这是我与陈凯歌合作的第一部戏,在此之前并不熟悉,彼此不是那么了解,对许多东西的要求也不甚相似。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导演,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跳出香港电影的框框,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电影。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应该了解当时中国把道德放在怎的位置上,他们会怎么看同性恋,因为我拍过很多电影,对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掌握自然很小心,我想,问题可能出在陈凯歌自己要有计数,大家都要心有计数。
关:你的意思是针对观众?
张: 对,就是针对观众,看看观众可不可能突然间去面对一个同性恋的议题,在看戏思路上是否转得够快?这个虽然有例子在前,但似乎还是需要探索,需要去考虑有同性恋恐惧症的人,我想,「如何说服观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一面倒地单恋性格或许加重了你的戏份,但是做为一个演员,从小说到电影的这种改变——一面倒地单恋段小楼,这种感觉你觉得舒不舒服?
张:小说和拍出来的电影不尽然会完全一样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本小说和以前也有人找我谈过的同一部戏的其他剧本,加上陈凯歌的剧本,三者其实都不一样,基本上,我有我自己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而不是用小说的角度,至于你问我拍《霸王別姬》舒不舒服,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是有点不舒服,我觉得拍起来有点绑首绑脚,无法放开来作。
就这部电影来说,我觉得小孩子的部分比成年以后的部分好看,在小孩子的部分,陈凯歌义无反顾地表现所有的东西,反而是成年之后变得很多事是收回到心里去不想说了。
大概是因为这是与他合作的第一部戏,我尽量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希望下一部电影,可以擦出更多的火花。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大陆导演的思维风格,他们对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钦慕,还是很放不开。
关:这是不是也对应了刚刚谈到的,大家应该顾虑到市场和观众来做调整?
张:其实,我身为一个演员,倒是希望这部电影能多著重在两个男人的关系描述上,因为那才是大家最爱看也最值得探讨的。
曾经有人说,哥哥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与男友的感情问题,如果你看懂了这部《霸王别姬》也许就能明白哥哥为何轻生。